我也说不清,南阳老家是哪一年开始用割麦机麦的。只记得一个伤感的故事,我有个发小的奶奶跪在一台割麦机前,哀求远方来的麦客帮助割完家里的几亩麦子。她的儿子生前还是个村干部,死于绝症,自此以后,她做什么事都要求人。
抢收就是抢粮,也就是抢命。没经过六十多年前的那场饥荒,你不会认同老年人对粮食的感情。夺人田地,毁人青苗,盗人粮食,曾在无数年月里与拐人媳妇挖人祖坟一样败坏。因为,这些都会使人断子绝孙。
我很难接受唐河县连续好几天不许割麦机下高速的逻辑。传说中的这证那证很多很多,但阴雨当前,抢收的窗口期也就那么几天。你们当干部的是不愁吃喝,但老百姓的麦穗就活该在田地里发芽吗?
发芽的麦子不是不能吃,是吃了不顶饿。今天下午,我的朋友圈有很多朋友跟帖,分享他们吃发芽小麦的经历。他们来自河南的最多,还有陕西和山西的。我当然也吃过,那是一九九零年代,大概有两年时间,现在想起发芽面馒的味道,嗓子就有点呕。
它有点甜,但带着霉味。馒头蒸得时间再长,也软塌塌的,吃着粘牙,咽着咽喉。这种面粉还不能轧面条,丢锅里一煮就会烂。
但农民还得交公粮,粮管所是不收这种麦子的,那一年你要么交陈麦,要么直接给镇政府交钱。到第二年,你再把好麦子卖一些换钱。这也是我们只有一年遭了雨灾,却吃了两年发芽麦的原因。
我以前写过,我上初中之前,春天基本都吃不饱。捱到割麦,就能吃饱了。割麦虽然苦,干起来却很是有劲儿。经常天不亮,我就被母亲喊(打)醒,握着镰刀走到几里外的麦地,一直割到大中午。户外三十多度的暴晒并不可怕,最难受的是腰疼。你不能站,不能蹲,只能弯腰躬脊,把一大丛麦芒揽到怀里,再一镰一镰放倒。汗水从你的额头不停流入眼睛和嘴巴,麦秸秆上的浮灰也漫天飞舞,呛得个人的脸上、身上和鼻孔里全是黑灰。
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绝望,就是在麦地里。一个十岁出头的瘦弱男,累极热极脏极之后,站直腰,面前的麦浪却还是看不到尽头,父母还在催促甚至叫骂。那就叫绝望。
不得不吃苦,恐怕是世间最常见的一种绝望了。绝望久了,人就难免顺服。当时割麦子,四十岁左右的父亲好几次开玩笑说,如果能请来孙悟空,变出一百个小猴子,帮我们赶紧把这块地割完该有多好?——让大圣给他变几张法币出来,他想都不敢想。
父亲在六七岁的时候,差点被饿死。为了给他和其他孩子分点口粮,我的曾祖、我奶奶的父亲和爷爷,都饿死了。你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如果我不专门去问,也不会知道。在历史上,他们不配拥有一个字符的位置。
前几天,被检查站分隔的麦客和南阳农民,他们在翻腾的乌云下,心急如焚,求告无门。他们一定也很绝望吧,但他们确实也不配拥有名姓。——接下来,有哪个有名有姓有身份证号码的人,不得不在明年春天勒紧裤腰带,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我们只会被告知,人民都吃饱了。只是有些官员呀,吃得太饱,没事找事。他们真不配先人节衣缩食地养他们长大。
(刚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我家有十来亩麦子,也烂到了地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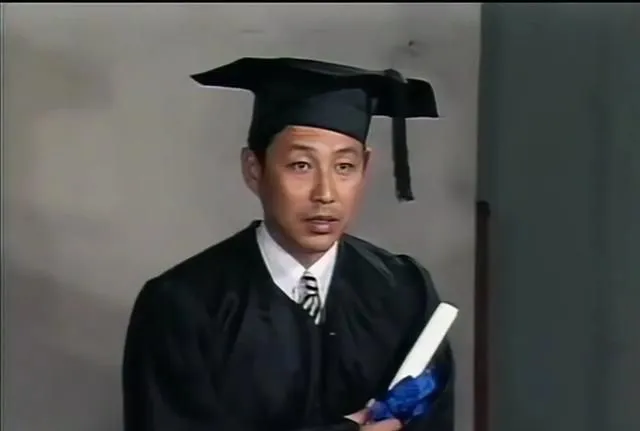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微信或手机浏览器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