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不必然是“打工人”,只有在一定的制度下,工人才会变成“打工人”。工人变成打工人,最根本的条件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这个分离最初是在80年代出现的。
一、城乡资本的复活和体制外打工人的出现
(一)城乡小生产的发展:第一批打工人的诞生
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破坏了集体经济,这造成了两个后果:(1)农村形成了大量自由劳动力。集体经济时期,农民在农忙时节从事农业劳动,在农闲时期从事集体劳动(如修水利等);集体经济破坏后,农闲时期不再从事任何集体劳动,形成大量富余劳动力。(2)分田单干造成了小农经济,而不稳定的小农经济必然出现分化,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在政策的支持下承包农田、鱼塘、副业,并雇工经营。
1979年,在分田单干尚未大规模推行的时候,广东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并雇工1人。陈志雄的雇工行为引起了广泛讨论,1981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文章称陈志雄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
如果说陈志雄雇工一人还能说他收入较高主要是多劳多得,那么接下来的发展很快就突破了人民日报的论调。分田单干迅速导致贫富分化,“两户一体”(专业户、重点户和新经济联合体)大量出现,他们在政策支持下获得优惠贷款,承包农田、机器,雇佣农业工人进行生产。于是,农村中第一批“打工人”出现了。
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小生产也悄然出现。1979年,为解决闲散劳动力就业(比如返城知青)问题,召开了全国工商局长会议,允许在修理、服务等行业开展个体经营。这是城市资本发展的第一步。小生产快速发展的同时,一批个体户逐步积累资本开始雇工经营。怎么看待城市个体户雇工经营的问题,和怎么看待农村雇工经营一样,引起老干部广泛讨论。最终在1981年(也就是人民日报定调陈志雄雇工不属于剥削的那一年),国务院出台文件规定,“个体经营户,必要时,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于是,城市中也出现了第一批“打工人”。
(二)城乡资本的发展:第二批打工人出现
社会主义条件下居然出现了资本式的雇工,这到底算不算剥削,这个问题让很多老干部感到疑惑。为了在理论上给改革开路,有人从《资本论》中找到例证,通过篡改理论的方式论证雇工的合法性。事情是这样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这一部分中,马克思为了说明资本增值运动必须要有最低限度的价值额,为此而举例说,假如工作日为12小时,其中必要劳动时间8小时、剩余劳动时间4小时,那么为了使资本家的生活比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一半转化为资本,这样他必须同时至少需要雇佣8个人。有人如获至宝,明目张胆地篡改理论,说马克思划分了小业主和资本家的界限,雇佣8人以下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雇佣超过8人才是资本家。
中央以此为据,对雇工是否合法给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8人就不是资本家。但是资本的发展异常迅猛,几乎就在中央定调的同时,城乡资本的雇工已经超过了8人的界限。
在农村中,变卖或承包社队企业导致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进一步分离,这为资本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1978年前,社队企业是农村集体工业的重要体现,也是新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措施。他们采取就近取材、因地制宜的方式,从农副加工、采矿、建筑、农具制造、农机修配、运输等各种行业,旨在服务本地农民,反哺本地农业。但是改革以来,社队企业的固定资产被折价变卖或承包给个人经营,社队企业从名义上的集体企业变成了事实上的个人企业。而集体经济被破坏后,农闲时期又富余出大量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需要寻找就业出路。无疑,已经事实上私有化的社队企业成了他们就业的重要去向。他们农忙时候从事农业工作,农闲时候在社队企业从事工业劳动,典型的特点就是“离土不离乡”。于是,在农村开始形成了第二批“打工人”,他们受雇于名义上还是集体经济的社队企业(1984年改名为乡镇企业),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但是资本发展再次突破了这个界限。一方面,相对于集体农业解体后出现的大量闲置劳动力,乡镇企业的规模显得太狭小了;另一方面,私营企业迅速发展,开始和国有企业抢夺生产资料,导致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衡。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沿海开始推广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原料从海外来,产品往海外卖)。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完备的工业体系、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力以及优质的营商环境,是世界上一切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兼备的,这使得沿海成了资本增值的天堂。80年代中后期,农民工开始向沿海转移,出现了数千万“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这在农村中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打工人”,他们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工资成了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在之后的新闻媒体中,他们被称为“农民工”。
在城市中,一批积累了资本的小生产开始扩大规模,成为了事实上的私营企业。1979年,靠炒瓜子“发家致富”的年广九雇工已经超过10人。1982年,“傻子瓜子”的雇工规模超过百人。1986年,傻子瓜子年终销售更是在3个月内实现利润100万。于是,城市中也出现了第二批“打工人”,他们受雇于城市的私营企业,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城乡私营企业的发展是如此迅猛,到1987年,“城乡私营企业雇工达361万人,平均每户雇16人,雇工30人以下的占70%-80%,雇工超过100人的接近总数的1%。”
如果说个体户雇一两个帮手,老干部还能说服自己这不是剥削,那么对雇工高达100人的私营企业又当如何看待呢?这些老干部,不乏在参加革命前就是雇工或长工出身,难道他们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为平复老干部的情绪,总设计师多次开会统一思想。1983年他指出:“有个别雇工超过了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只要方向正确,头脑清醒,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十年、八年以后解决也来得及,没有什么危险。”,1984年再次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事实上,一直到1987年之前,我国只允许有个体经济,而不承认有私人资本。1984年文件指出,对雇工超过8人的采取“不鼓励,不禁止”的政策,而不能按资本主义看待。
私营企业就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野蛮生长,直到1988年修宪。而在私营企业野蛮生长的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侵蚀国企。
二、国企改制:国企主人沦为打工人的过程
(一)1978年之前的国企
1978年前的国企工人不是“打工人”,他们是“企业的主人”。他们和打工人的区别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工人与企业的关系。打工人只是企业的雇员,企业可以随时解雇他们。但当时的工人并非企业的雇员,企业没有权力开除工人。由于企业没有权力开除工人,因此企业的干部也不敢随意训斥工人。干部和工人的关系相对融洽,干部不是靠权力压服工人,而是通过模范带头作用引领工人。
其二、企业利润的分配。打工人只能获取工资,而不能享有企业的利润。当时的工人是企业的主人,那企业的利润自然应该由主人享有,而不是由企业的管理层霸占,这是工人和打工人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当时的企业,除了支付工资外,还通过各种福利将利润反馈工人。比如,企业有自己的医院、学校和修房子的住建科,职工享受免费的医疗和教育,并且享受福利分房。
其三、企业的管理。打工人仅仅是企业的雇员,因此他只有服从领导的义务,而没有管理企业的权力。当时的工人是企业的主人,那么主人就不能仅仅有服从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权力。《鞍钢宪法》作为当时企业管理的原则性规定,在制度层面保障了工人对企业的管理权。《鞍钢宪法》可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被动的工具,不是被动的领受任务,而是主动的自觉的人,主动参与到企业计划的制定和管理之中。
企业不能开除工人,工人能够参与管理,因此工人也能够最大限度监督干部。70年代末期,某个钢铁厂的领导公车私用,被一群工人堵在厂门口,要求他下车来解释,这个车拿去干嘛了,为什么要占国家的便宜,厂领导乖乖下车,低头认错。
这个年代的工人,有福利、有待遇、有民主、有权力,他们由衷感到自己就是企业的主人,他们和打工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对国企而言,改革改的就是这三点。
(二)国企改革在改什么
国企改革的第一步是收回工人对企业的管理权。1979年国家推行放权让利,在国营企业建立厂长负责制,收回工人对工厂的管理权。为缓和工人的抵触,在收回工人权力的同时,给工人增加工资和奖金。从短期看工人收入增加,从长期看工人权力丧失,最终必然导致更大的经济利益的丧失。
国企改革的第二步是利改税(1983年)和拨改贷(1985年)。我国企业以前所有利润统一上缴国家,如果需要扩建厂房或者购买设备,则由国家无偿拨款给企业。利改税和拨改贷,就是用所得税替代利润上缴,用有息贷款替代无偿拨款。先看利改税。以大企业为例,国营大中型企业按55%的比例缴纳所得税,税后盈余还需按一定比例上交。整体而言,企业要将大约7-8成的利润通过利税方式上缴国家。再看拨改贷。国家收走了企业8成的盈利,却不再给企业的建设拨款,而是要求企业向银行借贷。私企外企的综合税率只有17%-33%(本身税就低,还有各种减免),而国企综合税率高达7-8成,这使得国企在极度不公平的环境下参与了市场竞争,为之后国企破产埋下伏笔。
随着一长制的恢复,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权利,管理层逐渐失控。1982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表明,一些领导干部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的子女安排较好的工种,在提干、晋级、住房分配等涉及群众利益方面,都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以特殊的照顾。企业厂长由上级领导任命、委派,实行负责制,职工满意不满意都得接受,干好干坏群众既不能褒,也不能贬。他们说:“工人只尽主人翁义务,没有主人翁权利,主人担风险(企业办不好,领不到工资),公仆有保险(企业办垮了照样当官或调走了事)”。企业干群关系开始紧张,工人用消极怠工来对付干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1987年推行的承包制进一步降低了工人的积极性。承包制就是把国营企业的各个车间部门承包给各种厂长、书记、主任等等,这些人按承诺缴纳一定的利润,剩下的钱可以自行分配。承包制使得工人和干部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这样,通过两权分离就创造出来“先富起来”的一批干部,工人与经营者奖金差距日益拉大。工人对工厂的变化看的非常清楚,工人中都流传着这样的话:“工人穷,厂长富,车间主任万元户,厂长挣钱没有数。”此时的工人,已经开始逐步从主人沦为打工人。
一长制使得厂长建立了工厂里面的独裁,承包制扩大了工人和干部的收入差距,这还没完。厂里面的领导为了赚更多的钱,开始在外面建小厂。钢铁厂的领导开个焦炭厂,高价把焦炭卖给自己单位;媒矿的领导在外面开个洗煤厂,私底下利益输送。这一切,都被工人看在眼里。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工人和工厂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曾经在毛时代积极奋战的工人,有一些人开始变得偷奸耍滑。70年代的时候,某个钢铁厂的领导公车私用,被一群工人堵在厂门口,要求他下车来解释,这个车拿去干嘛了,为什么要占国家的便宜。80年代的时候,还是那个钢铁厂,还是那些工人,他们开始从厂里面偷钢偷铁,拿一块好点的钢回家去打把菜刀,或者投点特殊钢材拿去卖给私人老板。你问工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干啊?”他说,“领导大偷,工人小偷,这有什么问题吗?国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部分工人开始了磨洋工。当资本制度全面建立时,曾经的主人由抱怨而愤怒、由愤怒而反抗,最初这种反抗是消极的,是以怠工或磨洋工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一种声音出现了,他们痛斥工人偷懒,他们大呼人性本恶,他们说国企效率就是低下,国企工人就是磨洋工,他们说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国企没有清晰的产权制度,“全民所有就是全民所无”。但他们却从来不说这一切都是什么造成的,他们也从不建立一个规章制度去限制资本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这些人献言献策,要建立一个由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明晰的产权制度构成的现代化企业,去防范工人从厂里面拿钢拿铁,去防止工人“偷懒摸鱼”。其本质,就是把工人从主人变成打工人。
1994年通过并于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劳动者仅仅是企业的雇员,而不是工厂的主人,也就是说,从法律意义而言,工厂有权力开除工人了。
90年代中后期,随着住房、医疗和教育改革的推进,国企工人享有的最后一点福利也被剥夺。
他们不再享有管理企业的权力,他们不再拥有铁饭碗的身份,企业的利润也不再通过各种福利反馈他们。从这个时候起,国企工人彻底沦为“打工人”。
(三)下岗:第一批被优化的打工人
1996年一季度,在长期不公平的竞争中(至少有两点:其一、税收不平等。其二、私企和外企只给职工发工资,而国企除了工资,还要给职工修房子、看病、上学),在国企乱象横生的背景下,国有工业企业首次出现全行业净亏损。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6599户,亏损面达39.1%。而导致这一切的锅,自然又是由那些“磨洋工”的国企“打工人”背了。
面对当时的局面,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砸三铁、甩包袱,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台的。在此前后,国有企业甩卖了自己的医院、学校,分出了自己的住建科成立房地产公司,优化了大批国企“打工人”以减少成本。
被优化的打工人生活境遇迅速下降,以三线职工为例,2005年三线被优化的职工月收入低于300元的有68%,收入的92%用于衣食和子女教育,88%的人无法养活自己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福利、亲友救济。被优化的那些人生活没有着落,出现了各种人间悲剧。有女工为了小孩读书,被迫去站街。有男工为了自己的小孩上学,吃了某种药制造了一个大新闻,让社会捐助自己的遗孤。还有一个在全国都流传很广的事情,某家小孩好几个月没吃肉了,忍不住去菜场偷肉,抓住后被痛打一顿,让父母来领人,他父亲老泪纵横,当天晚上花了所有钱买了一只鸡炖给全家吃,这锅汤里面放了准备好的老鼠药。
1997年刘欢的《从头再来》就是给这些被优化的人。“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工人听了这个歌当时就直骂娘,你为什么不走进风雨,凭什么叫我们从头再来!
黄宏的小品也是在说这个事情,里面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笔者父亲听了当时就火冒三丈。笔者和他争论,工人就是要为国家想啊,要有大局观啊。他把衣服一脱摔在地上,背对着笔者说,“看见没有,背上的这些伤,你爸爸没有为国家想吗!我和你妈,现在都四五十岁了,我们TMD被当包袱甩了,你懂不懂!”至今,这些人谈起那些要把他们当包袱甩掉的人,简直是咬牙切齿。
这些沦为“打工人”的曾经的主人,有数千万人被优化掉。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迫使他们开始关注自身的权利。到2005年,全国群体上访涉及约400万人,其中以他们为主体的有40%。
三、新世纪以来私企打工人的生活
打工人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资本的雇佣奴隶。“要理解什么是主人,就要理解什么是奴隶。主人的对立面就是奴隶,奴隶的主人是不信任奴隶的,怕他们偷懒,所以随时都拿着皮鞭抽打他们,强迫他们工作,根本不把他们当人,只把他们当会说话的工具。”
打工人奴隶般的生活,在沿海的私人企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你就是个打工的
1993年,致丽大火夺去了87个女工的生命。调查结果显示,资方为了防止打工人偷东西,将逃生通道用拉闸门上锁封死,将窗户用铁条焊死,以至于在厂区起火之后,女工只能从仅有的一个出口逃生。众多女工涌向狭小的通道,在相互踩踏、浓烟肆虐中失去了生命。致丽大火以一种异常悲凉的方式,提醒着全国人民,资本对打工人的统治已经彻底建立起来了。
致丽大火促进了《劳动法》出台,但《劳动法》的首要意义并不在于它规定了若干保护劳动者的条款,而在于它明确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工人不再是企业的主人,而只是企业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在打工人已经在城乡各地出现十数年之后,法律终于明确了他们的身份,“对!你就是一个打工的!”。
在招商引资的大政方针之下,各地争相优化营商环境,资本肆意蹂躏打工人。
管理方面,资方管理粗暴,动辄辱骂职工,体罚工人,更有甚至部分资方嚣张跋扈,殴打职工,限制职工人身自由。工资方面,打工人工资不仅长期不涨,资方还故意拖欠发放、逼迫员工自离,花样百出克扣工资。
打工人领着微薄的工资,自然也只能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大多租住城市的犄角旮旯,80%以上是临建房或简易房,位置偏远、建筑密度大、卫生条件差、安全隐患高。频发的城中村电动车起火事件,夺去了不知多杀打工人的生命。为了打工,他们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小孩,数以千万的打工人小孩成了留守儿童。
他们为资本增殖贡献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但在资方眼中他们只是创造财富的工具。资方会爱护机器,因为机器是资方花钱买的,坏了还要花钱修,但资方不会爱护打工人,因为打工人伤了把他开了就是。《广州日报》2005年有一篇报道称,广东省有1300多万农民工,珠三角企业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珠三角的工业辉煌,民工们“贡献”的手指头已经几十万计。
(二)抗争、《劳动合同法》和996
这一切都引发了打工人自发的抗争。根据劳动部专家的分析,我国从1990~1994年五年中参加集体停工的人数分别为:24.3万人、28.9万人、26.8万人、31.0万人、49.6万人。到1999年,全国受理劳动争议案件12万件,其中集体争议涉及的私企和外资劳动者占21.9万人。排第一位的争议原因就是欠薪。
2003年沿海地区出现季节性缺工后,工人同老板的谈判能力提高,行动越来越多,掀起了一股延续数年的小浪潮。
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以前不到1万起,每年集体劳动争议工人数顶多30万;到2004-2005年每年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就达近2万起,每年集体劳动争议工人数40-50万;到2008年,集体劳动争议案件达到2.2万起,集体劳动争议工人数超过50万。
![[s]1.jpg](http://img.wyzxwk.com/p/2021/01/d949b7df448dd22bebe147f27fbae48d.jpg)
这构成了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的大背景。
如果把劳动与资本的对抗看做一场战争,劳动合同法这种法律出台,一定程度上又可看做两军在重新制定停战协议书。
以前体力无产者需要在每一个场合通过个别斗争来争取合法权益,但有了劳动法律之后,他们很大程度上不必如此。即使在某些场合,体力无产者的力量明显不足以争取到这些权益,资方也可能出于“守法”的考虑而主动妥协。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这个阶级之间的停战协议,保证了被压迫阶级在某些力量较小的个别场合,也能获得相应的权利。
对体力无产者而言,5天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标准、劳动法关于加班费的条款,这三者必须连起来理解。通过限制最低工资,迫使体力无产者自愿加班,通过加班费条款,使得体力无产者在6天12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能够养家糊口。对统治阶级而言,这才是加班费条款的真实意义,即,通过这个条款调节体力无产者的收入,使其在6天12小时工作制下能够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至于脑力无产者的加班费,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看来,这种996剥削方式能更好地压迫劳动者群体,而暂时还不至于引发实质性反抗,因此根本不必改变。
当然,法律作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停战协议,自然也应该适用于阶级中的任何一个群体。比如,加班要给加班费这个规定,就应该既适用于体力无产者群体,也适用于脑力无产者群体。但是脑力无产者的这种适用,与体力无产者的这种适用截然不同。脑力无产者还必须通过在单个场合的个别斗争,才能去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费。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脑力无产者似乎还有一些阶层跃升的希望,因此他们宁愿忍受没有加班费的996,而不愿和公司闹翻去要加班费。
2015年后,随着经济下滑,劳资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资本的压迫更重了。以前,996虽然残暴,但还有些念想,年终奖毕竟还比较客观,房价也没有那么夸张,就算被公司优化,找工作也并不困难。现在,996更加残暴,年终奖没啥指望,房价早已上天,35岁以上的人工作都朝不保夕。不得不感慨,好日子似乎到头了。
近些年来,熟练掌握互联网的脑力无产者抱怨越来越多。他们用各种黑话表达不满,用各种梗冷嘲热讽。而官媒总希望劳动者闭上抱怨的嘴吧,和他们一起讴歌盛世。前段时间某官媒微博发文,鼓励年轻人顶住压力追求梦想,微博下面一片骂声,有说房价的,有说工资的,有说996的,官媒被打脸后不得不关闭评论。有人截图后写了一句话,才一千条评论就顶不住了,你还让年轻人顶住压力。
脑力无产者玩打工人梗的风波,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这样的行为,从现象层面看是玩梗,是自嘲,从本质层面看,却标志着脑力无产者自发的觉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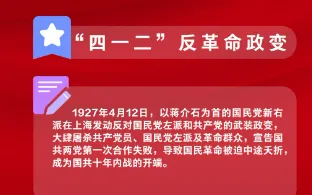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评论功能已恢复开放,请理性发表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