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财政亏空
《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在国产剧里评分很高,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部剧。喜欢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反映历史,事实上“改稻为桑”这事本身是编剧虚构出来的。但这完全不影响它是一部好剧,好就好在它里面所讲的矛盾、政策、权力、党争,都是围绕着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展开的。
现在的很多剧,好像大家都不用考虑吃饭,不用考虑经济问题,剧里的人每天净为了些舞文弄墨、争风吃醋的破事斗得不可开交。即使讲点政治斗争,也因为脱离了生产实践,而显得极其幼稚。
言归正传,回到这部剧里“改稻为桑”的问题上来,为什么这样一项看起来“上利国家,下利人民”的政策,在嘉靖亲自下令实施,多方势力极力推动的情况下,最后仍然走成了一步死棋?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从这项政策的诞生源头开始。
为什么一开始会有这个“改稻为桑”的国策?
原因很简单:财政亏空。
不要以为财政亏空只是引起“改稻为桑”的原因,事实上它与改稻为桑的失败本身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后面再细细地讲。
大明为什么会有财政亏空?
核心原因有两个:
一是底层生产不足。
封建社会个体经济容易破产,但凡遇上点天灾人祸,百姓就活不下去。而官僚地主,则可以趁火打劫,以低价贱买农民的土地。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变成奴隶或佃户,靠给地主种地或是租种地主的土地艰难维持生计。这样一来,农民大半劳动成果被地主拿走,剥削很严重,这种高强度的剥削之下,农民自己想要搞点扩大再生产,比如开点荒,置办点农具,买几头耕牛啥的都很难实现。封建社会,农民就是最核心的生产力,他们得不到发展,生产又怎么可能得到发展。土地兼并越厉害,农民就越苦,生产力就越不发展。生产力不发展,财政又怎么可能好起来呢?农民种不出那么多粮食,如何承担那么多赋税呢?
更不要说农民手里能有点余粮、余钱啥的,可以去市场换点或是买点东西了。农民太穷,商品没有市场,所以资本主义也很难自己发展起来。即使萌芽出一点商品经济,也都是些瓷器、古玩、丝绸之类的东西,只有官僚地主阶级消费得起。
生产不足,缴纳的税赋少了,财政就容易陷入困难。
二是上层贪墨挥霍无度。
《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第一集就开始算账,算亏空的账。去年一年,兵部修战船亏空300万两,工部修河堤亏空250万两,嘉靖修宫殿亏空400万两,这些都是大头,其他开支用度一算,全年超支1400万两。
这里面最有趣的是什么呢?是大家心里其实都很清楚,这些亏空里面有大量的银子都流进了官僚群体的私囊。而银子流进私囊的过程,又统统是在正当用途的旗号下进行的。谁能说修战船没有必要,谁又能说修河堤没有必要,即使给嘉靖修一座宫殿,那也是光明正大在搞。但奈何“光明正大”与私下搞钱绑定在了一起,事情就难办了。它形成了一个体系,任何事情只要经过这个体系运转一遍,都得先被扒一层皮才能办成。这个官僚体系里面,除了从财政收入上搞钱之外,最方便也最有利的渠道,其实是通过财政支出来搞钱。因为从财政收入上搞,太明目张胆,容易暴露,但是从财政支出里面搞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些支出很多都可以打着为民生的旗号来进行,比如里面修河堤,造战舰,哪一项不是为了人民。有这个旗号做掩护,一俊遮白丑,搞起钱来自然就安全方便多了。
嘉靖修一座宫殿耗费了700万两,下面一品二品大员,给自己建一座宅子,花个几十万两不过分吧。没有这些亏空,小阁老的宅子和9个老婆自然也就没有着落。
财政亏空,国库没钱,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即使嘉靖的宫殿不修了,小阁老的老婆不要了,其他各种公共开支也难以缩减。底层官吏的薪饷要发,沿海抗倭的军饷要发,这些都没法缩减。
怎么办?
在这种背景下,嘉靖与内阁一起搞出了一个“改稻为桑”的办法。
二、
改稻为桑
从改稻为桑的逻辑链条来看,这个政策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的丝绸有海外市场,国内一匹丝绸卖6两银子,出口到西洋就能卖15两,中间差价都有9两。这里咱就不考虑航运成本、出口风险、贸易战之类的东西了。总之,这剧的设定是海外市场能消化50万匹丝绸,咱就按这个设定来。
50万匹丝绸,就能比以前多赚450万两。嘉靖去年修完了宫殿,今年也就不会再修了,这又减少了一笔700万两的专项债支出。所以,只要改稻为桑搞成了,就能大大弥补财政亏空。
这个想法是没问题的,既然在原有的个体小农生产力的基础上,已经不能再增加赋税,那就搞点丝绸这类当时的“新质生产力”,然后出口赚外汇,借以弥补财政亏空。要是搞得好的话,还能吃到技术红利,甚至还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式的规模化生产创造了条件。这事怎么看都没有坏处。
可是要多搞丝绸,就要多产桑叶,多种桑苗。所以严嵩提出把浙江一半的农田改为桑田。
于是问题就来了,个体小农基础上的生产力十分落后,一年产的粮食也就勉强糊口。你把他们的土地都改种桑苗了,那农民吃什么呢?
严嵩又提出了解决办法,种桑树的经济效益比种粮食相对高,农民可以把种桑树的收益拿到米行上换取粮食,按正常市价,比自己种粮食还能多结余点。农民虽然没什么余粮,但是地主、米商手里有啊。只要丝绸有市场,农民种桑树的收益得到保证,那逻辑上就没什么问题。
在这个政策里,国库可以在6两一匹的基础上,再额外多赚9两的差价。50万匹凑齐的话,就额外多赚450万两;丝绸商虽然没赚到这个差价,但只要有市场,能多产丝绸,即使他们只能按照原来6两的价格出售,也是赚的;农民种桑树的经济效益高于种粮食,哪怕多结余一点也是结余,看起来至少不吃亏。
这事是嘉靖急于推动的,严党也指望着办成这事来堵清流们的嘴,下面的一众官员,想着可以从中捞取油水,商人代表们能扩大市场多产丝绸多赚钱。即使清流派在后面使点绊子,也绝不可能凭他们的力量就能阻止这样的国策。
所以当杭州知府马宁远在推动改稻为桑政策,受到农民阻碍的时候,就发出了灵魂拷问:“改稻为桑是国策,上利国家,下利百姓,天大的好事,为什么就推行不下去?”
想了半天想不到农民反对的原因,于是他只能得出一个答案:一定是有倭寇这样的境外势力煽动民众,对抗大明国策。所以他把带头闹事的齐大柱给抓了起来,罪名是通倭。

大家不要觉得好笑,如果不是胡宗宪保下来了,那几个带头闹事的村民,当晚就得被就地正法。
那这里面的问题到底出在哪?村民为什么一开始就反对改稻为桑?
原因很简单:虽然村民们不了解什么是国策,也不清楚里面有些什么猫腻,但是他们很了解常年骑在他们头上的官僚和地主。
一旦他们把秧苗拔掉,改种桑苗,秋收以后就没饭吃,而这时候的桑树嫩叶还换不到粮食。这也是小农生产的严重弊端,生产力落后,地主盘剥又严重,多数农民家里没有余粮,都指望着当年那点收成吃饭。所以历朝历代对土地上改种经济作物都慎之又慎。
尽管官府承诺从官仓里面借给他们粮食,等他们的桑苗长成了以后再还回来。但到时候官府借不出来粮食怎么办?饿着肚子的农民能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时候地主、官商们趁着农民饿肚子,低价贱买农民土地,那农民是卖还是不卖?农民土地一卖,以后不更是任人宰割吗?
事实证明农民的想法完全是正确的。胡宗宪当晚一问官府调了多少粮来改稻为桑,结果是其他省份调不出来,米商也不愿借粮。如果真照原来那么去改,秋收以后农民就吃不上饭,到时候要么出反民,要么大片土地被兼并。
为什么其他省份不愿意借,当地米商也不愿意借?
当地米商不愿意借很容易想明白。一旦农民秋收后没有粮吃,他们就可以囤积居奇卖高价,甚至可以趁机贱买土地。这发财的机会他为啥不要?更何况,米商把粮食借给官府,中间也存在诸多变数,万一官府还不上,米商又能去找谁?你贪图官府那点利息,人家搞不好要吃你的本金。
其他省份自然也有同样的顾虑,你借了不还咋办?此外还有另外一个特殊原因,清流派不希望改稻为桑成功,想借这个机会扳倒严党。因此给邻省打招呼了,后面赵贞吉不借粮就有这个原因。
但是如果问题只停留在这里,那么改稻为桑就还不是死棋,就还有机会……
三、
事缓则圆?
对于一个封建专制体制来说,虽然民众的民主权力很有限,但这种体制也不是全无好处。至少它在对地方的掌控,皇权意志的贯彻等体现集中优势的方面,都相对更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专制体制也一样,在某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领域,某些需要集中管控的领域,这种集中就会更有优势。但是因为专制、监督环节薄弱,由此带来的缺点也很明显。
封建专制下,嘉靖想要实现邻省调粮,严禁米商抬价,甚至强令米行借粮,都是行得通的。这一点,从胡宗宪延缓改稻为桑的计划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晰。他给嘉靖上奏折,让皇上下令从邻省调粮,又用浙江官府的名义强令从米行借粮,并不准米商抬价,违者以囤积居奇治罪。从胡宗宪这一系列操作看,借到粮食,保证改稻为桑的农民秋后有粮,在实践中是可以实现的。我们把方案设计得再人性化一点,先把借来的粮发给农民,然后再由官方秋后按市价收购桑农的桑叶或生丝,如未能按市价收购,则农民所借之粮无需偿还。这样一来,地还是农民的,农民改稻为桑零风险,还能增加收益,推行起来农民自然不会反对了。
只不过那么搞,速度就慢得多了,只能借一点粮,改一点地。想要一年完成50万匹的任务自然是不可能,不过好歹也是一个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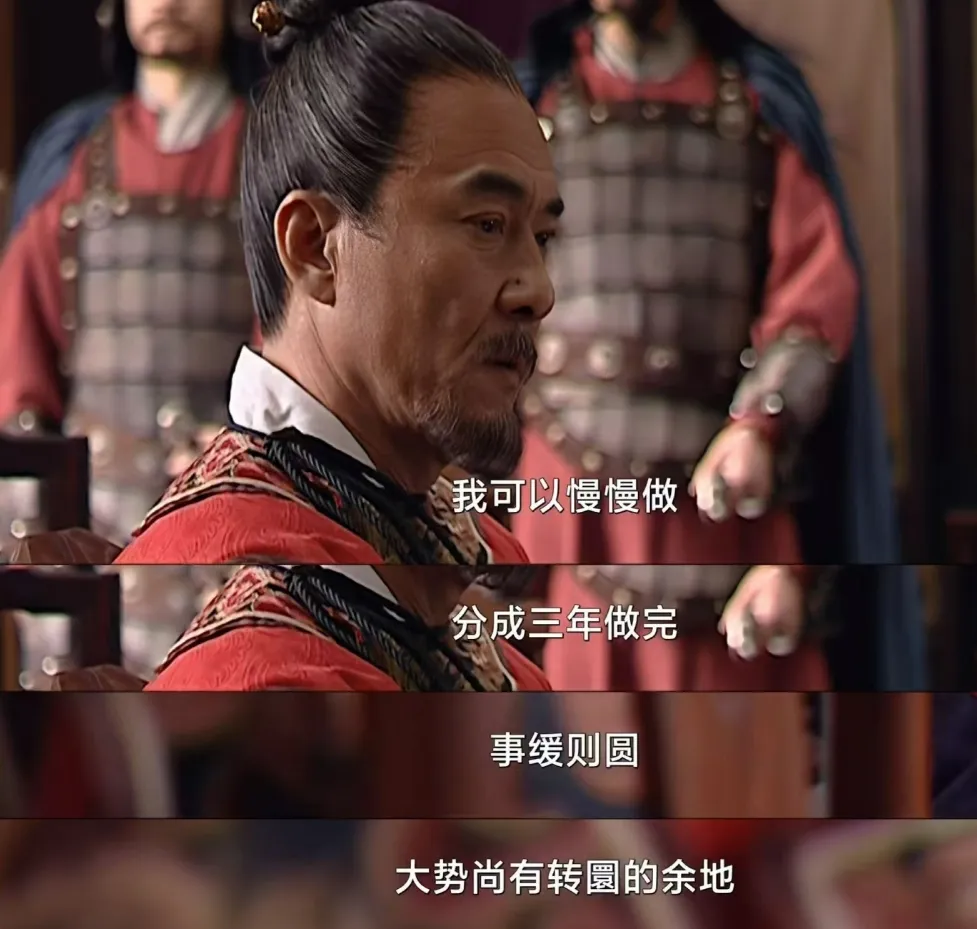
但是按胡宗宪这个搞法,官僚和地主想要兼并土地的愿望就落空了,不但兼并土地的愿望落空,压榨桑农的希望也随之落空。因为如果土地在地主手里,他可以把桑叶价格压到很低,他可以雇佣农民来干活,而且能做到统一耕种,统一收购,反正都是自己的,还需要跟农民讨价还价吗?当然不需要。
可是如果土地还是农民的,农民手里又有了粮,这事情就不好办了。大户想收购,收购价格和收购成本都要增加,尤其是收购价格。即使你提前约定一个市价,但是农民仍然有可能拿这个价格和其他作坊比价。总之那么一搞,不确定性就从农民身上转移到了大户身上。
杨金水、郑必昌、何茂才等一干人既不想等那么久,更不想给农民让利,各个都急着借改稻为桑的国策搞政绩,捞钱,于是便有了联合商人大户沈一石,指使杭州知府马宁远毁堤淹田的丧心病狂之举。
他们原本以为把河堤炸了,把田淹了,老百姓又没了粮食,他们就可以趁机用低价买田,淹田的事到时候给上面报个天灾糊弄过去也就是了。大户买了田,种上桑苗,改稻为桑这事也就顺理成章的办成了。然而这么一干,又容易制造出一批反民。那时内有民变,外有倭寇,浙江又是纳税大户,一乱起来,就不是改稻为桑那点收入能弥补得了的了,更何况这还动摇大明的根基。
很多人看到这里,就很容易认为,改稻为桑这事儿全赖这几个丧心病狂的官僚和大户。他们不那么着急,不那么贪,肯缓一点,肯让渡点利益给农民,改稻为桑这事就能成。
按照这个结论,只需要让胡宗宪来全权负责,嘉靖给他撑腰,再来几个像海瑞、王用汲这样的清官,事缓则圆,时间缓上个几年,哪有办不成的事?
胡宗宪一开始是这么想的,海瑞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很多看这部剧的人也是那么想的。
如果这部剧的结论仅仅是这样,那它连一部三流剧都算不上。
《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把改稻为桑这事各个环节都说透,说穿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论证改稻为桑这步棋,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是一步死棋。
四、
已经烂了
说郑必昌、何茂才这样的官员贪墨无度,说沈一石这样的官商利欲熏心都没错。但如果以为把他们换掉事情就能解决,那就实在太高看他们了。
之所以有改稻为桑,一开始就是为了补朝廷的亏空,这一点很重要。跟外商谈好了50万匹的生意,为了能年底交货,所以才那么着急把浙江一半的稻田改为桑田。
一匹丝绸国内市场是6两银子,出口海外是15两,中间的差距9两都得用来补亏空。所以,这50万匹丝绸一共可以卖出750万两银子,但其中的450万两都得上缴国库。而国库的亏空是怎么造成的?是整个上层建筑里的官僚体系造成的,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嘉靖、严党只不过是这个官僚体系里的一个代表罢了。官僚们在这个他们自己构建起来的系统里面,通过一项项国库开支,打着修河堤、修公路、修花园的旗号,在花钱中搞钱,贪墨挥霍。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私人发了大财,但国库却落下了巨大的亏空。
所以,这450万两的差额,换个角度看,是整个上层建筑的官僚体系要瓜分的利益。而且,还是他们不得不分的利益,否则就补不了亏空,亏空补不了,就会威胁嘉靖的统治,也威胁整个大明的统治。这可不是随便换另一个人来就能解决的。
到这里,问题都还不大。我们上面说了,即使按6两的市价,丝绸商还是有得赚。但是,这一匹丝绸6两的银子里面,作为大户的沈一石又能拿走多少呢?按照后面从沈一石家里抄出来的账本和信件交待:20年里,他一共织了400余万匹丝绸,其中210万匹上缴朝廷,100万匹被各级官员分走,他真正用于维持丝绸行运营的利润,实际上仅仅是90余万匹。换句话说,一匹6两银子里面,他实际上能分到的还不足四分之一,也就是最多1.5两,这还得包括各项成本在里面,他自己还要从这1.5两里面赚钱。

而这次改稻为桑,要新增30万匹丝绸,就需要多有50万亩田地的新增投资,以及新增织机。单说这50万亩田地,即使按照正常灾年30石粮食一亩的价格来买,也需要1500万石粮食。如果是按照丰年40-50石一亩的价格买,则花费更多。郑必昌、何茂才估算过,1000万担粮食就需要大概700万两白银,那么1500万担粮食,就需要1050万两白银。沈一石前半生一共干了20年,能落到他手里的,按营业额算总共才600万两,营业额里还要除去人工、生丝、纺织机等各项成本,他哪来那么多钱买按正常价买田呢?
从后面抄沈一石家的情况来看,他这20年积累下来的资财,就是那180万石粮食,这些粮食折合白银大概126万两左右,加上家里剩下的现银1万多两,一共就是127万两白银。这当然也是一笔很大的钱,但是相对于要执行改稻为桑的花费来说,就远远不够。
即使假设他联合其他织造商凑钱一起买田买织机,一匹丝绸分1.5两,还要除去生丝、人工、织机等成本,那么一年出口50万匹丝绸,到他手的利润能有50万两也就顶天了,事实上还不可能有那么多。如果按照正常价花1050万两去买田,他20年都回不了买田的成本。这事还怎么干得下去呢?更何况,这种利润的生意,他又上哪去找人凑这么多钱呢?
所以,要想改稻为桑,就根本不能按照正常价购买农民的田,得极限压榨,极限兼并。就是按照他说的10石一亩,8石一亩的贱价(这个价格农民很可能要饿死),对沈一石来说,仍然感觉困难。这里面原因是那样的简单透彻:官僚系统吃得太多了,官僚系统吃完,沈一石自己也要吃,最后只能通过极限兼并和极限压榨,把成本转嫁到农民身上。
可以想见,在这之前的20年里,如果沈一石不是和官府的人一起靠着贱买田地,低价收购生丝,极限压榨雇农,把利润建立在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上,织造局可能早就被吃破产了。
所以到这里原因才真正浮出水面,为什么说改稻为桑从一开始就是一步死棋,换了谁来都没用,胡宗宪不行,海瑞就更不行了。就是因为在这个已经形成的官僚体系里面,利益分配结构已经锁死了。在这个分配体系里面,你不贱价买田,不低价收购生丝,不极限压榨雇农,这事就根本没法干。
然而真那么干了,那么即将出现的另一个局面,就是胡宗宪说的,浙江多出30万个反民。
固然,你换了胡宗宪、海瑞来干,他们是清官,他们可以不拿。但是他们两个清官,能不能制止嘉靖不拿?能不能制止严党不拿?能不能制止各级官僚机构不拿?补国库亏空这事,本身就是在帮着整个官僚系统搞钱,你一两个清官不拿,又能给百姓减轻多少负担呢?
后来郑必昌、何茂才感到危机不远了,哪里还有半分心思放在搞钱上,只想着能保命就不错了。但还是同样的道理,就算他们两个不拿,又怎么改变得了整个织造行业里的利益分配结构呢?
所以,改稻为桑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改不下去,要么改出一堆反民,两者必居其一,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中间余地。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评论功能已恢复开放,请理性发表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