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李北方新书《北大南门朝西开》收录了他近几年的各类作品,对于当下社会的反思,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视角。如今,许多人提起“新工人”都会将其与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结合起来,甚至有人提出《劳动合同法》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李北方从更为底层的视角,为我们做了诠释。“新工人”是一个较于“老工人”的概念,要明白谁是新工人,得先看谁是老工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此宪法原则在法理层面规定了中国的国家性质,但现实的情况远为复杂。市场化的浪潮冲击了每一个人,总体而言,工人在利益上承受的损失是最大的,表现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急剧下降。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工人研究领域也悄然退场了,事实也大部分如研究者所看到的那样,工人不是一个有着同一性的“阶级”,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庞大的“群体”。
老工人的美丽传说
中国革命和建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主要依靠力量是农民。这并非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引的方向,但建国后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指导思想。同时,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国家建立了一整套工业体系,创造出了一个“工人阶级”。黄纪苏对此有精辟的概括:“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
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由此导致了诸多“名”与“实”的矛盾之处。《新华字典》对“工人”的解释是:“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以工资收入为主,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这一定义无疑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做出的,描述的是伴随资本主义市场化进程和“人的商品化”趋势出现的、作为私人资本或私人资本家阶层的对立面存在的“工人”。
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人”不符合这一定义,他们不是市场化进程的产物,是政治进程创造了他们。老工人虽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但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一样的,都以生产资料的主人身份出现。通过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国企管理体制,老工人和干部阶层被尽可能紧密地捏合在一起,在生产中锻造出了某种程度的“主人翁”精神。在后来的国企改制过程中,老工人们往往将国企管理者的腐败行为斥为“败家”,即是这种精神的回响。
老工人的生活方式是对“人的商品化”的反动。王绍光将1949年至1984年这一历史阶段的经济模式概括为“伦理经济”,即人的经济生活服从于人生存的伦理准则。通过单位体制,老工人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单位既是工作的场域,也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依托体。
政治进程可以造就老工人,同样可以摧毁老工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掩盖了工人的实际政治影响力和工人真实的集体意识,随着意识形态取向的转变,老工人与干部阶层表面上的平等瞬间就消逝了,国企管理者迅速将对国有资本的管理权变现为剩余索取权,以不同的形式成了改革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李静君将这种管理模式称为“混乱的专制主义”,老工人的反抗则表现为“集体懈怠”,以出工不出力、偷懒、自发停工、旷工等方式抗争。这无疑会导致国企效率的降低,低效则为激进私有化提供了借口。
在私有化过程中,老工人则被无情地甩了出去,有的下岗,有的被迫适应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人和干部共同参加生产和管理的一页被翻了过去,有趣的是,正是在翻页的过程中,工人才意识到“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含义,才寻找到了集体认同,但为时已晚。
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取向是平等,然而其现代化建设方式却创造出了新的不平等。老工人在工资之外,还享有住房、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的福利,乃至稳定的可以传承的工作权利。工人出身意味更多的社会机会,更不消说“工人老大哥”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总体上,工人的处境要远远好于农民,在这个意义上,“工农联盟”只是一个宣传上的幻像,而非对实际政治结构的客观描述。
在老工人群体的内部,不平等也是存在的,有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和集体企业职工之分,后者在福利待遇上稍有逊色。这种不平等在当时是不明显的,到了国企改制阶段才表现为在工龄买断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区别对待,成为改制过程中对工人分而治之的手段。
被商品化的农民工
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分割不是绝对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部分农民得以通过招工的形式转变为工人。这与后来的进城打工不同,成为工人即享受工人的一切待遇,是一种身份的彻底转变。此外,农民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参与工业生产,即在地方集体办的企业里做工,但不改变身份。在计划经济时代末期,中国的化肥产量有一半由农村地方工业贡献,也就是乡镇企业生产的,1970年代中期,几乎每个县都有上百家生产数百种不同产品的小工厂。据此可见,参与工业生产的农民为数众多。
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勃兴开辟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作模式,农业生产的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化为乡镇企业的工人。至今仍有论者认为,乡镇企业是真正具备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可惜的是,19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逐步被政策放弃了,为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让路。
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分割和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为后来的大规模使用农民工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条件。首先,农村的境况大幅落后于城市,这个对比在1990年代以后愈发地明显,以至于农民进入城市打工,无论如何都是向上流动,中国农民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性在此激励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其次,1980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虽然促成了农业生产效率的增长,但代价是集体主义的瓦解,这深刻地影响了农民的行为模式。早期农民外出务工有不少结伴同行的情况,这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在市场中的博弈能力,集体主义瓦解后,大量农民工只能以原子化的形态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契合了资本积累的需要。
农民工是市场进程创造的,但农民工也不符合字典上“工人”的定义。农民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即土地,早期绝大多数农民工是一个人外出打工,其他家庭成员在家务农。他们将打工视为阶段性的选择,期待一旦赚够了盖房子或其他某种特定用途的钱,就回到家乡,继续在土地上讨生活。这种心理导致了外出务工者省吃俭用、将打工所得尽可能地寄回家的行为模式,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的巨额汇款对缓解地域差距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在上个世纪末期曾经是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在市场经济时期,生产的目的是资本累积,这与“伦理经济”时期以满足人的需求为首要生产目的是截然不同的。这决定了农民工的地位与老工人天壤之别,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成为市场上的商品,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民工则作为“廉价劳动力”,被经济学家们视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所谓“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等贸易形式正是建立在对这一比较优势的理性利用之上的。
在“效率优先”主导的时代,中国极度缺乏社会保护政策,人和自然环境都成了资本积累的工具。在微观经济层面,企业的目的获取最大利润,提高利润率的方法之一即是控制成本——人力成本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于是,压低农民工工资甚至大面积拖欠农民工工资成为普遍现象,这才出现了总理替农民工讨薪的事情,甚至使用“奴工”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劳动保护措施的匮乏导致了一代农民工为经济发展付出了血与泪的贡献,有估算认为,在1993-2002年间,有5-7%的农民工因工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且未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新一代,新挑战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水平应以足以支持劳动力再生产为标准,这是一个硬约束,因为工资若是达不到这个标准,劳动力再生产就会在萎缩的条件下进行,长此以往会危及整个经济。劳动力再生产的内容不仅包括劳动者自身的吃穿住用,也包括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等家庭开支。
农民工在老家有一片土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身份只是“半无产者”,其劳动力再生产一部分成本由土地承担了,理论上,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工家属也间接地受到资本的剥削。这是农民工可以承受低工资的奥秘,中国因此成了资本的天堂,博得了世界工厂的虚名。
现代化意味着减少农民,但是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农民的数量持续增长。这表明,风风火火的城市化并没有安置城市的建设者。不少人是希望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的,即继续把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丢给农村,维持现有的资本积累方式,但他们同时又把目光盯在农民的土地上,希望把土地的资本化作为下一个增长点,仿佛没有意识到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成立的。
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变化,最显著的是代际更替。研究表明,跟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呈现以下特点:保持了吃苦耐劳的特性;接受教育程度更高,薪资水平却更低;已经结婚的新一代农民工往往夫妻双方全部脱离农业;完全不懂务农,回归农村已经不可能;遭遇不公正时,反抗的倾向更强烈;等等。
这一代农民工夹在城乡之间,既有的经济模式下的收入无法支持他们在城市定居,成为新市民,有调查结果显示,40%的打工夫妻不得不各自住在宿舍或工棚,因为工资水平负担不起租房的费用;回到农村也不可能,甚至有些人的土地已经因为流转或征地而失去了。无论如何,靠农村承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已经无法维持。他们怎么办?这是中国社会亟待回答的问题。
这个庞大的人群暂时还是沉寂的,尚未形成集体意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表达的渠道,几年前产生的几个农民工人大代表无非是个点缀。他们最常用的反抗形式是“用脚投票”,频繁地更换工作,但这使得对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形同虚设,最终结果是有利于资本。极端的反抗是以死抗争,富士康“连跳”事件是对农民工经历的非人性化的境遇最振聋发聩的控诉,旋即却又归于死寂。
谁是新工人
“新工人”这个概念越来越多被使用,但还不是一个规范性的理论范畴,不同的人用“新工人”指代不同的人群。那么,谁是新工人呢?
潘毅曾提出,新工人包括农民工、国企下岗工人、国企转制工人。有数据显示,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从1995年的7544.1万人减少到2007年的2382.1万人,差额为5162万人,这五千多万人即为下岗和转制工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方式类同于进城的农民工,又与农民工存在着直接的竞争,他们在吃苦耐劳方面显然略逊一筹,对农民工抢占工作岗位、拉低工资水平多有抱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基本在城市里有自己的住房,具备在城市长期生活的基本条件,这是农民工无法企及的。
但是,如果以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人为参照,那么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工人都是“新工人”,因为计划经济年代无法复制,老工人的社会地位同样是今天的国企工人无法比拟的。高收入的国企职工集中是个别行业和特定的岗位,并非一线工人,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1979年,这一差距仅为1.18倍。今天的国企已经蜕变为纯粹的营利性机构,管理方式上与私营企业的差异渐趋雷同,两千多万国企工人已泯然众人矣。
还有一部分论者口中的新工人仅指农民工。他们主张用新工人这一称谓的理由是,为农民工争取产业工人应有的地位,同时也是要打消一些人对农民工还能回到农村的幻想。潘毅的论点比较精确地概括了这种倾向:研究农民工是要解体农民工,让农民工可以真正转化变成工人。
也许对“新工人”进行界定并非紧要的任务,紧要的是认识到工人群体分裂和孱弱的现状,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他们的境况得以改善。而最急迫需要面对的,正是农民工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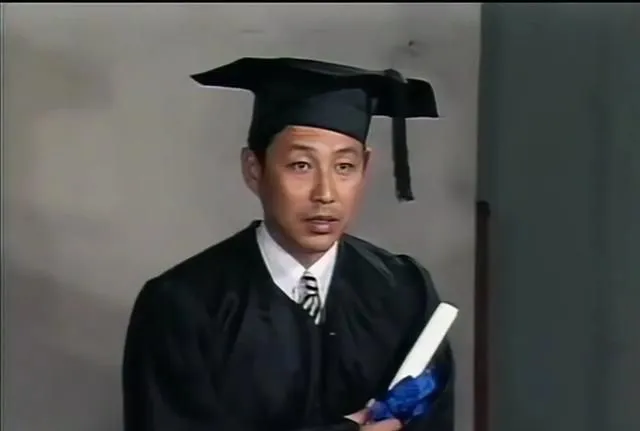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微信或手机浏览器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