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李大钊开革命史学之先河
--纪念五四文化革命一百周年
--纪念李大钊殉难赴义92周年
龚忠武
【作者注:为了纪念李大钊对五四文化革命的贡献,作者已经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三家文斗,仁者无敌》,二是《试论李大钊的精神和业绩不灭论》。本文是第三篇。之所以如此,旨在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地彰显李大钊在五四文化革命中占据的独特的历史地位。】
题旨:李大钊开革命史学之先河
五四文化革命时期,作为其主将陈独秀、鲁迅、胡适之外的另一位主将李大钊,除了参与文学革命、道德革命、史学革命之外,还作出独特的贡献,就是引进阐述马克思主义,宣扬列宁主义主导下的俄国大革命,开创革命史学之先河,为学术与政治之紧密互动、史学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开辟广阔的道路。
史学革命与革命史学,同中有异;史学革命的旨趣在于批判中国传统的史观、史学也即编纂史学historiography,批判以《春秋》为代表的道德史观和等级(非阶级)史观,是一种静态的纸上谈兵的史学思想革命。而革命史学,则在批判儒家治史方法和等级史观的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将学术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紧密结合,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付诸革命实践,直接主导这种革命的进程,也即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成为动态的革命史学;质言之,就是来自感性的实践,上升为理性的理论,再回归实践,成为动态的循环反复的过程,从而与史学革命同中有异,界划厘然有别。
史学与世变:以史救世
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和历史学发生这样重大的变革,绝非偶然,而是时势促成的;存在决定意识思想,而不是相反,所以史学革命和革命史学的产生,只是五四时期内外交困的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在史学领域的一种折射而已。
当然,这也与中国的史学传统密切相关,中国是个具有深厚史学传统的人本文明,不是神本的文明;前者以史为鉴,从而产生史学,后者以神启为鉴,无需史学;(1)每逢乱世,受中国人本文明熏陶的、忧时伤怀的思想家,当然不会像神本文明的人一样向超自然的神灵求助,(2)而是试图从以往圣贤的治国理政的经验也即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寻找知识、经验、智慧,找出良方对策,以济时救世,安邦定国;所以这时史学随之成为显学。
最好的例子就是生逢乱世的孔子,著《春秋》,旨在从道德史观出发,借「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的书法,来端正当时的政风习俗,以使乱臣贼子心生畏惧,不敢造反,从而达到拨乱反治、政治清明的地步。(3)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汉司马迁的《史记》(4)和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5),目的都在让当政者以史为鉴,正己正人,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
到了近代,是一个较之春秋战国更加动荡不安的乱世。所以时代又将史家推到了时代的前端,史学与政治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首开其端的是梁任公,一位对旧史学富有深厚造诣、笔端流露浪漫诗意激情、普受尊敬的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将这个道理,用夸张的笔调,讲得十分透彻。他在1902年发表的名著《新史学》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强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肯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飢食,乙刻不容緩者也。然徧覽乙庫中數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吾所欲,給吾所求者,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6)
任公所谓的「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简直到了把史学革命看成是唯一的救世良方, 万灵丹了;虽然语或夸张,但足见其重要性,遂成显学。质言之,梁的这段话点明了历史学的时代任务:即史学救国。
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旧史学不但无助于实现此时代任务,反成为一种包袱,所以史学本身必须进行一次革命性的大转变,因此任公提出了史界革命,也即在方法上和史观上进行一次革命;任公在其《新史学》一书中,对旧史学进行淋漓尽致的激烈批判,概而言之有四大弊端: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7)
由此又衍生两种毛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有此六病,令人在读旧史时,又产生三种恶果:
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弹。前既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然则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职此之由。(8)
所以,必须痛下针砭,对旧史学进行改造,从而开「新史学」风气之先,启动建立「新史学」之进程,即进行任公所谓的「史学革命」。李大钊是任公的后辈,只小任公十三岁,可以视为同一时代的人,所以具有同样的时代感。例如他在《狱中自述》中就自承早在青年时期,深感「国势之危迫」,遂立志救亡图存、脱民水火,于是「亟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好学的他,肯定读过任公之《新史学》,因而受到任公史学救国、史学革命思想的启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而从事史学研究,以挽狂澜,实现急迫的时代救亡任务。(9)
所以,对于任公指出的旧史学的弊端和恶果,李大钊当然完全同意,例如他说:
中国旧史,其中所载,大抵不外帝王爵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而于社会文化方面,则屏之弗录。(10)
这和任公基本上是一个调子。但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的李大钊,1924年,他进而据此为历史下了这样简明扼要的定义,历史是:
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11)
即历史是已经发生或正在进行的人类活动。他进而将这种历史和历史记录作出区别:
「(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12)
「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连续,是人类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
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象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纪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这活的历史,固屹然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而有他的永续的生命。(13)
到这里为止,李大钊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看法,基本上同任公保持同调,唱和任公《新史学》中对旧史学批判的基调。
开革命史学先河
这是史学革命时期,对史学研究在方法上和史观上,作革命性的探索;但是一旦有了良策,自然要知行合一,从静态的书斋走入动态的社会,将研究结果付诸实施,见诸革命实践,为革命服务,(14)遂进入革命(的)史学时期,开动态的革命史学的先河,适与梁任公开静态的史学革命之先河,前后相映成趣!也反映了梁、李两人--一个是史学革命家,一个是革命史学家--的个性、志趣、立场和时代任务的不同!
李不但是一个革命史学家,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学家,所以他对历史记录的选材取材的角度,又与史学革命家梁任公大异其趣;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记录的取舍:
历史原本就是人类活动的记忆记录,但是记什么,不记什么,是随立场、观念、价值而有所取舍选择。李大钊自从公开声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史学观,成为革命史学家后,史学对他就成为革命工具、斗争武器,必须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所以史学要从记录的任务功能上发起革命,就得记载「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是人类活的变迁(变革)」,所以他讴歌「庶民的胜利」:
我們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鬧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
是那一个?我們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講一句話,
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
一国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庆祝,不是
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界的庶民庆祝。……
……。我們国內的战爭,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爭。結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敗。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結果,是資本主义失敗,劳工主义战胜。……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漸有和他們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終。这新紀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資本主义就是这样失敗,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間資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責本家的資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繼袭,就是靠着資本主义經济組織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这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15)
所谓庶民,就是劳工大众,就是普通人,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人民。在中国的正史传统例如二十四史中,像这样反压迫造反的事,循例被视为大逆不道,罪在不赦,而在李的眼里,却是高尚的义行壮举!
基于同样的原因,李也高度赞扬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动的群众或庶民运动:
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謠。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紛紛戍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革命。象这般滔滔滾滚的潮流,实非現在資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紀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間一有动蕩,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嗚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間,历史土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貴族咧、軍閥咧、官僚咧、軍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一一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挾雷霆万鈞的力量摧拉他們。他們遇見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過見凛冽的秋风一點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弛。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声。人道的警鐘响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6)
于此可见,李大钊和梁任公虽然都主张史学革命,都主张以史学革命救国,但由于两人的立场、史观、个人性向、治学方向不同,所以大异其趣;任公止于史学革命,而李却更进一步,构建革命史学。
这是史学革命家梁任公绝对不会做的,甚至认为过激而极力加以反对的。
发现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或范畴
梁任公认为历史是探讨人的事,而人是感情的动物,其思想心绪多变,难以度测,所以很难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史蹟所以詭異而不易測斷者:其一,人類心理,時或潛伏以待再現。凡眾生所造業,一如物理學上物質不滅之原則,每有所造,輒留一不可拂拭之痕跡以诒諸後。但有時為他種勢力所遮抑,其跡全隱,淺見者謂為已滅;不知其乃在磅礴鬱積中,一遇機緣,則勃發而不能復制。若明季排滿之心理,潛伏二百餘年而盡情發露,斯其顯例也。其二,心的運動,其速率本非物的運動所能
比擬。故人類之理想及欲望,常為自然界所制限。倘使心的經過之對於時間的關係,純與物的經過同一,則人類征服自然,可純依普通之力學法則以行之。惟其不能,故人類常感環境之變化,
不能與己之性質相適應。對於環境之不滿足,遂永無了期。歷史長在此種心物交戰的狀態中,次第發展,而兩力之消長,絕無必然的法則以為之支配。故歷史上進步的事象,什九皆含有革命
命性;而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後之史蹟,皆最難律以常軌。結果與預定的計書相反者,往往而有;然不能因其相反,遂指為計畫之失敗。最近民國十年間之鑒史,即其切例也。其三,人事之
關係既複雜,而人心之動發又極自由;故往往有动机極小而结果巨大者,更有結果完全舆動機分离而别进展于另一方向者。(17)
与此可见,任公虽然力倡史学革命,但却陷入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的陷阱而不能自拔。李则反之,认为有规律可循,例如辩证唯物史观对历史运动的结构,就可以发现像自然科学公式般的规律,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转而反作用于下层的经济基础,是为主观能动性的反作用力效应;简称为「上红下专」公式。由于涉及到革命史学的基本理论,值得详为引述如下,以资论证: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
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前者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內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
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来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18)
上述论点可以简化为下列公式:
下层的物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的意识形态(哲学、宗教、艺术、道德、政治等)。(19)
但必须强调,这种上下关系是辩证的,不是机械的,所以上层建筑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下层经济基础,推动历史前进:
下层的物质(经济)基础←上层的意识形态(哲学、宗教、艺术、道德、政治等)(反作用于)。(20)
合成一条公式则为:
下层经济基础 (决定) → ←(反作用)上层的意识形态
这就构成了革命历史学理论结构的有机互动的整体关系。这是李大钊有名的「上下」思维模式或范畴,也可视为李大钊革命历史学的思维范模式或范畴。
对李大钊而言,这是唯物辩证史学发现的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用来解释说明古今中外的所有历史运动。此外,还有与之密切相关的阶级斗争说和剩余价值说等,但此非本文的主旨,故从略。
这个认识,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一般常识,但在当时,对急于寻找救亡图存真理的少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不啻是一次中国史学上、石破天惊的大革命,使他们由此找到了开启救亡真理大门的钥匙。
而且,从长远的意义来看,这个思维模式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因为唯物史观从此将今后中国文明的发展置于稳固的科学和物质基础之上;因为,在儒家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之下,经由儒家主张的求圣的不断内在超越,尽量发挥精神力量,以推动历史发展的理路,已经在近代将中国文明的命运逼进了死胡同,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国古文明在近代备受摧残的噩运,充分证明了没有近代物质基础的精神力量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缺乏抗压力和承受力。
然而,在上(红)下(专)的思维之下,经由求专的不断外在超越,尽量发挥生产力,以推动历史前进,则将中国的文明建立在无穷尽的强大而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于此可见, 这种唯物辩证史观对中国文明的新生及其未来的命运是多么重要。由此足证,五四文化革命时期,李大钊开创的革命史学,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超过备受后世赞誉的文学革命、道德革命。可惜至今一直未受到史学家应有的重视,总爱夸大陈独秀、鲁迅的思想革命、胡适的文学革命对五四文化革命的贡献,至少也应当等量齐观。
但是,这种唯物辩证史观对美国杜威主义的信徒如胡适而言,却是不能理解的;胡适同梁任公一样,对历史采取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无法用人的意志来加以操纵控制的,不承认历史中有什么规律、法则。所以,当胡适说历史是一连串偶然事件造成的,又说历史像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也就不会令人感到大惊小怪了。
根本改造论与点滴改良论:问题与主义的辩论
--中国社会的方向、道路的辩论
1917年至1919年发生于李大钊和胡适之间的关于「主义与问题」的著名辩论,涉及到革命史学中从理论到实践的大问题,因为革命史学的精髓是实践,是改变旧世界,构建新世界。这是当时的思想界和政治人物,面临的最大的时代问题。但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着手?(21)
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的各个思想流派都有自己的看法,甚至左翼流派中的看法也没有共识。李大钊坚定地认为,必须从事根本改造,对中国社会来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也就是一场从体制、思想、社会的全面的大革命。
就这个问题,李大钊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同胡适代表的杜威主义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辩论;单从思维方式上看,这是一次马家的唯物辩证思维和杜家的美国实用主义唯心形式思维的辩论。
这次论争是由胡适挑起的。1917年 7月,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指名道姓地攻击社会主义: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言。(22)
事实上,马家信徒更强调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所以这不是两家争论的焦点,争论的焦点是两家思考问题的方式。胡适所根据的是「点滴改良论」,本此方法,他将人力车夫这类具体的社会问题孤立起来看待,不去联系造成这些问题的外部原因,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
胡适说不谈主义、学说,而杜威的实用主义就是一种主义和学说,所以这场争论本身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胡适借此论争反对革命,鼓吹改良。因此,他还特别请他的老师杜威亲自来中国助阵(23)。同时,英国的思想界权威罗素,也被张东荪请到中国来从旁助阵,鼓吹改良的社会主义,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24)。
这时,李大钊已经走出唯心论的进化论、民主主义,改信马克思唯物主义了;作为马家的鼓吹者和代言人,他对他的朋友胡适这种指名道姓的挑战是绝对无法坐视不理的。1919年8月,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写道:
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它们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 、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25)
这就是李大钊著名的“根本解决论”,它联系了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从整体看待问题,因此与胡适的“点滴改良论”,针锋相对 。
值得强调的是,李大钊所用的这种唯物辩证思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与孔丘主义的唯心辩证思维,格格不入;但实际上,两者相反而相成。前者可以简化为上下思维,即下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意识形态,上层意识形态再反作用于下层建筑。后者可以简化为内外思维,即内在道德精神世界决定外在事物世界,外在事物世界再反作用于内在道德世界。例如,孔家的经典《大学》中说:
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内圣而后外王,外王再促进内圣(26)。同样地,根据上下思维,可以得出:下专而后上红,上红再促进下专(27)。于此可见,两者基本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互容互补的。李大钊通过唯物辩证法间接地对孔家唯心辩证思维方式的改造,正如同马克思改造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一样,将它颠倒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维持辩证的形式,但将内在的道德世界换成下层的经济基础,将外在的事物世界换成上层的意识形态。
简言之,同内外思维一样,上下思维也包括三个基本的构成部分:矛盾对立、执两用中和时中发展,但后者已通过马克思主义而建立在更高的客观的、物质的基础之上。
因此,在两种思维方式的整合中,李大钊对孔家的内外思维的传统,有扬弃,也有继承。当然,他在这个改造整合的过程中,只是开其端而己,但在当时所起的先驱启蒙作用,却是厥功至伟。
然而,以孔多塞(Condorcet)和孔德(Comte) 为代表的法国实证自由主义却相反地对历史采取一种“可知论”的态度,肯定历史中有法则和规律。他们认为人类已经掌握了某些基本的历史规律,而且深信人类可 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按照这些规律来控制历史的进程,创造一个与自己理想相符合的完美社会。法国实证自由主义的这种史观,正切合当时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所以李大钊也大量引进吸收(28),成为他的革命新史学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由上所述,五四后期及其后的中国思想界逐渐拒斥杜威主义,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文化思想和历史上的原因。同时,由此也可清楚地看到李大钊在史观方面,由孔丘主义借道法国实证自由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再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曲折心路历程。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上下思维范畴,初步解答了下列几个中国社会进行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
中国文明的再生问题
首先是中国古文明再生的问题。五四初期,李大钊本于孔丘主义的生机说(organism),兼采佛家的轮回说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博格森和尼采的意志论及自然科学知识等,论证文明必然像宇宙和生物界一样,经历永恒的由盛而衰、由衰而盛的往返流转过程,从而证明中国的古文明必然由“白首之民族”,恢复为“青春之民族”(29)。
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之后,他遂将这个主观的哲学信念改而建立在客观的科学史学或社会学之上。根据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科学考察也即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在未来的人类历史中,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死亡,社会主义必然取而代之,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李大钊完全接受这个论断,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30)。发生在苏联的大革命以及当时发生在欧洲和世界其它各地的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带来了这个体现正义与平等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世纪的信息。(31)
中国加入世界革命进程
其次,中国是否具备加入世界革命进程的客观条件这个大问题,使中国理论界和思想界深为困惑,而李大钊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不但要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还要走苏联的道路。当时的中国虽然正处于资本主义革命的初期阶段,但李大钊认为日本和欧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长期剥削已经使整个中国成为一个虽然没有现代产业工人阶级、但有无数受尽剥削之苦的工农劳动大众的无产阶级国家。这是李对中国加入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进程具有创意的经典论述,值得引述如下:
国內的工业都是手工工业和家庭工业,那能和国外的机械工业、工厂工业竞爭呢?、結果就是中国的农业經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經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国內的产业多被压倒,輸入超过輸出,全国民漸漸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級,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追不安的現象。在一国的資本制下被压迫而生的社会的无产阶級,还有机会用資本家的生产机关;在世界的资本制下被压迫而生的世界的无产阶級,沒有机会用資本国的生产机关。在国內的就为兵为匪,跑到国外的就作穷苦的华工,展轉迁徒,賤卖他的筋力,又受人家劳动阶級的疾視。欧战期內,一时赴法赴俄的华工人数甚众,战后又用不着他們了,他們只得轉回故土。这就是世界的資本阶級压迫世界的无产阶級的現象,这就是世界的无产阶級寻不着工作的現象。欧美各国的經济变动,都是由于內部自然的发展;中国的經济变动,乃是由于外力压迫的結果,所以中国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牺牲更大。(32)
李大钊在这里为革命历史学创造了一个「中国是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核心观念,点出了近代中国革命不同于欧美社会甚至欧俄社会的特殊国情。这种客观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客观社会条件,加上时不我与的迫切追求解放的主观愿望,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具备了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和可能性,从而为他的革命史学提供了客观的社会阶级基础。
主观(精神)能动性的反作用论(反映论)
最后也是革命史学的核心概念,就是道德精神在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问题。
显然由于深受深厚的孔丘主义人伦传统的熏陶及其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对它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说深感不安(33),从而觉得有必要予以批评和修正。所以,同时又主张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受伦理道德精神的支配:
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的法则。我们要晓得人间社会的生活,永远受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就可以发现出来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何时何处,都有它潜在,不论他是梦想的,或是科学的,却随着他的知识与能力,把他的概念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34)
这样,他就陷于阶级斗争的经济决定论和互助协合的道德决定论的两难的理论困境。但是他不认为这是不可克服的,首先,他将阶级斗争译为阶级竞争来缓和由此名词带来的“争夺强掠残杀”的气氛(35), 然后根据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从理论上论断有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假”历史,然后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斗争,使人类社会进于“真”历史之境。所以,阶级斗争不过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体现大同社会精神的互助协合才是改造社会组织的目的。换言之,他主张同时对物质和精神进行改造: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36)
他认为这样才可以纠正马克思学说“抹煞一切伦理观念”的缺失,并提出了社会主义伦理的概念。 他引述欧俄持相类观点的思想家的学说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支持他的观点。(37)他还进而认为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人自私自利的私欲还会存在,所以还要用社会主义伦理的互助协合精神来改造人类的精神。由此,李大钊将心物的矛盾统一起来了,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孔丘主义的道德决定论的两难困境解决了。简言之,他通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孔丘主义的道德决定论和贵和说,通过孔丘主义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论;两者不但可以互容,而且可以互补。
尽管他已经运用上下思维方式,承认经济因素是道德精神的导因,但是他特别强调道德精神的积极能动作用,纠正了机械唯物论的弊病。他认为,人在了解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之后,不是被动地、宿命地听由历史规律的支配,“坐待新境遇的到来”(38),而是主动地运用历史的规律,充分发挥自由意志,来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来创造历史,创造未来。很自然地,他由此主张是人创造了历史,而不是什么超人的东西如神等创造了历史:
斯时人才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求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的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消极)的生物,……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之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39)
这是李大钊革命史学的主观能动性的反映论的原型,虽然尚未明确使用「能动的革命反映论」的概念。这样,他一方面,通过孔丘主义仁性人本主义思想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物本主义思想,(40)避免了可能产生的唯物主义的宿命论;另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物本思想和自由主义的民主思想,纠正了长期麻痹中国人思想的唯心主义的宿命论。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李的上述论证,显示了他曲解了马克思主义(41),有的中国学者认为他的马克思主义不纯,掺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42);他的朋友和战友鲁迅也说他的有些观点“未必精当”(43)。这些看法,固然言之成理,但可能忽视了他像严复译介西方进化论和自由主义思想之同时根据中国的国情加以批判一样,如将社会主义译为《群己权界论》,在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努力之同时,他也是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是机械地全盘照搬;可能认识不到他正是批判地继承孔丘主义,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
这正是本文论证的主旨;正是李大钊把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吃掉了,消化了,融入中国文化的机体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正是李大钊而不是别人,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让后来者步其后尘,发扬光大。
是的,正是一个也是酷爱历史的、自承亲聆其教诲的毛泽东(44),继承了他开创的革命历史学,进一步深化阐扬了他的主观精神能动性的理论:
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领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45)
毛泽东认为,在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物质的东西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当然,两个“决定作用”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就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来说的,物质决定精神贯串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后者则就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环节说,精神的反作用具有了决定意义。
毛泽东又进一步证明了能动的革命反映论,是解决思维和存在关系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46)
由此,毛泽东进一步从理论上完善充实了李大钊革命历史学的核心概念,能动反映论的理论。
李大钊和毛泽东在革命历史学方面做出的贡献,郭湛波作了这样的总结,也作为本文的总结:
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依据这个观点,贯彻了实事求是的路线,才科学地认识了中国的国情,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47)
正是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革命历史学思想的启蒙下,经过毛泽东的充实完善,历经国内和党内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的激烈斗争,最后取得了大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设了中国社会主义,成就了中国崛起的伟业!
(全文完)
注释
1、梁启超认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三联书店,1980,页54);沈刚伯:《史学与世变》,见于沛主编的《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史学理论卷》,2000年,兰州大学出版。页467:世界上有了人,就有历史但是有了历史,不见得就会产生史学。古代曾有许多文化相当高的民族,如!埃及、巴比伦、希伯来、印度等,都产生过很优美的艺术、很玄奥的神学同很实用的科学;但是他们统统没有能够产生史学,尽管他们留下来不少珍贵的史料。这些文化都以神道为主,人世间一切的创造都附丽于宗教之下。像那样以超自然的势力为依据的文化是不会产生史学的。能产生史学的文化一定是以人道为本。。那就是说:它承认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用自由的意志,经过理智的考虑,而后创造出来的。因此一切结果都应自负责任,其动机与影响才有供人研究之价值。这种研究便是史学,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古代文化,实只有东方的中国同西方的希腊才有史学。
2、同上:可是这史学并不是在这两种古文化一开始就有的,其产生实在那些文化已经相当发展之后,而忽然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那就是说:当它们的政治结构濒临崩溃,社会组织大大动摇,经济生活和礼教活动都有很大的转变,那时候才产生史学。
3、中国产生史学,是在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同上,页468:沈刚伯认为:孔子修春秋,才正式产生史学。当时正是大变动的时代,东周的中央政权已经衰微到了有名无实的地步,诸侯各自割据,成了无数的小朝廷,这是政治方面的情形。就社会变迁而言,则当时封建制度已开始动摇,中产阶级,尤其是士的阶级,渐渐兴起,他们已经打入政治界,并且开始掌握了一切学术。经济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这时候铁器的使用,已经增加了农业生产;同时商人阶级也起来了,他们的力量,往往可以影响到国内外的政治,甚至左右了军事行动。这时候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既然都起了变动,旧有的礼教便自然无法维持社会秩序。加以内则诸侯兼并,外则四夷交侵,成了干戈扰攘、沧海横流的状况。孔子在政治上倡导的改革运动失败了,乃退而重修鲁国的春秋,想藉这部历史,一方面保存过去人类一些有价值的活动,另一方面则用很简单精确的字句来表示那些行为的正当与不正当。这就是所谓用笔削褒贬之法,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史学。根据这种史学的义法,一般人可养成历史思想,以为处世、论人、治事、立身的准则。中国文化也就因此逐渐形成了一个定型。
4、同上:秦汉统一中国,实现了“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的理论,自然要进一步做到“行同伦”;于是汉武帝乃有罢黜百家以配合其政治上需要之学。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的变迁导致了司马迁的史学。………。他这种编辑方法historiography竟成为我国正史的典型。……以“史”名书,使成为专门之学,在中国实自他起。……他是我国第一位专门史学家。尽管中国史官之设很早,而且一般思想家如儒家、墨家、法家等对于历史都有他们独有的看法,但他们毕竟是哲学家而不是专门史学家。
5、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资治」二字,点出其修此史书是要当政者,仿效历代的圣君贤相,向他们汲取治国的经验、智慧,以达到安邦定国、济世利民的目的。可参见宋神宗《資治通鑑序》: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 漢司馬遷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光之志以爲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敎,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自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敎,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墜顚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宄,厥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6、1902年初刊于《新民丛报》,后收入其《饮冰室合集》。另参见陈平原,《“元气淋漓”与“绝妙文字”—梁启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中之第一节:“史界革命”与“文界革命”,载于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88。
7、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新史学》,页4-6,香港三联书店,1980。
8、同上,页7-9.
9、事实确实如此, 李自称「夙研史学,平生收集书籍颇不在少」,是个历史的爱好者和研究者。(《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页888、889、893)当然也有人认为救国应从文学下手,如鲁迅放弃医学,从事文学。
饶有趣味的是,回顾中国历史,每逢天下大乱,改朝换代之际,首义发难之人,除了后汉的刘秀之外,大半起自民间的不学有术的草莽英雄好汉,例如刘邦、刘备、朱元璋,秀才造反的屈指可数,一个是后汉的刘秀,另一个是清末的洪秀全;前者成功,后者失败。到了近代,国民党的孙中山,中共的李大钊、陈独秀,都是大秀才造反。然而以研究治乱之道的历史学家的身份造反,独李大钊一人,岂非正是任公心目中之救国良史?于此可见,古今世道时运变化之大、之深!
10、《李大钊史学论集·史学要论》,页200。
11、李大钊,《史学要论》,页199。
12、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载于《李大钊史学论集》,页188。他举研究列宁为例,列宁是个活人,是有生命的。研究他,必须参考关于列宁的书籍,但不能说关于列宁的书籍便是列宁。由此可以类推二十四史中之列传,以及各种传记,都是研究历史人物的材料,不是历史本身,活的生动的历史。
13、李大钊,《史学要论》,载于《李大钊史学论集》,页197-198。
14、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见于沛主编,《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学·史学理论卷》,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页247:历史科学是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而斗争的有力工具,也即革命的理论武器。此即革命史学。
15、李大钊,《李大钊文集·庶民的胜利》,上,页593-595
16、同上,《Bolshevism的胜利》,页602-603;《李大钊选集》,页117。同类的文章中重要的还有:《唐山煤场的工人生活》、《列宁》、《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列宁不死》、《十月革命与中国》、《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马克思与第一国际》、《工人国际运动史略》、《一八七一的巴黎“康妙恩”(即巴黎公社)》、、《胶济铁路略史》、《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史》,等,均见《李大钊文集》、《李大钊选集》、《李大钊史学论集》。
17、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中国历史研究法》,页166-167。
18、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页13-14。
19、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下,页139;《李大钊史学论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页44;《李大钊史学论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李恺尔的历史哲学》,页132。
20、详见下文关于精神与伦理的作用一节。
21、根本改造论,出自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原文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另,李大钊在介绍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时,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学。 他是这样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
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从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人主义。……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李大钊史学论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页4)
22、《胡适文选》,第 40页。
23、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第 230-232页; Meisner, Li Ta-chao,第107-108页。
24、同上,第 233-235页; Meisner,Li Ta-chao,第150.151页。25、李大钊,《李大钊文集·再论问题与主义》,下,第 37页。26、孔丘主义的内外唯心辩证思维,经过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加以发展后而更为系统化,成为宋明以后帝王之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27、五十年代中期及文革时期,红专矛盾曾成为思想界和理论界争论的主题。28、他介绍了鲍丹(Jean Bodin)、鲁雷(Louis de Roy)、孟德斯鸠(Montesquieu)、韦柯(Vico)等的历史思想。参看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页73-119。29、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见《文集》上;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第 11页;Meisner,Li Ta-chao,第 26-28页。
30、《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文集》下,第 544-545页。
31、《 庶民之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新纪元》, 见《李大钊文集》上。
32、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之原因》,页62-63;《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李大钊文集》下,页454-455。MauriceMeisner,Li Ta-Chao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7,页144-145。
33、他说“有许多人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的原故”, 其中的所谓“深病”实在是夫子自道。参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同上,第21页。
34、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文集》下,第16页。李大钊的这个论点同前胡总倡导的和谐社会是多么的契合,所以今后在长期的和平年代建立和谐社会,也是可以从中国近代的革命传统中获得宝贵的思想精神资源的。
35、同上,第18页。
36、《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集》上,第22页。
37、《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集》上,页21。
38、《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史学论集》,页148-149。
39、同上,页148。
40、这个论点同前胡总报告中提出的“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是完全不谋而合的。
41、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页16; Meisner:Li Ta-chao:第六章。
42、《李大钊同志生平事略》,《李大钊选集》,北京,1959年,页12。
43、同上。
44、杜江帆, 《毛泽东回忆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中国军网,2017年5月3日。
4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矛盾论》,人民出版社,北京,1966,页314。
46、《毛泽东选集·实践论》,页285。
47、冯契,《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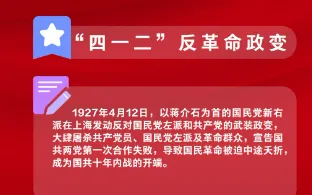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评论功能已恢复开放,请理性发表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