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
最近,有两位“文化人”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一位,战士作家高玉宝,于12月5日去世,享年92岁;
另一个,“诗人”流沙河,死于11月23日,他活到了88岁。
媒体对两位已故作家的态度颇值得玩味。
对于高玉宝,多家官微转发的是这样一段话:
【送别!“周扒皮”形象作者#高玉宝去世#享年92岁】12月5日,知名作家高玉宝逝世,享年92岁。他仅上过一个月的学,却先后写出总计200多万字的几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半夜鸡叫》还被拍成木偶电影,其中“周扒皮”形象深入人心。

客观、平淡、不含褒贬,突出高玉宝是“‘周扒皮’形象作者”。
如果把这一“突出”放在这些年来网上被自由派公知带起来的对所谓高玉宝“造谣污蔑周扒皮”疯狂攻击的背景上来看,那么这一“突出”甚至可以说是大有深意,一切尽在不言中的。
对流沙河,就不一样了。请看这样一段话:
#流沙河去世#【XX微评:流沙归河,潋滟随波】流沙归河,“蟋蟀”从此独叹息;“豇豆”摇落,谁来续写草木篇?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在中华文化中浸淫,在汉语中穿梭,老先生无愧“汉字侦探”美称。潋滟随波,春江月明,文化生生不息,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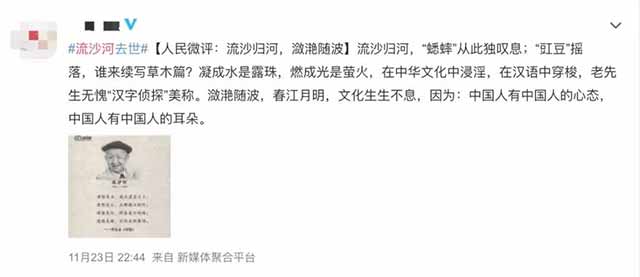
深情、哀婉、留恋与不舍,甚至有一点为不能追随于地下而深表遗憾的伤感。
说起来,这两个人还真不一样。
02
—
先说流沙河。
流沙河本名余勋坦。解放前,余家是四川金堂县有名的大地主,他的父亲余营成在县里当着兵役科长,以“吃人骨头钱”闻名当地。
余营成过着什么日子呢?据当地农民回忆——
生活过得好派头。大老婆和三个子女居住在成都,他和小老婆(原是丫头,被强奸后收上房的)与六个子女住在一起,雇了四个人:一个伙房,一个老妈子,两个奶妈。子女都在上高中大学。他哪里来的钱呢?就是买卖壮丁,敲诈勒索,吃人骨头的钱。
(以上引文见《四川的<草木篇>事件和流沙河先生》一书)
这样的派头,看来是需要亲自学鸡叫的“周扒皮”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1951年,余营成因为组织“反共救国军”等罪行被人民政府镇压,余勋坦也因此结束了号称“九老少”的少爷生活。不过他究竟聪明,一个华丽转身,就咸与维新,“参加革命”,到文联去当作家了。
然而杀父之仇,究竟没齿难忘。所以1957年,毛主席在看了流沙河的《草木篇》之后,不无感慨地说:“那些有杀父之仇、杀母之仇、杀兄之仇、杀弟之仇、杀子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一个《草木篇》。”
确实,毛主席目光如炬,没有谁能比毛主席看得更远、更透彻了。
到了新世纪,也许觉得时机成熟了吧,流沙河开始出来为自己失去的天堂和被新中国镇压的兵役科长之父辩护了:“99%的壮丁是自愿去的”,“《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好一个“诽谤旧社会!”
流沙河似乎忘记了,“诽谤旧社会”根本不算什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包括高玉宝在内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奋斗中,旧社会被推翻、被砸烂、被粉碎了!
你有什么不服气吗?
关于“抓壮丁”的事,已经有很多文章驳斥流沙河,这里不赘。但“诽谤旧社会”这句话很值得研究,而高玉宝的主要贡献,正是“诽谤旧社会”。
03
—
和从小养尊处优的余勋坦相反,高玉宝出身东北的贫苦农民家庭,没有条件上学,他15岁做劳工、17岁学木匠,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在辽沈战役的烽火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也是一位战斗英雄,在辽沈、平津、衡宝战役中立大功6次。
高玉宝入伍时,几乎是一个文盲。人民军队培养了他,他也凭着顽强的毅力,边打仗,边学文化。
一开始他连“半夜鸡叫”四个字都不会写。“半”字画了半个窝头代替;“夜”字画了个星星一看是夜晚;“鸡”的繁体字最难写,他只好画了一只鸡;“叫”字在小学看图识字课本上见过,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便画了一张大嘴,张着口大叫的样子。
就这样一步一步,他终于成长为著名作家,1962年,他还被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高玉宝在小说《高玉宝》中塑造的周扒皮的形象,阴险、毒辣、奸吝,体现了地主阶级的本质,也折射了旧社会的本质!
因此,高玉宝遭到那些把“旧社会”视为人间天堂,对“诽谤旧社会”痛心疾首“民国范儿”及其拥趸的诋毁与冷遇,也就不足为奇了。
04
—
高玉宝与流沙河,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代并都得享高寿,他们晚近几十年的奇幻之旅及身后的不同际遇,再次证明了列宁的一个著名论断——
“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毒害我们。”
就让流沙河沉入流沙吧,我们永远需要高玉宝!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