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先提一个问题,假如你处于生孩子的年龄,生个孩子给你100万,你生还是不生?
携程网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在11日发布的自媒体文章中表示,扣除二孩的堆积效应,近几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1左右,差不多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这个生育水平接近世界最低水平,比日本和南欧国家等典型的低生育率国家还要低很多。“未富先老”成为中国面临的一大难题,即便是简单地维持当前的人口基数都做不到。
梁建章说,鼓励生育是一项综合工程,包括很多社会政策的改革,复杂的教育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给你一百万生不生的问题。房子的问题怎么解决?教育问题怎么解决?许多家庭不堪重负,怎么生孩子?房地产政策、教育政策不改变,怎么可能奖励生孩子。
梁建章还表示,这些政策改革的推出和落实需要时间,短期见效比较快的措施是什么?就是——给钱!是给出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来直接补贴多孩家庭。
生育率的问题这样就能解决了吗?如果中国需要把生育率从现在的1.1提高到日本1.3-1.4的水平,需要花费GDP的2%;如果要提高到发达国家平均1.6的水平,需要花费GDP的5%;如果要提高到更替水平2.1,需要花费GDP的10%。以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是100万亿元来计算,GDP的10%,也就是说每年要花10万亿的财政支出。如果按照中国每年需要多生1000万的小孩来计算,每个小孩需要给予差不多100万元的奖励。
这种奖励可以是现金、所得税和社保减免,房价补贴等多种形式,单个家庭生与不生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拿出GDP的10%就要挤占其他方面的开支,这意味着会产生一系列更复杂的联动效应。因此,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一个孩子奖励100万的问题。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前,人口话题不时受到关注,“出生人口再刷新低”、“人口即将负增长”、“老龄化进程加速”等观点被热传,“北京户籍人口出生数创十年新低”更是冲上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榜。
在这之后,“2020年我国人口持续保持增长”这则官方消息的发布,对似乎弥漫全民的人口焦虑起到了一定的缓释作用,但似乎仍无法扭转全民人口焦虑之势。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那么,是否可以统一口径为“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为1200万⼈,相比2019年的1465万人减少了265万人,降幅约18%。与过去几年的出生人口数量相比较,自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创下小高峰后,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已经经历了2017-2020年的“四连降”。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七人普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我们应当认识到,低生育水平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还应该看到,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宁吉喆说。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变化及相关问题?除了持续走低的人口出生率,哪些关注点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从更长远的视野来观察,中国该如何应对人口问题?认了?还是拿出钱来改变政策取向?人口出生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吗?发达国家走这条路我们就要走这条路吗?我们不是发达国家,却比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还低。
有人说是前些年计划生育过度了,在司马南看来,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政策方针,往左拐,不见得不对,该往右拐的时候要往右拐,你打错方向盘绕了一大圈回来了,说当时往左拐是错的,这就不对。计划生育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的,只是该拐的时候没有拐回来。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至少从人类近200年的工业文明史来看是如此。18世纪4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英国发起,英国的人口增长率从1870年代开始放缓,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过程也几乎完全遵循工业文明传播的轨迹。
1909年,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利用西欧的人口数据描述了人口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演变规律,并奠定了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雏形。其中的重要观点就是,受经济因素的驱动,为了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有意识限制生育。
当前,工业文明的足迹遍布全球,受影响的国家无一例外均开始了人口转变,生育率下降。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前景》,按照国民收入水平划分的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分别是1.67、2.35和4.52。
中国不是发达国家,但生育率比日本低。司马南认为生育率问题是一个关乎子孙后代、全国人民的问题,是这一代的问题,下一代的问题,这件事绝不能轻描淡写。
工业化和现代化推动生育率下降的机制是复杂多样的。借由生殖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医疗技术⽔平的提高,避孕节育技术的可获得性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弱化了家庭功能,逆转了代际间财富流的方向,使得多生孩子成为非经济理性的事情。人口的再生产由追求数量的粗放型向追求质量的精致型转变,最终使得人们自主限制家庭规模来实现家庭成员平均福利水平的提升。
另一个因素是,女性的就业和受教育机会迅速提高,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伴随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推动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强化了家庭对于子女数量的理性选择。因此,全世界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都正⾯临生育率下降的⻛险,中国也无法避免。人们寄希望于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来提振社会生育意愿,遗憾的是,众多学者的研究均表明,发达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并不及预期。
那到底怎么解决呢?有很多说法,一方面是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中国应尽快优化生育政策,让自主生育权回归家庭和个体。另一方面,要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才能对冲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
对于上述方法,在司马南看来都有道理,但落实起来没那么容易。倒相反,梁建章奖励100万的方法,与房地产、教育政策结合起来,倒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至于是否实行?怎么实行?学者对此怎么看?我们无法决定。
【司马南,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司马南频道”,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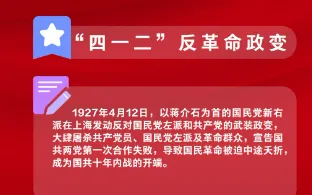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评论功能已恢复开放,请理性发表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