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隆重纪念建党100周年的缘故,拍摄了很多反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革命家活动的影视剧,如《1921》《革命者》等等,这是很好的事。
但必须指出,由于主创人员受到思想水平、视野,乃至立场、情感等因素的限制,这些作品主要集中于真真假假的“故事”,而不是“思想”,这些革命先辈对中国社会的深邃思考,对当年世界范围内各种新思潮的辨析,被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
这无助于观众贴近、感受那段历史,更无助于观众去理解、把握革命先辈的初心了。
比如,《革命者》这部以李大钊为主角电影,居然完全回避了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而这场发生在1919年的争论,可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播到中国之后,进行的第一场“理论战役”,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胡适的所谓“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的“主义”,是有非常具体的指向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而李大钊则针锋相对地声明:
“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如果说,“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障碍的第一回合,那么在北伐前夕,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新右派之间关于“孙文主义”的争论,则为第二回合。
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后,为了争夺“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国民党新右派中的“理论家”戴季陶连续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企图彻底切断“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转而将孙中山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统接榫。
戴季陶写道:
“中山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
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戴季陶又说:
“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接近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
在这一基础上,戴季陶梳理出了“孔孙道统”的概念,并声称“孔孙道统”是“中国的”,而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国民党既然是“孔孙道统”的承载者,就应该具备“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反对以“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
02
戴季陶在这里,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即把“中国的”和“外来的”之间对立绝对化,而忽略(或故意不承认)人类社会存在“共同”、“相通”或能够相互契合、理解的思想。
1925年12月,即戴季陶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小册子不久,郭沫若就在《洪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穿越文”《马克思进文庙》。
这篇文章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的笔调,描写了马克思走进文庙与孔夫子对话的场景。对话的结果是,孔子对马克思惊叹:
“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
而马克思对孔子惊叹:
“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
这篇短文,反驳国民党新右派的用意非常明显,也体现了郭沫若一贯的尊孔思想。
03
今天,戴季陶早已沉没在历史长河中了,但“戴季陶主义”却阴魂不散,因为总还是有人以“马克思是外国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为由排斥马克思主义,企图回到“完全的中国正统思想”上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马克思进文庙”、“马克思遇到孔夫子”的问题,就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所著的《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正是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以马克思与孔夫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的相遇为主线,通过特定历史语境的还原,试图从哲学观念、文化原型、精神气质等维度,揭示这种相遇的内在可能性,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何中华教授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洞见是:马克思主义与孔夫子的儒家学说,虽然在自觉的层面更多地表现为冲突,但在无意识层面却更多地表现为融会贯通,比如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与马克思所主张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等。
在这方面,何教授的结论和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一文的结论,颇有一点不谋而合。
由于二十世纪以来,人类追寻理想社会的努力不断遭遇挫折,许多人陷入失败主义情绪,更愿意谈“问题”,不愿意谈“主义”,但正如革命先辈李大钊所指出的,人类要进步,要寻求光明的前途,离开“主义”指引不行的。对历史、对未来,我们仍然需要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思考,而《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书,对我们进行这样的思考,一定会有所助益。
【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高度一万五千米”,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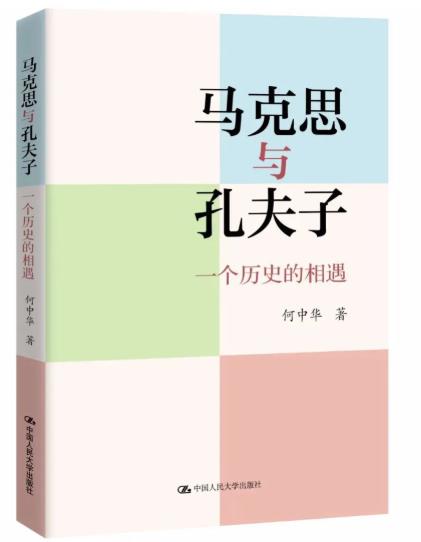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