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疫情当前,社区和居委会挑起战“疫”重担,如何更好发挥居委会的功能,群众自治如何和行政系统进行有效对接,如何激发社区活力,观察者网邀请长期研究基层治理、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讲讲他的观点。
观察者网:上海疫情初期,一篇8年前的采访传播广泛,其中提到“行政有效,治理无效”,居委会更多是居民自治组织,但现在构成了政府行政系统的一环,是否应该捋清居委会的权责,少一些制度性的障碍,有效发挥居委会的功能?
吕德文:如果把疫情防控比作战争,最高形式的防控策略则是群众自治。每个小区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觉执行防疫要求。
政府和民众都知道居委会的工作要自治和行政相结合,要权责明晰,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做不到,我们应该反思这个问题,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构想太理想了,时代和社会情境已经发生了变化。
第二个原因是可能没必要。这几年居委会的功能发生了变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变迁背景。近10来年,国家做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很多公共服务下沉了。以前老百姓办证得到街道或市民服务中心,现在很多事务,比如社会服务、养老、计划生育直接在社区办理。
居委会行政化并不是不好,行政化是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居委会做服务就是行政化最主要的表现,对基层治理研究者来说,他就是行政化了,因为他坐在前台和办公室,没有去发动和组织群众。
行政化并不是不好,它有一个特定需求背景,我们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要给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服务,还要依靠居委会。对居委会行政化我们要客观看待,它是公共服务下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居委会属于公共服务体系的最末端,它本身就属于服务体系和基层治理体系的核心环节之一。
从理想状态来讲,居委会应该是一个自治组织,但是自治组织并不排斥行政,以前的自治组织、现在的村民自治也都有行政任务。居委会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它还需要处理大量居民内部事务,比如纠纷调解、小区公共设施维护、养狗纠纷等等。
居委会行政化也有利于发挥它的自治功能。只有行政化了以后,居委会才有机会跟居民进行接触,从而找到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渠道,否则凭空无事去敲老百姓的门,老百姓不会开门的。行政任务跟自治功能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整个基层行政组织处于体系性的错位。公共服务体系下沉了以后,街道和上级部门很自然地把居委会当成一个下属单位,对居委会工作的考核,财政资源的拨付都是依靠行政任务。
居委会资金、工资依靠上面下拨,很自然地把行政体系的那一套运转逻辑引申到了居委会里,居委会变得越来越正规化,越来越按行政部门的逻辑去运作,它的目标也是完成上面的任务,运作方式是按部就班的,它被这个行政体系给吸纳进去了。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做好公共服务,所以考核体系引入了这些标准,相当于在资源下沉、服务下沉的同时,监督考核这一整套的行政运作制度也下沉了,居委会内部也科层化、行政化了。
这样改变以后,居委会的运转逻辑就不是自由自主地跟老百姓打交道和接触了,跟老百姓打交道变得没什么意义。而且现在反过来,为了让居委会跟老百姓打交道,走群众路线,结果走群众路线本身也被考核了,要求基层干部一个星期上门多少次,这种走群众路线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居委会带着上级的考核任务去跟老百姓打交道,老百姓如何信任居委会呢,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作考核需要拍照留痕,不是真正地和老百姓打交道。
其实和老百姓打交道很自然,我调研了很多社区,有一些社区书记和主任做得很不错,他们不坐办公室,每天在小区里转一圈,早晨和一些老人边聊天边买早餐,见到人打个招呼,下班之前又在小区里面转一圈,现在社区主任和书记不一定是要居住在本小区里,关键是要让老百姓知道你,要主动跟老百姓接触,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居委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这是一个体系性的问题,不是社区干部自身素质的问题。
我们的基层建设要把治理能力提高,通过服务老百姓来提高治理水平,把服务资源转化为组织和动员群众解决社区问题的契机和能力。
疫情防控就很典型,居委会有比较强的治理能力的话,小区的集体行动能力就比较强,不会说花费大半天叫大家下楼做核酸,还有人不配合。若是平常组织顺畅的话,只要在微信群公布不配合防疫工作的某栋楼某号,不用社区居委会出面,老百姓会组织形成一个统一的集体行动,自己来解决问题。
小区居民主动组织解决问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但是居民不是踢开居委会来自治,而应该是有效地在社区党委和居委会的领导统筹之下来搞自治。
观察者网:您讲到了社区居委会的三个能力,疫情期间,居委会需要跟志愿者、团购团长、物业保安、防疫工作者多方对接,期间也出现了很多摩擦,居委会没有时间培训志愿者、居委会与医疗防疫人员的对接出现问题等,群众自治组织和原有行政机构如何做有效对接?
吕德文:本质上还是居委会组织和动员群众的能力,包括对志愿者的培训、团购群众组织,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这也是社区日常工作内容,只是平时不太必要,所以积极性就不是很高,有些地方做得不是很扎实,现在特殊时期就显现出组织动员能力的重要性了。
我们有些社区没有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意识,反过来志愿者、团购负责人也没有意识到要主动对接居委会,在社区的统一组织和协调之下开展工作是最有效率的。
社区是一个中枢,它承接政府和街道防疫的统一要求,这些都要到社区来执行,所以最好是志愿者和团长主动做好跟社区居委会的对接。
武汉当时也面临这种情况,很多小区“团长”直接被社区居委会接管了,后来为了统一的对接,居委会的干部直接去接管团购。总归来讲,不能脱离居委会的统一的组织协调,否则肯定会乱套,居委会要对整个防疫目标负责,他们确实有这样那样的担忧,特殊时期更要通过内部协调来解决问题了。
观察者网:说到组织和动员群众,每个社区动员难度和情况都不一样,但在疫情状态下特别强调组织动员和社区活力,但是像上海这种大城市,社会原子化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到“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
吕德文:原子化跟社区活力之间不是因果关系,从社会学原理来讲,原子化程度越高,社会活力可能更强。因为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就说明每个人都对别人有依赖,大家才有动力组织合作起来。
这是相辅相成的,上海在这方面没有特殊性,每个城市都需要社区活力,每个地方具体的人口构成、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不一样,确实会让整个社区生态很不一样。
上海有商品楼、高端小区,也有类似于城中村、廉租房等区域,确实每一种类型的小区的活力程度有差别,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激发社区活力。
有些小区的活力在于居民以前都是同一个村,能够很自然地组织起来,商品楼小区有的业主意识比较强,一些老旧单位小区里,单位在补充力量,组织关系比较清晰,也可以把活力激发出来。
这是我们国家的强势领域,我国社会组织体系比较健全。各种类型的组织,不管是血缘地缘关系,还是单位、党组织都有这个优势。
某种角度来讲,我倒不觉得社会活力是通常意义上想象的西方社会的志愿者或NGO公益组织等,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志愿者和社区积极分子,还是来源于党员干部、群众里面的积极分子、戴红袖章的这些人。
我们得相信自己的社会,中国的城市有自己的特点和体系,激活社会活力的体系还是存在的,工作方法也是现成的,只不过缺少合适的激活契机。上海疫情已连续几天呈下降趋势,放长远看,我们终究还是会走过这一段时间,社会也有能力解决和应对这些问题。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以探讨居委会怎么样来利用社会活力,不单是上海,至少在我调研的各地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国家提倡整个基层治理现代化,也讲社会活力和社会组织,大家为了社会活力,请来很多外面的社会组织进小区做服务,政府购买服务,上海这种情况非常多,别的城市也是。
大量的政府资源和行政资源用于购买专业机构的服务,比如说大部分居委会请那些机构或专业的社会组织,最后反而机构代替了居委会的工作。
居委会给高龄老人、失独家庭服务,按道理应该是居委会自己去沟通和解决问题,为了创新或激活社会活力,请了很多专业社工组织搞服务,社区反而不出面了,看上去很多组织很有社会活力,但其实把社区的最重要的能力给丢掉了。
社区居委会和社会活力是合二为一的,一个社区有没有活力,在于居委会有没有组织和动员群众的能力,有没有发挥作用,有没有跟群众打交道。与其让那些外面专业的社工组织来,还不如发动小区的广场舞队,大爷大妈跟你一起去做志愿者服务,邻居都是本社区的,去了以后就增加了自己的组织动员能力,居委会跟老百姓群众之间的感情和联系才是最关键的。
我们现在的城市比较发达,资源和市场比较多,政府购买服务或外包也比较常见,比如垃圾分类本应该是组织动员群众很好的办法,大家共同把这个事情做好,居委会辛苦一点,也能把老百姓组织动员起来。
为了完成行政任务,有些居委会就找外包垃圾分类公司或让物业来做,专门有一个人守在那边,帮居民重新分类垃圾,这根本就没有动员群众和居民。
社会活力和经济发展、经济资源不是正相关关系,中间有很多机制有可能是相反的,资源越多,越不去组织动员群众,有钱有资源就很容易找到替代的办法。基层认为组织动员群众麻烦,需要受气和协调、很琐碎,一开始肯定是耗费心力的,一旦熟悉顺手后就特别轻松,但是基层工作人员往往胆怯这个过程,最后看似完成了任务,但是把社区的治理能力和组织动员群众能力给抹掉了。
观察者网: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防控期间的次生灾害问题,比如亲人去世无法去医院探望,大家都在质问,我们的清零政策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老人和小孩,但这个过程中却伤害了他们,如何让秩序更好地服务于人?
吕德文:在一个城市没有经历疫情防控紧急状态时,很多方面会出现问题,有一句话叫“吃一堑长一智”,我希望每个城市都能真正解决遇到的问题。反过来讲,疫情防控有其社会成本和制度成本。在疫情防控的过程当中,老百姓如果对政府不信任,上海形象就没有以前那么高大上,这都是属于制度成本的一部分,我觉得应该客观看待。
我们希望成本不要有或者越少越好,但是作为一个理性的分析者来看,这种理想化的情境其实不可能。最重要的是碰到问题正面应对,尽量减少重复出现错误,减少低级错误。
同时,疫情防控也属于国家治理行为,不单单要有明确的行政目标,背后也有一个更大的政治产品。我们要通过好的防疫防控来提高治理水平,提高国家治理的合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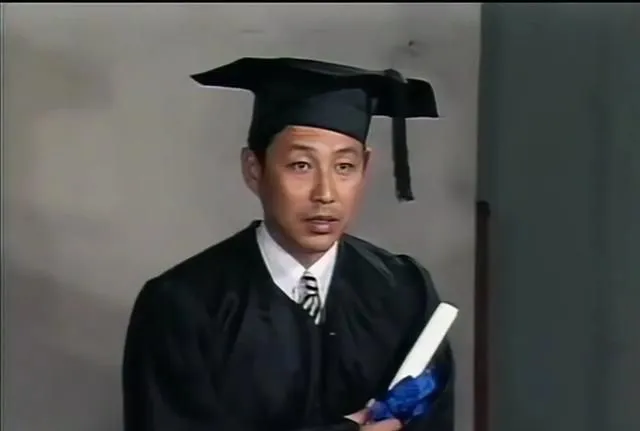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微信或手机浏览器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