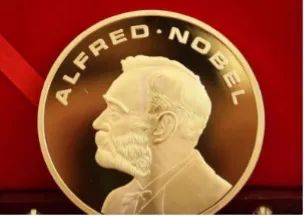
二战后,西方大国无法像过去那样进行殖民统治,越发重视通过“思想殖民”方式对非西方国家进行间接控制。在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武器中,最隐蔽的做法之一,就是通过颁发各种国际奖项,来塑造和引导非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审美标准。
这是因为,人类从认知到实践本身就是个环环相扣的链式反应过程:政策观取决于战略观,战略观取决于价值观,价值观又受审美观影响。审美观可以说是国家意识形态链条的源头之一。正像科学体系建构的前提是若干毋庸置疑的公理,每个国家价值体系大厦的根基,同样是不证自明的是非标准和审美标准。一旦审美观发生颠覆性变化,便会不知不觉地改变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最终导致灾难性的战略和政策。国际大奖看似只颁给少数群体,实则具有很强的示范带动效应。
在这方面,诺贝尔奖知名度高,同时意识形态色彩也较为明显,是西方重构和引导非西方国家价值体系的重量级武器。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以1974年哈耶克和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时代。但这些经济学理论并未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而是拉大了国内和国际贫富差距。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应对2008年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负有一定责任。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普通劳动者乃至国家都是全球利益再分配的输家,唯有大资本力量成为真正的赢家。
从国际战略角度看,诺贝尔文学奖和和平奖经常被西方国家当作实现地缘战略的重要工具,目的就是将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或地区收编到西方文明价值体系中来。在这方面,苏东阵营的经历最为典型。冷战时期,西方为从思想上瓦解苏东阵营,频频给苏东国家的异见作家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共有5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蒲宁(1933年)、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肖洛霍夫(1965年)、索尔仁尼琴(1970年)、约瑟夫·布罗茨基(1987年)。这些作家的作品大多或隐或现地带有解构革命、反抗苏联政府色彩,因而符合西方解构苏联价值体系的口味。
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将战略重心转向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成为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对象。在此背景下,伊斯兰世界的作家,如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旅法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旅法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雷、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阿切贝、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等等,一夜之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其中,埃及作家马赫福兹、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很难一一甄别这些作家的作品,但它们无疑是符合西方精英口味的。
诺贝尔和平奖看似是推动世界和平,褒奖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人士和组织,实则同样是西方国家收服非西方世界的糖衣炮弹。挪威本身就是北约成员国,与美国、英国关系密切。有学者尖锐指出,诺贝尔和平奖实际是个支持战争的奖项,并列举出5个证据:一是该奖项刻意塑造“我们是好人”的宏大叙事,据此有权决定世界其他国家的命运;二是美化非西方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为西方国家策动政权更替创造条件;三是通过制造特殊议题(如保护妇女权益等),为西方国家发动战争制造理由;四是渲染对手使用各种不人道的武器(如化学武器、凝固汽油弹等)的话题,借以发动战争或进行制裁,如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就获得2013年诺贝尔和平奖;五是褒奖有利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利益的和平条约,如1990年戈尔巴乔夫因向西方让步而获奖。
近些年来,伊斯兰世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士也在增多。2003年,伊朗社会活动家希尔琳·艾芭迪因“为民主和人权,特别是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所作出的努力”获得和平奖;2005年,埃及的穆罕默德·巴拉迪,因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期间,“在防止核能用于军事目的,并确保安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作出巨大努力”而获奖;2011年,也门的塔瓦库·卡曼,利比里亚的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和莱伊曼·古博薇因“为女性安全以及女性全面参与和平建设工作权利所做的非暴力斗争”,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4年,巴基斯坦女孩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和印度人权活动家凯拉什·萨蒂亚尔蒂,因“反抗针对儿童和年轻人的压迫,捍卫了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共同获得和平奖;2015年,名不见经传的“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组织,因“对促进突尼斯多元民主进程做出决定性贡献”获得和平奖。这些获奖者“事迹”各异,但无不符合西方国家引导伊斯兰世界价值观的总体要求。吊诡的是,就在这些伊斯兰世界人士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同时,伊斯兰世界却饱受西方欺凌,日渐陷入政治动荡和经济萧条交织的黑暗深渊。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围堵和遏制力度增多,中国所谓“异见人士”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和概率也在增加。这恰恰表明,“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距离中国越来越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微信或手机浏览器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