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时刻,有两份重要的学术文本值得我们关注:一是他写于1879年末至1880年初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是马克思对自己《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的一个基本的回应;二是1881年马克思给俄罗斯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这是他在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这些文本,共同反映了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识思想中的一定变化。在本文中,我们对其中的一些重要思想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研究的深入。
一
我们先说第一个文本生成的历史背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之后,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悄悄地形成了一种对马克思的思想“围剿”。这直接涉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问题。第一个需要提及的学术事件,是德国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在写给J.采勒的信中,谈到马克思“利用”了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一书中的观点,散布着马克思“剽窃”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奇谈怪论。1881年,在由鲁·迈耶尔出版的《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中,洛贝尔图斯在他的第60封信中说:“我现在发现,谢夫莱和马克思剽窃了我,而没有提到我的名字”(这个谢夫莱,我们在下面马上就会说到他)。在第48封信中,洛贝尔图斯更明确地说:“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本质上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这也就表示,如果洛贝尔图斯的指证成立,那么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秘密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原创性就受到质疑。实际上,马克思在世时,已经知道了这种荒唐的指责,但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他甚至跟恩格斯说:“如果洛贝尔图斯认为他自己的叙述更简单、更明了,那就让他去享受这种乐趣”。马克思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长达四十多年时间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别是对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秘密的艰辛探索过程,我们会对洛贝尔图斯的这种狂妄自大感到好笑。对于这件可笑的事情,恩格斯后来做了必要的澄清。
第二件应该提及的学术事件,就是同被洛贝尔图斯指责为与马克思一起剽窃了他的思想的阿·谢夫莱。这个作为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经济学家,于1870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研究的大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别是对经济活动形式和财产形式的考察》(Kapitalismus und Socialismus,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Geschäfts-und Vermögensformen,Tübingen)。此书洋洋洒洒700多页。从内容上看,此书由15篇演讲组成,其中,谢夫莱在第5篇演讲中,先是区分了“家长制的(patriarchalische)、神权政治的(theokratische)、封建的(feudale)和资本主义的(kapitalistische)国民经济(Volkswirthschaft)”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之后,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过程(Wesen und Hergang des Kapitalis-mus)———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Kapitalismus und Liberalismus)———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相对有效性(Relative Geltung der kapitalistischen Organisationsform)”等问题。并且,他在第11篇演讲中专门提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这里,谢夫莱明确指认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批判观点,这主要涉及“作为未支付的剩余劳动的资本利润(Kapitalprofit als unbezahlte Me-hrarbeit bei Marx)”,基本形式为资本家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侵占(Aneign-ung)”。然而,谢夫莱的最终结论也是十分明确的,他认为,“废除资本主义会导致更糟糕的弊病(die Aufhebung des Kapitalismus ausübel schlimmer machen würde),以前的国民经济还是不完善的,资本主义内部的实际弊病不是无法治愈的(die th atsächlichen Uebelstände innerhalb des Kapitalismus nicht unheilbar sind)”。这表明,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谢夫莱,无法接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最后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剥夺者将被剥夺”中最终灭亡的断言,他仍然幻想着通过各种方式的修补使资本主义长久生存下去。对于谢夫莱的观点,马克思觉得并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虽然他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在表面上受到了《资本论》的影响,但其学术观点仍然是极其肤浅的。马克思在1870年9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顺便说一下,杜宾根的教授谢夫莱出版了一本荒谬的厚书(价值十二个半先令!)来反对我。”恩格斯在9月13日的回信中称,谢夫莱虽然是个“庸俗的经济学家,但有可能是马克思的‘真正对手’”,而马克思则说:“谢夫莱说他研究《资本论》已经十年了,可是仍然理解不了”。这是因为,谢夫莱根本无法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真正透视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中的真实占有过程与经济表象中剩余价值转化形式中利润、利息和地租等的复杂再分配的关系,也根本不可能进入经济拜物教背后,去发现资产阶级特有的经济物相化编码中的事物化颠倒与劳动异化关系的更深构境层。这是谢夫莱自身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立场和非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决定的。
不过,对谢夫莱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我有以下的补充性评论:一是出版于1870年的谢夫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别是对经济活动形式和财产形式的考察》一书,是让史学大师布罗代尔被打脸和出丑的历史事实,因为这比他简单否定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概念所列举的谢夫莱的学生桑巴特的《资本主义史》(1902年)要早了近30年。固然,谢夫莱的书是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影响下写成的,他也专门划界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比我迄今所使用的这个词的概念要窄”。这也说明,连谢夫莱自己都承认马克思是率先提出和系统研究资本主义问题的人,但是,同时应该承认的事实为,谢夫莱的这本书的确是第一本以资本主义(Kapitalismus)为直接标题的研究性论著。二是谢夫莱在此书中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自由主义”弊病所提出的修补方案,特别是经济结构中强调“国家援助(Staatshil-fe)”力量,以生成“资本主导的(kapitalherrschaftliche)和合作社的(genoffenschaftliche)”两种“资本主义管理(kapitalistischer Geschäftsführung)”混合经济的观点,是后来20世纪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等资本主义修补方案的先声。这可能是过去相关研究所忽视的思想史实。
第三个学术事件,就是同属德国新历史学派的“讲坛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瓦格纳于1876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第一卷。在此书中,瓦格纳声称要通过教科书的方式对“一般或理论的国民经济原理(Allgemeine oder theoretische Volkswir-schaftslehre)”给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应该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出版近10年后,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的最新经济学看法。这显然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瓦格纳的这本书由两篇8章组成。在第一篇中,他从“国民经济的基础(Die Grundl-agen der Volkswirthschaft)”开始,依次讨论了作为“人的经济本性(Die wirthschaftliche Natur des Menschen)”的需要、欲望、劳动和经济概念,并通过获得财富的不同方式推导出“经济财富(wirthschaftliche Güter)和交往财富(Verkehrsgütern)”,以对应财产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区分了个体经济(Die Einzelwirthschaften)、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并着重讨论了私人经济为核心的“自由竞争的现代体系(Das moderne System der freien Concurrenz)”的缺点(Nacht-heile),以及“强制性公共经济”的可能性和国民经济中国家的补救行为。在第二篇中,他从“国民经济和法律权利”的关系入手,特别分析了所谓财产权问题。在对“财产制度(Eigenthumsordnung)”的讨论中,他区分了“占有理论和劳动理论(Die Occupations-und die Arbeitstheorie)”,分别对地产、林产、矿产、路产和房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所谓财产的侵占问题。可以看出,瓦格纳的这本教科书,明显受到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但是在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时却始终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在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矛盾时,采取了改良主义的立场,试图通过国家的“强制性公共经济”干预,来挽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
二
显然,瓦格纳的这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被马克思视作需要认真对待的事件。1880年,马克思写下了《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Randglossen zu Adolph Wag-ners“Lehrbuch der politischenÖkonomie”)一文的手稿。在这一未完成的手稿中的经济学讨论中,马克思只是评论了瓦格纳这本800多页的教科书中的很少内容,即到第一篇第2章第3节(第131页)的内容。这里,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评论瓦格纳的观点。
手稿一开始,马克思就指认了这样一个他关心的问题,即瓦格纳说,自己的观点同我们上面提及的洛贝尔图斯和谢夫莱的观点“相一致”,并且,“在‘叙述的基本论点”上他‘引证’洛贝尔图斯和谢夫莱的话”。也就是说,马克思意识到了这种同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混浊暗流中的合流。但从手稿的实际写作情况来看,马克思只是几次简单提及谢夫莱从《资本论》中学去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和抄袭走的“物质变换”概念,而对洛贝尔图斯的评点也是零碎地出现在瓦格纳引述的经济学观点中,显然,马克思主要批判的对象还是瓦格纳,因为他觉得需要认真对待瓦格纳这个成体系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大杂烩。
马克思看到了瓦格纳的理论前提是“经济的社会生活的条件”(Bedingungen des wirtschaftli-chen Gemeinlebens),并“根据这些条件来确定个人的经济自由的范围”。从客观的“经济的社会生活的条件”来确定个人的经济自由状态,这是我们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就已经熟悉的社会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然而,马克思说,瓦格纳并没有从历史认识论的视角去进一步分析不同时代中作为经济社会条件核心的“劳动的具体性质”,这就使瓦格纳的这些看起来不错的观点成为抽象的空话。我们已经知道,从经济条件背后的物质生产中,透视出工人主位的劳动过程,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构境中观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关键的基始视位。马克思告诉瓦格纳,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起始对象既不是抽象的“价值”,也不是没有具体历史性质的“交换价值”,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特定历史现象的“商品”。马克思说:“商品作为价值,只代表某种社会的东西(etwas Gesellschaftliches)———劳动,所以商品的价值量,在我看来,是由商品所包含等额的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的,因而是由生产一个对象所花费(Produktion eines Gegenstands kostet)的标准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这里,马克思所指认的价值代表的etwas Gesell-schaftliches(社会的东西),其实是指瓦格纳不能理解的一定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的由工人劳动物相化活动塑形和构序对象的社会经济关系场境。从根本上看,商品的“价值量”不过是工人生产一个对象所花费的一定劳动时间在劳动对象中的对象化,这里的“标准的劳动量”,是指社会必要劳动的尺度。这是李嘉图早就说明的问题。我们知道,这是马克思接受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之后,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一直到《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已经反复思考、讨论和阐述的基本观点。然而,马克思此时公开发表的文本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和《资本论》第一卷。这些公开文本中,已经看不见这一重要观点生成的复杂历史过程,特别是马克思基于向公众叙述理论观点的需要,他本人在经济学批判中创立的历史现象学中的经济关系事物化颠倒和劳动异化批判构式都被策略性地遮蔽起来了。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能看到马克思像教小学生一样,向瓦格纳、谢夫莱和洛贝尔图斯之流说明这一观点最基本的要点。这也使得马克思的这一文本,与他已经写下的丰厚经济学手稿相比显得像白开水。显然,这不能怪马克思。
首先,马克思必须说明自己与李嘉图在价值理论上的差别。因为,上述观点在表面上看起来形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马克思告诉看不懂《资本论》的瓦格纳:“我和李嘉图之间的差别,李嘉图实际上把劳动只是当做价值量的尺度(Maßder Wertgröße)来考察,因而他看不到自己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的本质(Wesen des Geldes)之间的任何联系。”如果劳动仅仅是价值量的尺度,那么,劳动的交换关系客观抽象所生成的一般价值等价物,到这种社会关系自我脱型和颠倒地通过货币的自然物性表现出来的事物化和异化的历史本质就会被掩盖起来。这也必定会导致“李嘉图(随斯密之后)把价值和生产费用混淆在一起”,进而在面对机器化大生产进程中的社会生产时,再将“价值和生产价格(它只是在货币上表现出生产费用)”混淆起来,最终再通过生产成本和平均利润(地租、利息和税收等)的假象掩盖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马克思显得非常“遗憾”地说,这些问题他已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讲得清清楚楚,可是身为经济学教授的瓦格纳竟然看不明白。因为,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瓦格纳与李嘉图一样,他会反对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看作是“暂时的(transitorisch)”,似乎他们所面对的机器化大生产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是永恒存在的“自然法”,这当然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中坚决反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告诉瓦格纳:“社会的生产过程(gesell-schaftlicher Produktionsprozeß,更不必说生产过程一般),在私人资本家出现以前就存在的很多公社(古代印度的公社、南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等等)内,是不存在的(nicht existierte)。”马克思已经从摩尔根《古代社会》了解到,在原始部族生活和东方仍然存在的土地公有制的农村公社中,人们在土地上劳作,但根本不可能出现劳动交换中抽象为价值的社会性的生产。这表明,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所依托的“私人资本家”控制的现代生产过程本身,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出现的社会历史现象,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这里,马克思提出的丝毫不存在现代“社会生产”的古代印度和南斯拉夫的公社生活,是他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进行的古代社会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成果,这些重要的历史史实,进一步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为他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界限。
其次,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问题。这是马克思透视和解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本质最重要的方面。针对瓦格纳提出的资本家作为生产成本回报的利润是价值的构成因素,而不是对工人的剥取和掠夺的观点,马克思说:
我把资本家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并且非常详细地指出,他不仅“剥取”或“掠夺”,而且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帮助创造属于剥取的东西;其次,我详细地指出,甚至在只是等价物交换的商品交换情况下,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符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
马克思没有办法向这位专业经济学教授说明,资本家并不是主体意义上的人,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居统治地位资本关系反向物相化的人格化伪主体,他只能用通俗的语言将这种复杂关系场境表达为Funktionär(职能执行者),并且,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取”虽然不是直接的掠夺,却是在商品交换的公平原则下支付工人劳动力使用权价值(工资)后,合法地在生产过程中悄悄地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我想,马克思与这些学院派的教授讲剩余价值理论肯定是心累无比的,马克思最后放弃公开发表这一手稿的原因,应该也与此有关。
也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提及与瓦格纳同伙的谢夫莱的“Kapitalismus”etc(“资本主义等等”),这显然是指后者已经出版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马克思对谢夫莱外在地搬弄Kapitalismus这一概念,却无法科学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荒谬的厚书”,显然是嗤之以鼻的。因为,谢夫莱根本没有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生、统治关系的本质以及微观运行机制,这恰恰是马克思长达40年艰辛努力获得的科学社会主义中的伟大理论发现。
其三,关于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关系问题。马克思已经发现,经济学教授们擅长“玩弄概念”,瓦格纳在十分繁琐地讨论客观价值与主体价值之后,将“价值一般”直接等同于使用价值,并且援引洛贝尔图斯“只有一种价值,即使用价值”的说法,由此指责马克思“主张‘使用价值’应该完全从‘科学’中‘抛开’”。可想而知,读到这段话时,马克思必定是哭笑不得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的确说明,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商品的价值关系以及货币、资本等复杂经济关系,但他从来没有否认工人的具体劳动之所塑形和构序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关系的物性前提。在我们过去自己的经济学和哲学研究中,真的不太关注马克思在中晚期经济学研究关于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对象的使用价值问题。
马克思告诉瓦格纳教授:
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这里我发现,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本身就是“交换价值”。对后者的进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换价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表现形式”,独立的表达方式,而后我就来分析价值。
因为瓦格纳及洛贝尔图斯都停留在经济物相化编码的表象之中,所以他们根本无法入境于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构式中特有的复杂社会关系场境,只能看到商品作为对象性的物及效用(一般物相化结果的“使用价值”),而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前提,从一开始就是透视第二层级经济物相化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这种历史现象学的批判性解码,让马克思着眼于工人劳动所塑形和构序的“劳动产品”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特有的定在形式,即市场交换场境中同时具有价值经济关系的商品:一是商品作为客观的用在性实在,是工人通过具体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起来的使用价值,它除去能够被直接消费以外,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可以换取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物性承担者。马克思还专门辨识说,洛贝尔图斯和瓦格纳所假设的“一般使用价值”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一般物品的使用价值本身是历史性的。
人在任何状态下都要吃、喝等等{不能再往下说了,什么要穿衣服或要有刀叉,要有床和住房,因为这并不是在任何状态下都需要的};一句话,他在任何状态下都应该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到自然界去寻找现成的外界物,并占有它们,或者用在自然界发现的东西进行制造;因而,人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事实上总是把一定的外界物当做“使用价值”,也就是说把它们当做自己使用的对象。
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人首先要吃喝穿住,为满足直接生活资料的需要而进行生产,但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本质是人通过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制造”,改变自然中的“外界物”而获得用在性的“使用价值”,这是不变的社会定在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前提。然而,这种劳动物相化所产生的用在性关系却是具有历史性质的。所谓“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例如,在生活资料由社员共同生产和共同分配的原始公社里,共同的产品直接满足公社每个社员、每个生产者的生活需要,产品或使用价值的社会性质这里正是在于其共同的性质”。这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私人占有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原始部族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在那里,产品的效用直接服务于生活的“共同的性质”。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产品效用性在商品交换中生成的特殊历史属性。二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中的交换价值,只是商品中包含的抽象劳动———价值的“表现形式”(《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价值形式),也因为,这个不可见的商品价值是之后理解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的前提,所以价值关系才会成为关注的焦点。马克思说:“我不是把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它们当做‘价值’这个抽象分裂成的两个对立物,而是把劳动产品的具体社会场境(konkrete gesellschaftliche Gestalt)分为这两者;‘商品’,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因为单是表现形式不构成其本身的内容。”这里,马克思用下划线重点标识出的konkrete gesellschaftliche Gestalt(具体社会场境)一语是极其重要的,我觉得,根本不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教授们,是无法入境于这个“社会形式”“自然形式”“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之间复杂的场境关系存在论的。这亦表明,虽然洛贝尔图斯指责马克思“偷了”他的剩余价值观点,谢夫莱用一本厚书讨论Kapitalismus(资本主义),瓦格纳编写了关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他们根本不可能真正进入马克思的经济学构境,特别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批判话语编码。马克思分析说:
物(Ding),“使用价值”,只是当做人类劳动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 men-schlicher Arbeit),当做相同的人类劳动力的消耗,因而这个内容表现为事物的对象性质(gegenständlicher Charakter der Sache),表现为事物本身(ihr selbst sachlich)固有的性质,虽然这种对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不表现在其自然形式上(正是由于这一点,特殊的价值形式就成为必要)。
这是马克思这一文本中比较重要的一段深刻表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不仅区分了可见的“自然”实存的Ding(物)和一定社会关系场境赋型和编码中的Sache(事物),也再一次使用了劳动的Vergegenständlichung(对象化)和事物的Gegenständlichkeit(对象性)这样一些他自1844年就开始思考的哲学话语,这是马克思超出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济物相化无形编码的关键。在此,马克思深透说明了商品物的使用价值不过是工人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活动的对象化结果,但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力的消耗”,在商品交换中必然客观抽象为离开其“自然形式”的价值关系,这种不可直观的价值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则会以另一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颠倒地表现出来,这就是价值形式(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历史生成。当然,这是一种高度浓缩的理论概括。
其四,劳动二重性与商品价值二重形式的关系。马克思进一步告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教授们,在商品的价值关系背后,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遮蔽起来的劳动二重性。
在分析商品的时候,我并不限于考察商品所表现的二重方式(Doppelweise),而是立即进一步验证了商品的这种二重存在(Doppelsein)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质(zwiefacher Charakter der Arbeit):有用劳动(nützlichen Arbeit),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具体模式(konkreten Modi),和抽象劳动(abstrakten Arbeit),作为劳动力消耗的劳动,不管它用何种“有用的”方式(“nutzlichen”Weise)消耗(这是以后说明生产过程的基础);论证了在商品的价值形式(Wertform)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货币形式即货币的发展中,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另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论证了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
我还是觉得,马克思特有的经济学构境对于瓦格纳、谢夫莱和洛贝尔图斯等人来说,像是天书一般,商品价值关系表现的二重方式本身就已经让教授们难以理解,其背后再揭示的劳动的二重性质,更会使他们不知南北。马克思这里揭示的劳动二重性,既有可见的工人们的具体劳动模式中直接塑形和构序的用在性上的使用价值,也有作为一般必要劳动时间“消耗”的不可见的抽象劳动。只是这种用于商品交换关系中凸显出来的抽象劳动———价值关系,在自己的颠倒性表现方式———不是在它自身的价值形式(“交换价值”)中,一般价值等价物———货币以自己的物性(自然形式)事物化地颠倒呈现出来。不理解进入这一特定的构境,就更不可能领悟为什么剩余价值会是工人劳动力价值交换关系背后的特殊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秘密。由此,马克思才感叹道,教授们无法知道,抽象地谈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语句,与具体地分析客观发生的社会历史进程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现象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前提,即不是抽象地讨论非历史的概念,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ökonomisch gegebnen Gesell-schaftsperiode)出发的分析方法”,所以,商品、货币和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场境存在,“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生的,而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即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才发生的”。马克思的最后结论是:“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kapitalistischen”Warenproduktion),按照商品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归资本家,而不归工人”。其实,一直到这里,马克思都是在向经济学教授简要地说明自己劳动价值论的基础知识,他还没有开始进入剩余价值理论更复杂的思想构境。我猜测,也许马克思愈加觉得这种与资产阶级学院派教授的争论是无意义的,于是,他立刻放弃了这一努力。
三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文本,就是马克思1881年写下的《致查苏利奇的信》。这一文本,也反映出晚年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上的一些重要改变。1881年2月16日,俄罗斯女政治家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希望马克思就俄国社会的未来命运问题的争论发表看法。在查苏利奇看来,这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俄文版在俄罗斯出版之后,围绕着“俄国土地问题和农村公社”展开的重要争论。因为,在查苏利奇和其他激进的俄国民粹主义分子眼里,俄国的公社式土地所有制是不同于欧洲土地私有制的特殊类型,只要摆脱了封建专制和地主的“蛮横专断”后,俄国公社“在集体原则的基础上,逐渐组织自己的生产和分配”,由此完全可能“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却认为,按照《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一种陈腐的形式”,它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必然走向灭亡,这样,俄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经历“几百年”资本主义的悲惨命运。她写道:“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么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
其实,这里的背景是非常有趣的,作为民粹主义的政治家,查苏利奇等人当时的争论对手正好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俄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俄国的民粹主义看到了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社会的不平等,所以他们力图使俄国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跳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沿着不同于欧洲的俄国公社的特殊道路,在避免阶级冲突的情况下达到农业社会主义。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则强调,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具有的普遍意义,他们认为应该欢迎俄国资本主义的到来,因为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所以,他们不承认民粹主义者所说的俄国的特殊道路,俄国绝不可能停留在农业公社的阶段上,它必然会经过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列宁当时的态度集中反映在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正是在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是否为俄国社会的必然历史命运这个大的争论背景下,查苏利奇才写信给马克思。这里出现的问题实质是,马克思所面对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是一种世界所有民族和地区人民都要经历的普遍适用的社会历史必然性?
其实在此之前,同样是俄国民粹主义理论家的米海洛夫斯基,在1877年10月的《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了名为《卡尔·马克思与尤·茹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在此文中,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认的资本的世界历史逻辑,表达了一切民族不论所处历史环境如何,都会走上与西欧一样的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道路的观点。他断言,俄国“将会紧随欧洲去经历整个过程,对于这一过程马克思已经有所描述并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但区别在于,我们不得不重复该过程,也就是自觉地完成它”,马克思自己恰恰否定了“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所做的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尝试”。然而,马克思同年11月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评论米海洛夫斯基: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Kapitalismus in Westeuropa)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allgemeinen Entwicklungsganges)的历史哲学理论(geschichtsphil-osophische Theorie),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赋型(ökonomischen Formation)。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此时,开始进行古代社会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经济学研究中所面对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的社会Formation(赋型),特别是Kapitalismus in Westeuropa(西欧资本主义),并非一定是世界上所有地区或民族必然通过的历史阶段,特别是俄国存在着的土地公有条件下的公社制度,所以,马克思开始明确Kapitalismus(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道路本身的边界。这是马克思在自己的文本中少见地明确使用Kapitalismus的概念。马克思说,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
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这里,马克思所提及的分析社会历史发展中一个具体时期,并将其“分别加以研究”所获得的“钥匙”,显然不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而是特指与他自己中晚期经济学研究相对应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对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认识。马克思已经发现,不能将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变成贯穿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将这种原发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变成超历史的普遍原理。应该说,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中的重要进展。
查苏利奇的这封信件,显然触发了马克思的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从1881年2月底到3月初,先后写下了四份草稿和一份定稿。在马克思的全部文本中,这可能是除《资本论》第2—3卷的多重手稿之外,第二个多复本手稿。从文本的基本情况看,前三个草稿中的观点塑形和思想构序线索较为细致并渐次展开,第四稿(同定稿)为马克思对此问题打算给出的最终看法。这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呈现出一个非常真实的思想实验过程,也表现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认识边界的一定改变。
在四份草稿的初稿中,马克思明确指认,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production capitaliste)的起源时将其基础理解为“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命运’(《fatalitéhistorique》)限于西欧各国”。这可能是指他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开始讨论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解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前提,特别是欧洲中世纪后期“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生成的必要历史条件。在书信草稿的二稿中,马克思增加了从“封建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转变”一语。三稿中增加了“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转换的限定语。能够观察到,在米海洛夫斯基、查苏利奇与普列汉诺夫、列宁共同关注的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的“历史命运”上,马克思特意打上了双引号,以标注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的社会历史必然性的一定边界。我推测,此时也因为马克思从古代历史和人类学研究中获得的全新认识,他知道世界上不同地区和民族的社会历史进程并不是同一的,甚至从原始部族生活开始就可能是异质性的,所以不能用完全相同的一般社会赋型或者生产方式筑模加以套用。他认识到:“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赋型(formations géologiques)一样,在这些历史的赋型(formations historiques)中,有一系列原生的(primaire)、次生的(secondaire)、再次生(tertiare)的等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在书信草稿的三稿,这段表述被改写为:“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序列,这些序列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这也意指着,欧洲原始共同体的解体,一直到中世纪结束以后“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的历史赋型,甚至他所提出的资本的世界历史逻辑,并非俄国公社或者其他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必然经历的命运。
首先,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此时关于社会历史赋型的观点里,直接使用了地质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这是他在50年代就开始并在70年代中期再次进行的地质学研究的成果。比如for-mations géologiques(地质赋型)、primaire(原生)、secondaire(次生的)、tertiare(再次生的)等十分专业的科学术语。可以看到,这是马克思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从其他学科借用概念的一次较为集中的表现,这里,地质历史流变中的赋型、地质赋型中历史进程中的原生、次生和再次生赋型等概念,都挪移到人类社会历史辩证法运动中来。这极大地改善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话语塑形的精准度。一是马克思重温和强化了自己在50年代的《伦敦笔记》中遭遇地质学中formations géologiques(地质赋型)的观点,在《伦敦笔记》的第13—14笔记本中,马克思曾经分别摘录过约翰斯顿的《关于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演讲》(Lectures on Agricultural Chemistry and Geology,1847)和《农业化学和地质学问答》(Catechism of Agricultural Chemistry and Ge-ology,1849)两本书。从地质学中,能够看到马克思已经使用过的formation(赋型)概念的另一种运用:在马克思先前的学术构境中,formation通常用来表示社会交往活动赋型生产方式(《德意志意识形态》),意识活动场境赋型观念话语的Ideenformation(《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却看到地壳“自然辩证法”历史运动中的地质赋型(geological formations)进程及其结晶化的具体机制,在《关于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演讲》中,马克思摘录了约翰斯顿对地质分层中由砂岩、石灰石和黏土的交替赋型(formation)为岩层的过程,也看到雨水冲刷将岩石赋型(rocky formation)的生成过程中泥砂重物质带离原产地的情形。也可能是这种经历,使马克思重组了历史辩证法的社会场境关系赋型社会定在的Ge-sellschaftsformation(社会赋型,《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我以为,马克思第一次自觉地将地质学研究中的“自然辩证法”地质赋型与社会历史辩证法发展进程中的经济的社会赋型链接起来,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他在讨论西欧资本主义生产从手工业到机器化大生产的转换进程时,明确提出:
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赋型(geologischen Formationen)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的社会赋型的筑模(Bildung der verschiedneu 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en)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在手工业内部,孕育着工场手工业的萌芽,而在有的地方,在个别范围内,在个别过程中,已经采用机器了。
显然,马克思确认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关系赋型,如同不同的地质赋型相继发生一样,在特定经济赋型中出现的生产方式筑模,并不是断裂式地出现的,而是在生产辩证法的自我运动中逐渐复杂和内嵌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技术赋型中,先是在手工业劳作中蕴育着工场手工业生产技能的构式,而后者又会历史性地构序后来机器化大生产的生产关系赋型和科技信息编码。而在19世纪70年代的专题性的“地质学笔记”中,马克思从地质构造学(Geognosy)看到了岩石生成(rock forming)和复杂矿物质形成(Minerals formed)以及完整的“矿脉凝结的赋型”(Formation of concretions and mineral veins)过程。显而易见,此处的Formation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对象性形态,而是一种功能性的正在发生的辩证运动状态。这使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运用formations historiques这一词组,有了更加明确的构境意向。
二是这里的地质学中地层赋型的原生、次生和再次生等术语。应该说,这一地质学科学话语编码的最早遭遇也是在《伦敦笔记》中发生的。在那一次摘录中,马克思在约翰斯顿《关于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演讲》中看到了这样的描述:古老的地壳的岩层中分为“原始地层(Primary Strata)”、“第二纪地层(Secondary Strata)”和“第三纪地层(The Tertiary Strata)”。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将地质学中的这种地壳运动赋型的历史性叠加和积淀方式,直接挪移到观察社会历史进程中来。而在此次“地质学笔记”中,马克思先在《农业要素、化学和地质学》中看到约翰斯顿讨论变质岩(Metamorphic rocks)中辨识的三种异质状态,即原生代(Primary)、次生的中生代(Secondary Mesozoic)和第三纪的新生代(Tertiary Cainozoic);然后,又在乔克斯的《地质学学生手册》的最后,读到了地质学中的通用地质分期:原始或古生代(Primary or Palaeozoic Periods)、次生或中生代(Secondary or Mesozoic Periods)和第三纪或新生代(Terti-ary or Cainozoic Periods)的重要提法。在这里,马克思才提出可以像地质构造中的不同时代地壳“自然辩证法”运动赋型一样,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原生赋型的原始公社的历史解体,也会生成一系列不同的历史辩证法次生赋型和再次生赋型。在这个隐喻性的话语塑形中,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原生赋型作为一种现实发生过的erste Gleichungen(原始方程式),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观察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参照系,原生的社会赋型中曾在的各种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场境,会成为之后次生社会赋型和再次生社会赋型复杂构式和生产方式筑模的基始性em-pirischen Zahlen(经验数据)。于是,社会生产的初期产品过渡到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场境,再发展到资本主义经济赋型中的复杂经济物相化编码中事物化关系颠倒和劳动异化场境,就有了直接的现实参照。这当然也深化了历史认识论的原有视域。
在这封书信的第二草稿中,上述这段话被这样改写了:
地球的太古赋型或原生赋型(formation archaïque ou primaire)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叠加(superposée)而成的。古代社会赋型(formation archaïque de la société)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
这里,马克思进一步强化了Formation概念的话语构序,并且干脆直接使用了自己在“地质学笔记”中摘录的内容,在对《地质学学生手册》中地质层级演变的分析中,乔克斯将地质层赋型视作不同时期岩层变动的叠加结果,并且区分了原生代中的“二叠纪”(Permian Period)和次生代中的“三叠纪”(Triassic)。马克思将地质学中的这种岩层历史活动不断积淀和叠加赋型的过程,类比于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中不同时期的关系场境演进的积淀和叠加。这也表示,每一个时代的社会赋型都会是一系列不同社会关系场境不断积淀和结晶的历史过程,并且是在自身中叠加过去社会赋型的场境。这让人想起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理解史前社会赋型简单结构的那个比喻,即人体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是一系列史前社会赋型不断积淀和叠加的结果,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从中可以看到过去不同生产关系的裂变和转换因素。不过,与各个时期地质层赋型不同的是,在社会生活的关系场境赋型中,这种历史辩证法运动中关系性的积淀和结晶不是直接改变某种物性存在结构,而是社会生活方式筑模的格式塔转换,外部社会物相化物性附属物的改变,比如从祭台到教堂,再到议会大厦的变化,只是重新激活不同生活场境关系的物性持存编码。依我所见,马克思的这些对科学话语的异域挪移,都大大地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话语构序。
其次,马克思提及自己在此前的古代史研究中所看到的毛勒对日耳曼古代史的研究。“德国的农村公社是从较早的古代类型的公社中产生出来”,在这种次生的公社里,“耕地变成了私有财产,然而森林、牧场、荒地等仍为公社所有”,这样,“毛勒在研究了这种次生赋型的公社(commune de formation secondaire)后,就能还原成它的古代原型结构(reconstruire le prototype archaïque)”。
这是过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史前社会历史分析中,对从奴隶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等不同所有制和经济的社会赋型中没有涉及的方面。现在他认识到:“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业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赋型到次生赋型的过渡时期。”这是说,在西欧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在原生的原始部族生活之后,曾经出现过一种从原始公有制到次生的私有制经济赋型的过渡时期,即农业公社时期。在书信草稿的三稿中,马克思进一步界定说,“农业公社既是原生的社会赋型(formation primitive de la société)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赋型(formation secondaire)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赋型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会是“再次生的社会赋型”了。更重要的是,在俄国等其他地区,今天仍然存在着这种次生的“农业公社”的社会赋型,并且,这种“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这使得它不必服从资本主义的modus operandi〔活动方式〕就能够吸收其各种成果),而且它还度过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被触动的时期”。这意味着,在不同于西欧的俄国等地区有可能出现一个摆脱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况且,马克思说,作为再次生的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système capitaliste)”,正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与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状态之中。在一段被马克思删除的文字中,马克思说,“它已经变为各种强烈的对抗、冲突以及周期性灾难的场所了;即使它表现得极其令人迷惑,它是一种由于社会回复到……而注定要灭亡的、暂时的生产体系”。“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crise),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type《archaïque》)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结束。”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1882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社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这一问题,显然是上述俄国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和革命的回答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我们看到,正是在这封书信草稿的第二稿中,马克思展开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分析:
在西欧,土地公社占有制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诞生之间隔着一段很长的时间,包括整个一连串的经济上的革命和进化,而资本主义生产不过是其中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
我觉得,这段表述应该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的最后表达。一是马克思给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专门增设了一个空间性的边界,即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研究。这也说明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本身的非普适性。二是再次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伟大历史作用和走向自身灭亡的必然趋势。也是在书信草稿的第二稿的最后,马克思继《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之后,再一次使用了法文中capitalisme(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概念。
综上,在马克思这两份最后的重要文本中,其实都可以看到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在后一文本中,他在对东方社会的历史性认识里,重新标识了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历史性,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提供了更加精准的逻辑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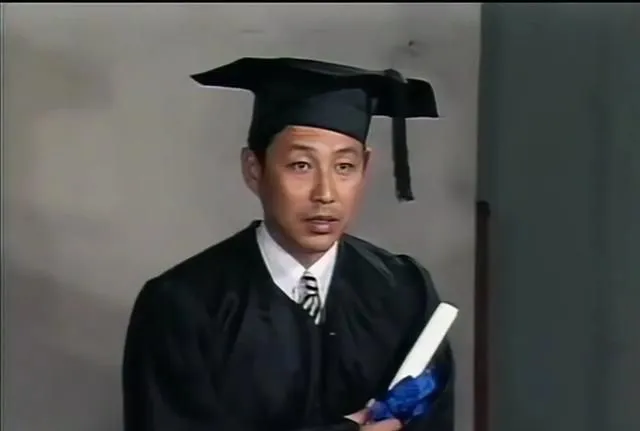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微信或手机浏览器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