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赵建,来自西京研究所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信用和财政、货币活动几乎都围绕着同一个行业运转:那就是房地产。
从地方政府到家庭个人,房地产成为了财富、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一个五千年农业文明社会,仅仅在几十年内就走向了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那份骨子里对土地的崇拜和眷恋,当然无法那么容易挥之即去。
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精神内驱力是中国人无与伦比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那么在工业化的下半场,房地产几乎就成为一种集合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宗教信仰。与其说是一辈子为其打工还贷的房奴,不如说是承载着一生物质保障和精神归属的“拜房教”信徒。
当年,被老百姓和地方官员簇拥着的许家印、王健林们,像不像“拜房教”的教主?当许家印被采取强制措施,恒大经营管理的各种内幕曝光被千夫所指之后,这一切又像不像一个教主人设的崩塌?过去他何以成为各地政府的座上宾,今天又为何成为人人唾骂的阶下囚?
今天,在冷清的售楼处感慨沧海桑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仅仅就在三年前,售楼处却像礼拜天、祭拜日的教堂、寺庙人潮汹涌?人们拖家带口的涌入其内,双手合十伏地祈祷,不过是为了抽个楼盘、楼层位置好的“上上签”。
个人努力奋斗多少年不如较早的贷款买一套房子,几十家上市公司的利润不如北上深的一套房子,再绚丽唯美的都市爱情故事在丈母娘眼里也不如一套房子,在一线城市只要抽签抽到买房资格就立即白赚几十万上百万......说的残酷一点,野蛮生长的房地产不仅扭曲了国民分配结构,还异化了国民精神结构。
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民支柱产业何以至此?问题当然不在房地产身上,行业是中性的。问题主要出在两方面:一是制度,另一个是人。
中国房地产体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于它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特有的二元结构,或者是一种市场扭曲形态:“一级”土地市场由地方政府垄断控制,“二级”房产市场却是完全市场化的。通过这种二元结构,中国在初步完成工业化进程后,为内部消化过剩的工业产能,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这也是很多经济学家宣称的“经营城市”的过程——地方政府卖地获取建设发展城市的“原始资本”,房地产商买地进行建房,进入城市的居民贷款买房获取市民身份。
这样就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土地—财政—不动产—金融—财富”的内循环引擎,在次贷危机导致外循环出口遭到挫折后成为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所以我们看到,次贷危机后中国的经济周期与房地产周期高度的耦合。
这个过程也是中国资产负债表周期大崛起的过程。一是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崛起。像经营公司一样经营城市,经营公司必须大幅扩张资产负债表,以满足政绩和升迁的需要。一个城市里最主要的资产当然是不动产,是房地产+基础设施。而资产怎么形成,靠细水长流的税收肯定等不及,所以就只能靠卖地获得资本化的收入,所谓土地财政;在此基础上进行地方平台融资,所谓土地金融。土地财政形成自有资金来源,土地金融形成借贷资金来源,共同推动了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大扩张。
二是城市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崛起,老百姓突然有了庞大的账面资产,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资产负债表的财富溢出效应也在显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老百姓的资产负债表是从负债端创造的,也就是通过借入房贷,通过杠杆快速的构建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如果房价不能持续上涨,居民的净财富并非看上去那么高,甚至在房价大跌的情景下变成负资产。而按揭贷款,可以看作是一个人一生人力资本的资本化——每个月拿出劳动工资的大部分收入作为房贷,其实就是一个资本化的过程。
而作为土地供给侧的地方政府,房地产需求侧的城市居民,两者的资产负债表创造活动离不开其中的中介方——房地产开放商和商业银行。没有他们,这个超级内循环体系就循环不起来。在地方政府和居民资产负债表崛起的过程中,银行和房地产商的资产负债表也迅速崛起。次贷危机以来,商业银行总资产扩张了近十倍,伴随的是广义货币M2的飙升,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的总和。而房地产开发商,原本是一个“轻资产”业务,但是为了在日益稀薄的利润率(土地价格越来越高)面前提高资本收益率,不得不采取充满风险隐患的“三高”模式,将自身的负债也堆的越来越高。
地方政府卖地,房地产商开发,商业银行房贷,城市居民买房,在这个轰轰烈烈的大循环过程中,财富神话被创造出来,房地产商一度成为中国现金流最为充沛,财富价值最高的行业。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房地产老板取代了煤老板成为中国电影事业的主要投资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中一半以上的俱乐部背后的金主是房地产公司,中国福布斯排行榜几乎全部被房地产老板霸占......
在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孩子的未来(教育),年轻人的婚姻,中年人的财富,老年人的养老,几乎全生命周期都寄托在一套套房产身上。我们常常称市场经济下人们的信仰是“拜物教”,这一阶段的中国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拜房教”。
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集体癫狂状态,其中最大的财富受益者房地产开发商老板自然更是变本加厉。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土地变现需要他们,另一方面买房心切的老百姓也需要他们,需要完成存贷指标的银行行长们更需要他们。在众星捧月的迷醉之中,房地产老板们仿佛真的成了“拜房教”教主。他们真的自以为,政府的财政、老百姓的财富、银行的信用——整个中国经济金融都与其捆绑在了一起。于是忽视了房地产这个行业的周期性,一直高歌猛进的借债、买地、开发、卖房。在这个过程中,也通过各种违规的利益输送结构将原本属于公司的财富“中饱私囊”。当房地产这种暴利行业长期存在的时候,其它的行业的营养就会被这个疯狂的物种挤占,企业家精神也会被扭曲异化。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资源,如何能健康成长和最优配置,取决于也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状况。
终于一切戛然而止。以“三条红线”为代表的房地产风险攻坚战已经过去两年多。从恒大暴雷到许家印被抓,期间留给社会的是上万亿的坏账、上百万人的烂尾楼、近千万人的失业、近乎枯竭的地方财政......捉拿许老板当然容易,但是如何处理好这个烂摊子则难上加难。“拜房教”崩塌了,信徒们也躺平了。经济陷入了需求不振的境地。
当初,很多经济“卫道士”们认为,“房地产不倒,经济不兴”——把房地产打下来,中国经济就高质量发展了,年轻人就有希望了,社会矛盾就缓和了,生育率就上来了。可今天的事实是怎样的呢?
事实证明,事情的复杂程度超出想象,一切并不是那么容易。房地产资产价格的确是下来了,但人们的收入和预期下降的更快,年轻人找工作都困难了,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如何买房?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是大跌了,但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却更加让人望尘莫及,房价-收入比依然很高,因为收入比房价下降的更快。“三条红线”刚出来的时候,静态测算也就是几家房企不满足,但是不到半年,几乎整个民企房企都全军覆没——很显然,“三条红线”忽略了事物是发展变化的,金融系统是“多米诺骨牌式”的勾连的。
最重要的还是地方财政。原来提供六七成收入的土地财政突然崩塌,但是新的来源一时半会又建立不起来,地方政府当下陷入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财政缺口和流动性危机。我一直无法考证熊彼特是否说过“财政是制度变迁的关键”这一句话,但实事求是的说,这句话是对的。因为财政是制度供给者——政府的收入来源。当地方政府的六成收入来自卖地收入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央地财税形态和社会治理体系,几乎就已经定型了。同样,当这六成收入被拿掉的时候,地方政府又该如何做来应对这场危机?
无非两种,一是开源,但税收却决于实体经济,短期内很难提高,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不降低就不错了,那就只能增加一些“营业外收入”,比如罚没收入;二是节流,公务员系统精兵简政、裁员降薪,大幅降低公共产品和服务,比如减少公交次数、环卫工人服务等。很明显,这两种做法都很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极限风险。更可能的做法是,中央自上而下顶层设计出一套“一揽子化债方案”。但归根结底也不过是地方债务中央化,中央债务货币化。那么这个方案后期会不会带来长期通胀和贬值的风险?我预判,为了规避这个风险,中央的化债方案肯定会采取“挤牙膏“的模式,不会采取大水漫灌的模式。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好的变化。今年以来的新型消费就在持续改善,这意味着人们的“拜房情结”一旦放下,就会发现其实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可以说,一念放下,万般自在。虽然总量上表现不明显,但是中国的消费型社会正在底部酝酿。消费不一定代表着乱花销,而是人们更懂的用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体验。事实上,我们对中国经济的韧性和自适应能力一直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想摆脱土地但又不得不屈服于土地,表现的是中国第一代城市化居民精神分裂的集体人格。依靠几代人、一辈子的积蓄,换取跳出农家的城市身份,换取后代高人一等的“起跑线”。教育、养老、医疗,新的“三座大山”,集中的背负在百十平方的钢筋混凝土空间之内,这一切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畸形。然而今天,在这个大时代落幕之后,在许老板被抓之后,人们的“拜房教”濒临崩塌的处境下,社会的财富应栖身何处,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应来自哪里,银行的信贷应投向何方?尤其是,市场经济大潮下人们精神信仰的物质载体该寄托于何处?这一切问题,暂时还是没有明确的答案。
或许,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一场没有下一个目的地的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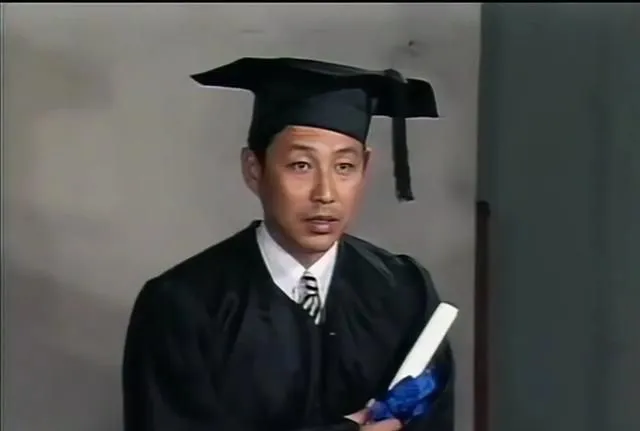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微信或手机浏览器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