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政治”(post-politics)是苏东剧变后一些国外激进左翼学者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它的本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状况下,在西方社会形成的一种掩盖政治性的政治统治。长期以来,这一概念并不受西方主流学术界的重视,也不为中国学界所关注。但事实上,在右翼民粹主义勃然兴起、全球局势日益走向动荡的今天,它可以成为理解当下这个时代的一把钥匙。
一、“历史的终结”与“后政治”的技术治理
1989年夏,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国家利益》杂志夏季号撰写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福山认为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相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因为其政体形式的严重缺陷和不合理正在日益走向崩溃,胜利的自由民主制度将会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成为人类的政治的终极形式,因此他宣告“历史”正在走向“终结”。在福山此文发表后不久,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陆续进入动荡,并接连陷入崩溃、解体与剧变,在二战后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冷战秩序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完全胜利而告终。在资本主义的外部敌人消失的同时,其内部的反抗力量——左翼势力也同时衰败。苏东剧变后,西方传统左翼政党也放弃了挑战资本主义的尝试和努力,以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民主党集体右转,彻底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和逻辑。一些学者批评说,英国工党等传统左翼政党完成了传统右翼政党所无法完成的任务:自我阉割掉最后一丁点批判资本的激进维度,开始使用他们的对手(新自由主义者)的语言和政策。这也就意味着,在西方社会内部已经不存在对资本主义秩序形成根本性挑战的政治力量,一切带有超越性的政治理想都被废弃了。撒切尔夫人因而宣称,尽管资本主义不是最好的社会制度,但是人类“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
面对20世纪捌玖十年代之后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转型与思想界的转向,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在区分政治与治安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终结论”。朗西埃认为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中,政治已经不再是对一个替代性的更美好社会的追求,而变为了一种围绕着“生产”和“经济增长”而进行的“掌舵”的艺术。治安逻辑取代了政治的逻辑,政治因此走向了终结。政治的终结也就意味着民主的终结。朗西埃把当代西方虚伪的代议制民主称之为一种“后民主”,即一种“共识性民主”。“共识性民主”以“民主”之名,实质上取消了“民主”与“政治”,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在这种民主形式中被排除了。在朗西埃所区分的治安与政治的基础上,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等西方左翼学者分别提出了自己对于“后政治”的理解。墨菲指出,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的隐退导致了一种否定对抗的自由主义观念的泛滥,形成了一种遮蔽对抗的“共识政治”,“在当今时代处于支配地位的共识性政治——它远远不代表民主的进步——表明我们正生活在雅克·朗西埃称之为‘后民主’的时代。”墨菲明确使用“后政治”一词来表述朗西埃所阐述的“后民主”现象。她指出,尽管朗西埃没有使用“后政治”一词,但他所剖析的现象已经涉及到了“后政治”的本质问题:“朗西埃在此指出的东西——尽管它使用的是不同的词汇——就是后政治的方法对对抗维度的抹除,而这一维度确是政治的构成部分,正是它赋予民主政治以内在的动力。”齐泽克关于“后政治”问题的讨论始于1999年出版的《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一书。在这本书里,齐泽克在朗西埃“政治”与“治安”划分的基础上,将朗西埃的“后政治”概念与巴里巴尔的“过量”等概念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对于“后政治”的理解。他将“后政治”理解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指出“后政治”不再仅仅是压制政治,而是更有效地排除它,“政治(诉讼的空间,其中被排除者可以抗议加之于他们的错误与不公正)被从现实的符号化回归中被排除了”。齐泽克将“后政治”的本质定义为“经济的非政治化”,指出在自由主义取得了历史性胜利的“后政治”时代,政治被降低为实用主义的专家治理,成为了一种强调运用“必要的专家知识与自由的审慎”来面对具体问题和需求的庸俗的务实游戏。
在这个放弃宏大政治目标、失去真正政治热情的“后政治”时代,各种“哲学乌托邦”或“意识形态”似乎都走向了终结,具有真正对抗性的“政治”不仅被压抑,而且被彻底“排除”了。政治被降低为一种由专家代表的治理性技术活动,而不再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争斗。一切社会矛盾似乎都可以通过技术性的协商、管理、调整而解决。在社会治理层面,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成为了一种被排除在政治辩论之外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一切社会公共问题也都被归结为技术性的治理问题;在公共领域层面,大众媒体被资本深度同化而成为了“伪公共领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政治批判功能,民众也日益去政治化和犬儒主义化;在社会运动层面,西方左翼主导下的社会运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而走向了以身份认同和多元文化主义为核心的身份政治,因而无法形成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政治挑战,沦为了新自由主义的同谋。
在这个时代中,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成为了所谓的“普世价值”,获得了一种压倒性胜利,成为“后政治”时代公开标榜的意识形态。这种“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霸权将一切试图根本改变现存秩序的意图或实践指责为“极权主义”,将共产主义视为和法西斯主义等同的20世纪“政治毒瘤”。尽管自由主义者们也承认资本主义秩序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但认为这些问题只是通过调整和改良就可以得到解决的技术性问题。任何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秩序的努力,都被指责为一条可能走向“极权主义”的路径而被禁止,“墨守成规的自由主义流氓便可以在为现存秩序辩护的过程中找到虚伪的满足:他们知道有腐败,有剥削,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但是,他们把所有试图改变事物现状的努力都指责为具有道德上的危险性,是不可接受的。”
二、“后政治”的危机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与自由主义者的乐观预言相反,冷战的终结并没有带来一个自由与和平的普遍主义世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肯·乔伊特所指出的,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终结并不是胜利的时代,而是危机和创伤的开始,即他称为“世界的新失序”的播种期。在他看来,所谓共产主义的终结“应该被比作灾难性的火山喷发,最初和最直接的影响只围绕着政治‘生物区’(比如,其他列宁主义政权),但它最有可能对半个世纪以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定义并号令世界的边界和身份产生一种全球性的影响。”“后政治”时代并不是一个政治终结的时代,是一个以去政治化的形式掩盖着政治对抗的时代;“后政治”时代也没有实现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是以非意识形态的形式掩盖着真实的、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统治之下,人类社会围绕着阶级、种族与文明的对抗和冲突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社会深陷经济危机与债务危机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移民、宗教、阶级等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恐怖袭击、难民危机等事件层出不穷。在严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困境面前,在“后政治”的政治中陷入功能危机的传统政党和政治精英对此无能为力。在此背景下,以种族主义和排外倾向为主要特征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迅速崛起,并进入西方的主流政治舞台。在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性质的政党的得票率达到了43%;右翼民粹主义分子所获得的议会席位从2009年的38席,大幅度提高到129席,其中包括来自14个国家的15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其中,法国国民阵线党获得了24.9%的票数,成为法国在欧洲议会中的第一大党。2017年,成立仅4年的德国另类选择党获得了将近13%的选票,首次成为联邦议院第三大党,仅次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以及社民党这两大老牌政党。近几年来,伴随着全球政治秩序的进一步重组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战争等事件的冲击,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得到了更快速的发展。在202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首轮投票中,国民阵线党候选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得票率达到了23.15%,得票率仅次于马克龙,排名第二;在第二轮投票中,玛丽娜·勒庞获得了41.46%的选票,尽管低于马克龙58.54%的得票率,但二者的得票差距与2017年大选时相比,已大幅缩小。2023年6月25日,德国另类选择党候选人罗伯特·泽塞尔曼(Robert Sesselmann)在图林根州松讷贝格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获胜,这是该党自2013年成立以来首次赢得地方行政长官选举,被英国《卫报》等媒体称为德国政治的“分水岭时刻”。在这种状况下,一些学者甚至用“民粹主义大爆炸”(The Populist Explosion)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右翼民粹主义在全球蔓延的趋势。
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方的蔓延,无疑表明在苏东剧变后形成的“后政治”秩序,已经难以为继。朗西埃、墨菲、齐泽克等学者在论述“后政治”现象时,都将右翼民粹主义视为“后政治”危机的体现。朗西埃将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后民主”时代的精英政治结合起来,指出各种基于身份、血缘、宗教的极右翼势力或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都是这种“后民主”时代专家统治的产物——“财富与知识所组成的寡头联盟声称要掌控所有权力,并且拒斥人民分化与多样化的可能。但这两种原则的分化开始从各个方向回归。这回归伴随着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以及身份主义者与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运动——他们反对寡头共识,并诉诸旧有的出身与血缘原则,以及某种根植于土地、血缘和他们祖先宗教的社群。”墨菲在阐述其竞争性多元民主的同时,将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归因于“后政治”时代消除了对抗的“共识政治”模式。墨菲指出,尽管自由主义宣告了集体认同的终结,但是集体性维度不可能在政治中被完全清除,这种被传统政党抛弃的集体认同逐渐被右翼民粹主义所重新复兴。齐泽克更是明确地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视为“后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在齐泽克看来,尽管“后政治”的治理逻辑一直试图排除对抗性的“政治”,但是这样的排除不可能彻底实现,被“后政治”排除的真正政治激情,必然以一种新形式种族主义或非理性暴力方式回归——“所以,今天‘非理性’暴力的兴起应当和我们社会的去政治化有紧密的关联,也就是和真正的政治维度的消失有关,政治已经被转译成社会事物‘管理’的不同层面:暴力以社会利益等方面来解释,至于那些无法解释的剩余只能显现‘非理性的’样子。”
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存在,一方面表明“后政治”的政治已经陷入了危机,另一方面它又是“政治”重新回归的一种表现。墨菲指出,让-勒庞等右翼民粹主义者提出的方案当然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人们却不能否认其话语的政治性质。”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指出,尽管右翼民粹主义者(他称之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并不会终结资本主义的危机,但是“他们会让政治重新登台,并让那些变为全球化失意者的中层和底层人永远活在政治的回忆中。”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打破了“后政治”时代“共识政治”的幻象,提出了一些鲜明挑战新自由主义体制和“自由-民主”霸权的政策主张。正因为如此,齐泽克将右翼民粹主义视为在“后政治”时代的政治舞台上唯一抱着真正的政治热情,抵抗自由民主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的力量,“新右翼民粹主义者是当今唯一用反资本主义话语对人民说话的‘严肃的’政治力量,尽管他们是打着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宗教的旗号(背叛我们国家的普通劳动人民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围绕着“人民”与现有体制之间的对立,缔造出了一种“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相对关系。这种关系取代了已经被弱化的左右对立,形成了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和政治对抗。如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认为,“民粹主义情绪的崛起意味着政治两极分化和更具对抗性的政治风格的回归。”尽管这种对抗性带有一定的暴力和非理性色彩,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对抗性根源于在“后政治”时代被掩盖和压抑的社会矛盾,它是在民众中现实存在的政治情绪和政治诉求的表达,“右翼民粹主义组织及其运动的确夹带了种族主义、本土主义或仇外观点,但其控诉往往指向问题的真实所在。”
但是,主流的自由主义话语依然不愿意从政治的视角来理解右翼民粹主义,而是将其视为一种道德化的“邪恶的敌人”。在墨菲看来,自由主义话语并不是将右翼民粹主义视为一种从政治上要与之“战斗”的对手,而是从道德的层面将其视为“邪恶的敌人”——在“好的民主人士”与“坏的极端右翼”之间划出一条边界。对于这些“邪恶的敌人”,主流社会并不是要跟其进行严肃的政治争论,而是要将其视为某种“道德疾病”并彻底根除。他们甚至不愿意严肃地分析这种现象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原因。在道德谴责替代了真正的政治分析的情况下,西方主流社会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方法,只限于划出一条把受到感染的人隔离“检疫”的“防疫封锁线”。这种对待右翼民粹主义的态度,导致西方主流社会和学术界无法真正认识到右翼民粹主义所产生的原因,不愿意承认右翼民粹主义兴起所暴露出的西方政治危机,因而也无法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
三、历史的“空位期”:旧的秩序趋于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
右翼民粹主义以种族主义和排外倾向为主要特征,并带有强烈的非理性和暴力色彩。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加剧了西方社会内部不同族群、宗教群体之间的矛盾,形成了愈演愈烈的暴力冲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指出:“右转趋势与大屠杀,暴力的种族主义和厌女症等社会痼疾的蔓延相伴而生并非偶然。在美国,社会结构破裂,大规模枪击事件的频率在增加。每天至少有60%的几率发生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而有17%的几率发生两次大规模枪击事件。在印度,极右势力的兴起带来了私刑的泛滥,而在德国,作为德国重要政治力量的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的出现与纳粹式的言论和组织的兴起相吻合。”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政策还将会导致全球社会的激烈对抗,甚至不排除擦枪走火、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将右翼民粹主义理解为法西斯主义的先声。如约翰·朱迪斯指出:“今天的某些民粹主义运动与两次世界大战时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确有相似性:振臂高呼的领导角色;炫耀民主规范;拿某一外部族群作替罪羊。”从其意识形态、阶级基础和运动方式来看,右翼民粹主义与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从意识形态来说,二者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从阶级基础来说,二者都是基于“垄断资本(今天的垄断金融)与中下层/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之间形成的政治集团或同盟”;从运动形式来说,二者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建制化倾向,主流政党和建制派政治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被民众逐渐抛弃。
当然,当下西方的右翼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还不能完全等同。一方面,与具有明显扩张主义倾向的法西斯主义相比,右翼民粹主义并没有很明显的扩张野心。相反,右翼民粹主义反对建立超国家、超民族的共同体,“如果说民粹主义令人厌恶,其原因也完全在于其所宣称的排他性的国家主义,而非征战全球的野心。”另一方面,与走向政治独裁的法西斯主义不同,今天右翼民粹主义并没有废除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制的企图。齐泽克指出:“旧时代的威权民粹主义(如法西斯主义)是要抛弃形式上的代议民主制,并真正接管国家,以强加一种新秩序。与之相比,今天的民粹主义并没有一个连贯的新秩序愿景——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积极内容,不过是贿赂‘我们自己的’穷人、为富人降低税率、把仇恨集中在移民和我们自己腐败的精英外包工作等等上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民粹主义者并不是真的想要摆脱已成建制的代议制民主,去完全掌握权力。”因此,在当下的政治形势之下将右翼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无疑“夸大了民粹主义的危险性——民粹主义政党从不鼓吹战争或解散议会。”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因为右翼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着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在资本主义危机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中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因素很容易与暴力行动相结合,向法西斯主义的方向转化。
面对这样的时代浪潮,全球社会将要何去何从?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借用了葛兰西提出的“空位期”的概念,来描述当下全球所处的历史阶段。所谓“空位期”,是一段旧的秩序已经被摧毁、但新的秩序还未建立的不确定的历史时期。在2016年以来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的冲击下,旧的全球资本主义“后政治”秩序崩塌了——“这个世界的政府为了不失去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接轨的机会,对他们国家的民主做了后民主式的、中性化的处理。”但是在旧秩序崩塌的同时,新的秩序还远未到来。这样的“空位期”是一个极具有不确定性的时期,“一切皆有可能,但没有什么能带来结果,尤其是人们期待的结果。”在这样一个时代浪潮之下,西方社会将要何去何从?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围绕着在特朗普与希拉里之间应该选择哪一个的问题,在西方左派中曾经引起过一些争议。弗雷泽将这种选择称之为一种在“反动的民粹主义与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霍布森选择(the Hobson’s choice)”。当时很多西方左翼秉持着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态度,认为应该选择危害性较小的希拉里。但是在弗雷泽看来,希拉里所代表的“进步新自由主义”虽然以为女性、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群体争取权益的“进步”面貌出现,但是它事实上代表着华尔街、好莱坞、硅谷等金融资本或服务业资本的利益,形成了一种“进步力量”与金融资本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进步力量与认知资本主义特别是金融化的力量,有效地扭结在一起。”这个联盟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上将广大的白人工人阶级推到了对立面。弗雷泽据此指出,西方左派在大选中所秉持的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所起到的效果是让左派继续“失声”,从而“实际上成为滋生新的和更可怕的对手的温床”。希拉里所代表的“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事物,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都是“无限制的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弗雷泽认为,尽管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义的种族主义和反移民倾向激起了很多的政治恐惧,但我们也不应当与以希拉里为代表“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联盟以共同反对右翼民粹主义,也不用哀悼“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在大选中的崩盘。特朗普的胜利标志着以身份政治为核心议题的左翼力量与金融资本所结成的政治联盟的失败,但是他身为总统却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也没有形成一个新的牢固的霸权,因此形成了一个“国家权力交接时期的空白,一个可以争夺民心的开放和不稳定的局面。”因此弗雷将这种局面视为“建立一个新的‘新左派’的大好时机”。西方的左派和进步力量应当拒绝在“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而应该努力“打造解放和社会保护相结合的新联盟来反抗经济金融化”,将被压迫的痛苦和愤怒转化为“深刻的社会改革和民主政治‘革命’”——这就是桑德斯的政治方案。
与弗雷泽一样,齐泽克也反对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但与弗雷泽不同,齐泽克明确表达了对特朗普的支持。在齐泽克看来,希拉里代表着一种维持新自由主义共识和既有统治秩序的力量,“希拉里共识传递给左派的信息是:什么都能给你,我们只想留下最本质的东西——全球资本畅通无阻的运行。我们可以对你们一切文化要求让步,只要不危及全球市场经济就行。”也就是说,希拉里通过在文化等议题上表现出一种“进步”态度,而掩盖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问题——经济领域的资本剥削。而尽管特朗普站在了一种错误的立场,但是他打破了自由主义共识和维持现状的惯性,“特朗普把我吓坏了,但正因为有了这个人,自由主义中间派的霸权才不再是铁板一块,出现了一道裂缝。”这种状况为新的政治重组和激进左派的重新崛起打开了空间,“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没有特朗普,就没有桑德斯了。”
弗雷泽和齐泽克等人之所以推崇桑德斯,是因为他代表的是一种面向经济和阶级议题的左翼政治方案。在2008年之后,在资本主义日益陷入危机的大背景下,受金融资本剥夺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日益走向联合,掀起了反抗资本统治的运动。如2011年前后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1%对99%的口号,动员了相对剥夺感最为强烈的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让经济议题重新回到了美国社会。在2016年的大选中,桑德斯把“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提出的“99%对1%”的诉求注入竞选纲领,提出了包括对富人增税、强化金融监管、公立大学教育免费、提高法定最低工资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尽管桑德斯在两次总统大选中均未能在民主党内“出线”,但是不能否认他在美国民众中尤其是年轻人中强大的影响力。
“桑德斯现象”的出现,代表着从左翼立场出发对于“后政治”共识的突破。弗雷泽指出:“桑德斯打破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反对‘受操纵的经济’——这一模式在过去三十年中以越来越大的规模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当然,桑德斯自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与革命策略,而是依然在资产阶级代议民主的框架内进行政治活动,并对希拉里等民主党建制派依然抱有一定的幻想,带有浓厚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但是他对于经济议题和阶级议题的关注,重新调转了西方左翼的航向。对于当代西方左翼来说,只有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才能突破“后政治”给西方和全球带来的历史困境,抵御右翼民粹主义所带来的威胁。
第一,在指导思想方面,左翼要告别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范式,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时,没有陷入对外在现象的经验描述,而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变规律,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和资本逻辑的总体性批判。对于当下的西方左翼来说,只有告别沉迷于“话语”或“微观政治”的后现代理论范式,回归总体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深刻认识当下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探索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路径。第二,在斗争主体方面,左翼要回归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运动。伴随着西方左翼向文化和身份议题的转向,工人阶级在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中的主体地位被抛弃了。只有重新回归阶级身份,在阶级同一性的基础上实现不同社会身份的工人阶级的联合,才能使西方社会从右翼民粹主义的泥潭中解脱出来。第三,在斗争策略方面,左翼要告别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斗争,而回归集中统一的政党政治。在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过程中,西方左翼出于对“官僚化”的恐惧和排斥,走向了一种无政府主义式的自发抵抗运动。他们排斥政党等“中心化”的政治组织,拒绝制定统一的、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纲领,制定明确的反资本主义议程。这种状况使得西方左翼所主导的社会运动陷于一种分散、混乱的局面,无力抵抗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西方左翼要摆脱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就应当从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汲取经验,重新发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遗产,重构一种以无产阶级政党为核心、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政治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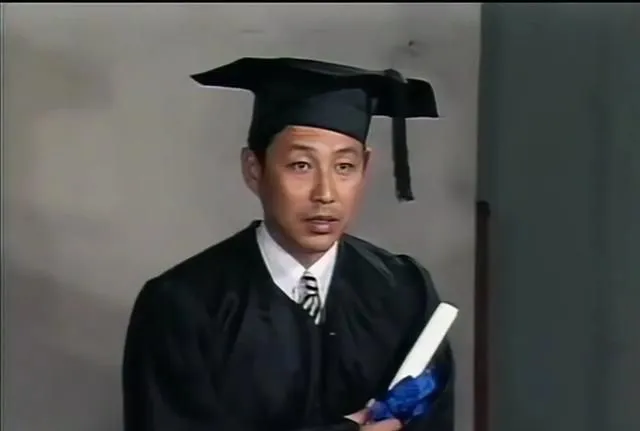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微信或手机浏览器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