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国家官僚制批判及其方法论意义
作者:张炯,原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
摘要:马克思的国家官僚制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青年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官僚制思想;在经历1848年革命的洗礼之后,马克思转而批判法国的国家官僚制;到19世纪70年代初,马克思批判现代民族国家的官僚制,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经典命题。马克思对国家官僚制的批判切入了19世纪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的国家官僚制批判因地、因时、因势而变,我们既要明确这一批判的历史性与历史限度,也要看到它对审视现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启发意义;不管批判的焦点与细节如何变化,始终不变的是坚持无产阶级根本立场。
关键词:马克思;国家官僚制;现代民族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上的“制度建设”问题被提上议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致力于寻求与之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资源。马克思当年留下了许多批判国家官僚制的文字,但是受限于其本人所处的历史时期,其意义始终没有被很好地揭示出来。本文试图梳理马克思国家官僚制批判的发展进程,继而揭示其方法论意义。
一 青年马克思对普鲁士官僚制的批判
“官僚制”是马克思在1843年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自行引入的概念,它既可以指国家行政系统,也可以指在这一系统中工作的人,而且通常指向后者。马克思基本遵循了当时德法学界、报界和政界对“官僚制”的使用,即“它不仅被视为一种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的治理形式;它也是这些官员的集体称号” 。它兼有“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内涵:“贵族制”大多数时候指的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而不是一种治理形式;而“民主制”则通常指的是实现人民意志的制度形式。马克思那里“官僚制”既指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又指向一种制度形式。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里用了11节内容(第287-297节)讨论“行政权”,马克思认为这些不配称为哲学的阐述,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普鲁士法典中。马克思从根本上反对黑格尔分离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做法,前者代表普遍利益,后者由特殊利益组成,然后通过等级制度、同业公会的独立权利和官员的崇高道德,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得以重新结合。马克思认为这是一幅完全扭曲的画面: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之间的理论对立是虚幻的,官僚们用它来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辩护,一纸资历是他们脱离市民社会的标志,国家的真正目的淹没在秘密的、机械的行动中,淹没在对权威的信任以及对更高职位的追求中。行政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只有当特殊利益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时,官僚制才会彻底结束。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揭示了德国官僚制的一系列经验层面的特征:首先,官僚制的特点是无能:“上层指望下层了解详情细节,下层则指望上层了解普遍的东西,结果彼此都失算。”但这种无能却已经变成了一种制度的牢笼:“官僚制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其次,官僚制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所以,“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信念,对官僚制来说就等于泄露它的奥秘”。正是这种神秘化导致人们对权威的崇拜:“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神化权威则是它的信念。”最后,官僚制内部是“粗陋的唯物主义”和“粗陋的唯灵论”。一方面,“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即官僚分子)的私人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另一方面,官僚制“想创造一切”:“它把意志推崇为始因,因为它只是活动着的存在,而它的内容是从外面得到的。……对官僚来说,世界不过是他活动的对象而已。”
对“官僚制”的批判构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既没有完成和发表,而且其内容在之后也没有被马克思自己引用,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这样处理“官僚制”问题?首先需要明确,马克思那里的“国家”和“官僚制”实际上是同义词:“没有对官僚制的界定,国家亦不能成其为国家。” 《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道:“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 这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而单纯的政治革命无法真正扫除这种有组织的暴力,还需要一场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根本转变的社会革命。但是这一转变暂时只是理论上的,现实中的官僚制却愈发表现为一种近乎自治的力量,它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发展着,以自己的利益统治着社会的其它部分。这与马克思后来对国家问题的思考是相左的。因为在马克思的思想谱系里,官僚制乃是一种寄生附属物,就像马克思眼中路易·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法国的行政权力有着庞大的官僚和军事机构,这是一个寄生在法国社会上的有机体。如果说,仅仅执行政府形式安排的机构就能够对社会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那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两极分化也会被这种国家官僚制所制止或调和,如此一来,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无用武之地”了。实际上,1848年革命时期的法国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这给马克思的这一信念带来很大挑战。
我们不禁怀疑,青年马克思处理官僚制的方式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把“官僚制”贬低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更多问题。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官僚制在德意志各邦兴起,并由于任何利益集团都无法支配其他利益集团而获得异常的独立性。这个过渡阶段在德国持续的时间比在其他地方都要长,但即便如此,它根本上仍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三年之后,马克思说,1848年的普鲁士自由派政府在柏林三月革命之后成立,它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必然取代旧的官僚制。“旧官僚不甘沦为资产阶级的奴仆,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资产阶级的专横导师。” 然后到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后文称《雾月十八日》),马克思看到法国广大的小农阶级为官僚制提供了合适的基础。路易·波拿巴的政权看似代表农民群众,但实际是维护资产阶级秩序,这种情况充满了矛盾。然而不可否认,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里的国家官僚制批判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 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国家官僚制的批判
有必要先明确如下一种区分,即“作为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之必然附属的官僚化”和“作为一种病理症状的过度官僚化”。波拿巴主义国家的“官僚制”实际指后者,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称国家官僚制为“寄生机体”。但是马克思还肯定了如下观点:路易·波拿巴能发动政变并最终称帝,法兰西的国家官僚制起了很大作用。在路易·波拿巴彻底接管法国之前,官僚制看似隐藏在市民社会和由普选产生的议会的背后,而在他接管之后,法国的国家机器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
马克思的这个说法暗示了国家机器不能以其自己的力量直接登场,法国的独立只有在路易·波拿巴作为超越议会的皇帝而独立存在之后才有可能。路易获得至上权威的过程很有特点:“路易·波拿巴只是用掠夺而来的东西再分配,结果人们却将此作为‘赠与’来接受。因此,他被再现为向一切阶级赠与的至高存在者,即皇帝。也就是说,通过将‘赠与-还礼’这一相互交换的外在表现,投射到由国家机器所实行的‘掠夺-再分配’这一实际交换上,路易·波拿巴作为皇帝的权力才得以确立起来。” 实际上,这个过程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存在。虽然大革命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但是革命真正活跃的能动者是城市小生产者和工匠,而且最终掌权的也并非资产阶级,而是拿破仑·波拿巴。1848年革命把这个“桥段”重演了一遍。
1848年革命带来的问题是,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决的预测至少表面看来“落空”了,而且法兰西路易·波拿巴和普鲁士俾斯麦的出现似乎证实了国家的独立性。尽管如此,马克思依然坚持认为,一旦废除了经济基础层面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那么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国家也会消失。虽然马克思后来把国家放到更大的研究蓝图中考虑,但是对于现实的革命而言,国家问题又是马克思无法回避的。这背后存在着“理论家”与“革命家”之间的张力,作为理论家和观察者的马克思显然比单纯的革命家要看得更远,如何依托国家机器来保存革命的胜利果实是当务之急。然而一旦触及“国家”,那么“官僚制”就是挥之不去的影子,“国家”这朵云投射在地上的阴影就是“官僚制”。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里揭示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代议制民主的资产阶级本质,并追溯了秩序党将法国交到一个骗子手中的轨迹。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一幅让人“心惊肉跳”的“可怕前景”。波拿巴主义国家的成因至今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雾月十八日》已经同时涉及“结构”与“个体”两方面,而且从他之后的研究轨迹来看,马克思更加偏重“结构”的一面。不过现在看来,马克思在这两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欠缺:一方面,在一定的历史情势中,个体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治制度的发展走势,而结构本身推动变革的力量往往不那么强大和明显;另一方面,即便结构的能量可能会因为其内部的阶级派系斗争而消耗殆尽,但结构的自愈能力依然强大。比如,经政变建立的、不道义不合法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苟延残喘了18年,而在战乱中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竟风雨飘摇了70年。正是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更迭之际,马克思再度进入国家官僚制批判的论域,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经典命题。
三 马克思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批判
《雾月十八日》的第二版序言里提到,这本小册子“对于清除如今流行的、特别是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马克思这样说的用意何在?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区分了“进步的凯撒主义”与“反动的凯撒主义”两种形式:“如果恺撒主义的干预协助进步力量获得胜利,即使搀杂了一定的妥协和局限,它仍然是进步的。如果它的干预造成反动势力获胜,其中虽然也有妥协和羁绊,它们却具有与前者不同的价值、深度和意义。恺撒和拿破仑一世是进步的恺撒主义的代表,而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则是反动恺撒主义的代表。” “进步的凯撒主义”同时具有“量变”与“质变”的特点,“它表现出国家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有如此多的、如此本质的创新,它们足以代表一场彻底的革命”;“反动的恺撒主义”则仅仅是有限的量变,“不存在一种国家形式向另一种国家形式的过渡,只是同一种类型的国家沿着原来路线的演变”。
在19世纪70年代初,正是这种“反动的凯撒主义”开启了以德意志帝国为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形式。1875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成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后的“哥达纲领”既是具体情势的产物,又表露出拉萨尔主义倾向,而且它还涉及了现代民族国家与国际观念的对立。马克思并不否认工人阶级斗争的舞台首先在国内,然而,合并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国际主义仅仅意识到“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这一结果,而不是“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 这一过程。也即是说,它回避了阶级斗争过程中的国际工人联合,而只是把这种联合作为结果,如此就暴露出拉萨尔派甘愿放弃斗争而寻求与当局妥协的意愿,暴露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国际信念上的薄弱。
与现代民族国家问题相对应,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里,相应地存在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政治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既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明确声明它是在德意志帝国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内活动,而这只有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民主共和国内部才是适宜的。这意味着“哥达纲领”的嫁接是多么不伦不类,而且其中提出的政治要求全是民主派在1848年的法国议会形式里早就使用过的陈词滥调,如普选权、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国民军等等。庸俗的社会民主派曾把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视为“千年王国”,他们没有意识到,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之上的国家形式将是最后的国家形式,而在这种国家形式下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应地也要进行最后的决战。1875年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把“国家”理解为“政府机器”、一种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的存在,这表明德国工人党的国家观仍然停留在1848年的水平,即“国家似乎成了完全独立于社会并对它进行奴役的东西”。
马克思此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体现了其对国家阶级统治职能的判断。资产阶级作为既有社会秩序的受益者,在面对底层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反抗时,必然会想方设法利用既有国家机器来压制反抗者、维护社会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是一种镇压和剥削的力量。《雾月十八日》第二版较之第一版的改动更加体现了马克思在面对这一问题时的谨慎态度:一方面,他肯定国家中央集权制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上层建筑,另一方面,他肯定军事官僚制在对抗过去的封建制度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这两方面一并使“打碎国家机器”的判断更加契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原理。
晚年恩格斯对国家官僚制的阶级统治功能作出更细致的解释:“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恩格斯并没有说国家“实质上”超出阶级斗争,而只是说国家“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且国家也没有“彻底解决”冲突,而只是“缓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国家把这些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如果这种秩序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那么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之上的国家官僚制就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来防止对抗发展为革命的暴力武器;而如果这种秩序是新兴无产阶级社会的秩序,那么国家就是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用来防止反革命力量的暴力武器。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暴力”的国家只是暂时的:“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
四 马克思国家官僚制批判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国家官僚制批判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欧洲的社会政治变化,它切入了19世纪的现实,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对于马克思的国家官僚制批判,我们并非要全盘接受其观点和结论,而是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反思其展开的过程。
首先,马克思的国家官僚制批判因地而变、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因地而变”,即因具体地区和国度的不同而变化。青年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是普鲁士政府,1848年革命之后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到1875年则是统一不久的德意志帝国。马克思注意到不同地区与国度的官僚制结构有所差异,既坚持了具体制度具体分析,也将具体制度的分析纳入其国家官僚制批判的总体之中。“因时而变”,即因自然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从退出《莱茵报》之后到1848年革命之前,马克思对国家官僚制的批判是彻底的激进的。在历经现实的革命之后,马克思自觉地以唯物史观来观察和分析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国家官僚制。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被当局残酷镇压,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与全德工人联合会为顺应德国国内情势而合并拟定《哥达纲领》之际,马克思再度批判了以德意志国家为代表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官僚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经典命题。“因势而变”,即因情势(尤其革命情势)的盛衰而调整。1848年革命之前,社会阶级反抗当局政权的情绪日益高涨,马克思批判的焦点在于推翻既有的国家官僚制。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不得不流亡英伦,这一经历为其回到书斋反思国家官僚制提供条件。再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革命的情势再度高涨,虽然这一势头很快就被反动势力所压制,但是马克思意识到现代民族国家开始成型,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也需要形成自身的国家理念,即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其次,既要明确马克思国家官僚制批判的历史性与历史限度,也要看到这一批判对审视现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意义。官僚制问题吸引了许多批判19世纪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正是马克思对官僚制的这种特殊态度,使得他与当时的革命者、思想家区分开。他不仅揭示了作为一种经验现象的国家官僚制,还揭示了官僚制内部斗争的复杂,这有助于我们透视当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后者的国家官僚制表现为一个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依赖关系代替由客观的劳动分工所定义的关系,在这里,党派集团的分组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叠加在等级制度的形式之上,并且往往根据他们自己的需求不断地重塑它。在主要党派之间的具体职位分配,就像过去政权更迭的时候瓜分战利品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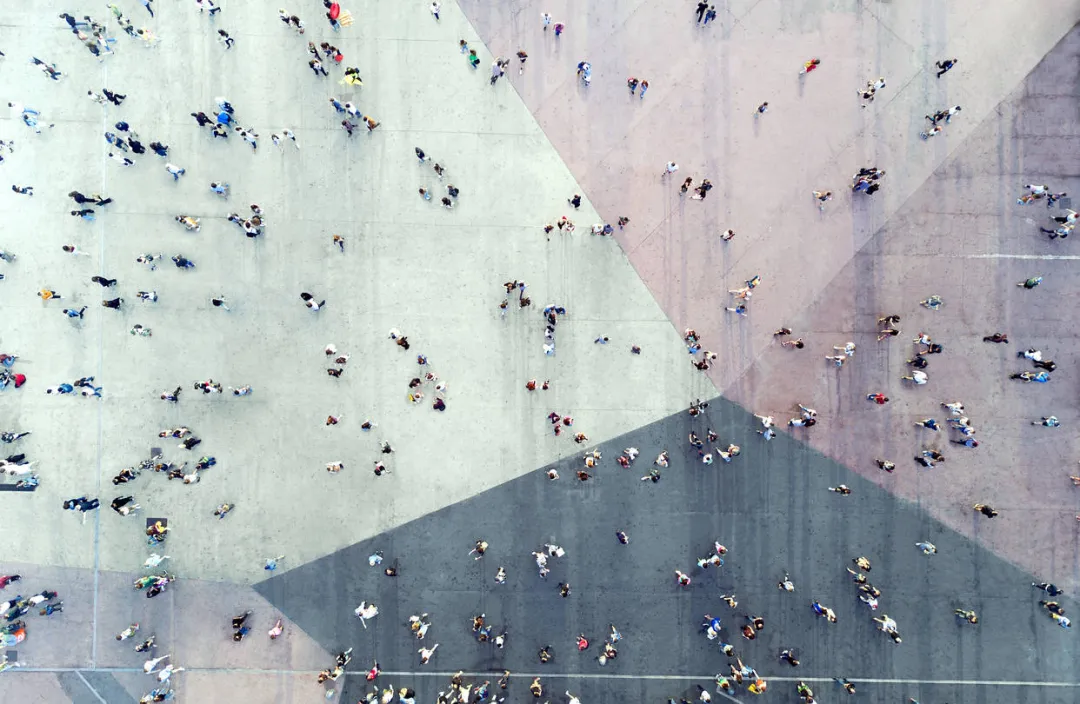
最后,国家官僚制批判应始终坚守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前提。“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阶级斗争的暴力工具。为此,马克思会认为巴黎公社在利用国家的暴力权威上尚缺火候,而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要想在一个国家里取得政权,首先必须采取的措施就是“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才能赢得“持续行动的时间”。虽然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多数人的支持,而且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也确实是多数人的专政,但这个专政本质上是“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之所以要延续国家镇压性的阶级统治功能,直接原因是为了维护革命的胜利成果。国家是社会受到威胁时的防御机构,而这些威胁往往又不断以暴力的形式出现,所以国家为了实现其功能,也不得不是一种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是一种作为“手段”的暴力。对于一个政治组织来说,“暴力”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常用的手段。但是,一旦其它手段失去效力,那么暴力才可能成为政治组织的专用手段,而且是最后的手段。作为手段的“暴力”是国家所特有的,也是它的性质中不可或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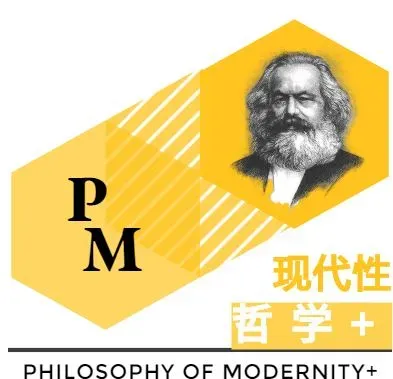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