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出来一段时间了,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18%,而总和生育率更是跌倒了1.3,不仅低于北欧地区,甚至低过了日本。
于是,社会舆论席卷而来,大家讨论的无非三个问题。第一,低生育率究竟是什么造成的?第二,它到底是好还是坏?第三,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这也许不是单纯的一个人口问题。我们不妨先搞清一个概念,那就是现代性危机。
“现代性”在学术界没有明确定义,大家泛泛的共识是追求理性、崇尚科学,以及建立一套自由民主的制度。
现代性与现代化密不可分,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结果。
当人类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时,就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蒸汽机被发明,电灯电话通向千家万户,汽车奔驰在纵横交错的公路,互联网打开了信息时代,这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图景。
1
现代性就是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作为商品经济化妆师的广告,最能体现这一点。
比如,你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广告,画面上是一瓶高档矿泉水、一支有质感口红、或是一个洁白的马桶,旁边往往会有性感的女模,搔首弄姿,笑语盈盈,文案则写着“生活态度”“人生梦想”之类的话。

如果不做任何联想,它们就是平平无奇的普通商品而已。但人偏偏会联想,你会想到自己也拥有这样一位娇妻,住在大城市的百平住宅里,衣着光鲜,彬彬有礼,和大人物谈笑风生,往来绝对没有白丁。
卢梭在浪漫主义小说《新爱洛伊丝》中写道,年轻的主人公迈出探索人生的一步,从农村走到城市,在给情人的信件中,表达了一种困惑和恐惧:
“我开始感受到这种焦虑和骚乱的生活让人陷入的昏乱状态。由于眼前走马灯似的出现了如此大量的事物,我感到眩晕。在我感受到的所有事物中,没有一样能抓住我的心,但它们却扰乱了我的情感,是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应当归属的对象。
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次终于会爱上谁……我仅仅看到了自己眼前的幻象,但只要我试图抓住他们,他们马上就消失了。”
这种感受放在今天的中国依然不过时。回想一下,当你刚刚踏入都市丛林,看着街上的车水马龙,闻到商场里刺鼻的香水,目睹五颜六色的大屏广告,阵阵轰鸣穿透耳朵,你是不是感到自己像走进了万花筒,从而感到“眩晕”。
用“眩晕”来形容现代性极为妥当,这是一种身体超然、呼吸急促、意识模糊的状态,让你想入非非,让你马不停蹄,越快越刺激,根本停不下来。
现代性塑造的资本主义景观,通过视觉、嗅觉、听觉等渗透进你的感官,从而来指导和规范你的生活。
马克思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生产的不断革命,社会关系不停动荡,永远的不确定,消费变成符号,算法控制人心,广告制造幻觉,这是后工业化时代区别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征。
对于刚从农业社会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来说,我们是很乐意拥抱这样的生活的,于是一味追求“发展才是硬道理”,搞钱搞经济被提上日程 ,大规模建工厂,建流水线,招海量工人,和全世界贸易,日子也是蒸蒸日上。

但时间久了,出问题了,咔地一下,手指断了,啪地一下,跳楼了,“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而火遍白领阶层的打工人梗,也让大家心有戚戚焉,今天办公室猝死了,明天担架抬走了,觉得活着没意思。
工厂和官僚化的办公场所不仅是生产、再生产的中心,更是将我们转化成物品的意识形态机器。这种生活是一种被动的体验,因为人需要成为的是一个机械系统中的零件。

这是现代性的必然,因为它包含三种制度层面的东西:资本主义、工业化及伴生的意识形态。
从生活的载体上说,现代性更容易在城市中体现出来。因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为了效率,必然要求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越来越高度集中化。
这就导致城市的人口密度越来越高,而东亚的人口密度在全世界又是靠前的,表现出来的就是节奏异常快。
2
城市的节奏很难具体来形容,一定要说的话,可能是人们起床后上班前的紧张动作,是通勤时的步伐速度,是奋力追赶公交车的气喘吁吁,是等待红灯时内心的焦躁程度。
香港,作为世界人口密度第三大的城市,在超级地租的疯狂压榨下,底层人生活令人窒息,一家人挤在十多平方的房间里,吃饭在这里,如厕在这里,睡觉在这里,压抑程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它又是密密麻麻的霓虹灯、起起伏伏的股票K线构成的电子荒原,对人敲骨吸髓后,然后又输入精神养料,完成一种循环。
可以说,这是资本权贵与金融食利阶层联手打造出来的畸形怪胎,也是工业文明与剥削机器制造出来的致幻乐园。
对岸的深圳也正在一步步向香港靠近,曾有人问,北京是帝都,上海是魔都,那深圳应该叫什么?

最风趣的回答,当属“戾都”。“戾”由户和犬组成,源自深圳两大著名现象:房和狗。
房,自然说的是房价高,年轻人接盘不易。狗,则代表禁止吃狗肉,以示与国际接轨。此外狗还代表畜牲,即社畜。
吃狗肉人士与不文明养狗人士的对抗,以及城市新地主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产生出了严重的戾气。过于稠密的人口在城市聚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摩擦和烈度更高的阶层冲突。

仅仅因为噪音这件小事就可以产生无数的纷争。媒体报道,在上海,两家楼上楼下的邻居,因为水管老化渗水影响到了楼下,由于没有好好沟通,遂反目成仇。
楼下购买震楼器进行反击,一震就是五年,搅得整栋楼都不得安宁。
精神病学专家马兹达·阿德里在《城市与压力》中认为,在城市当中长大的孩子,成年之后,患精神分裂、抑郁症的风险是农村孩子的2-3倍,越是大城市,患病的概率也就越大。

仔细回想,这些年来,我们生活中有哪些东西消失了?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开怀大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这片土地上消失,曾经遍布街头巷尾的嬉笑怒骂的场景再也不见了。
我们无法想象,五十年前日本还是那个开朗外向的民族,三十年前香港还是那个人人爽朗的地方,十多年前的内地还犹有欢声笑语的温存。
而多出来的尴尬又是什么呢?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路上迎面遇到像你一样的社畜,你从他畏畏缩缩的眼神中就可以判断出来。你们同时向左,又同时向右,最终差点撞到一起。
只要没有明确的规则指导,社畜寸步难行,瞬间就失去了对这个世界本能的反应能力。
人们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麻木、呆滞、尴尬,情感的表达越来越单一,语言功能慢慢丧失,开始抖音化、日语化、缩写化。
西方国家也碰到过这些问题,所以“逆城市化”浪潮逐渐兴起。20 世纪80年代,欧洲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西北欧,以及地中海中部地区的意大利,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比较高。
搬到城市的郊区去,在乡间小镇,在野岭山坡,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着新鲜空气和自然风光;有两三个孩子,养一双猫狗;时不时地露台上举行晚餐宴会;节假日就参加社区活动,与邻居们交谈、歌唱,举行有趣的比赛。
正是这样,曾经被称为低生育样板地区的北欧国家,在前些年反而逆势出现一波生育率显著攀升。

不过,这样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看似惬意,却要付出高昂的基建成本,而且即便如此,它本身也没有逃离现代性的桎梏。
二战以后,社会学家开始对现代性开始进行反思,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讲到,现代性有两个重要指征,一个社会生产造成了普遍的道德冷漠与道德盲视,没有人觉得自己有罪,却都是共谋,最典型的莫过于奥斯维辛的大屠杀。

另一个是理性,要进行大屠杀就需要对犹太人完成身份建构,这需要权力、管理和技术的高度融合。
哲学家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文明一定会导致极权主义,这不止是那种政治上的恐怖氛围,更是一种经济上的控制。
这个不难理解,当生产力把社会上所有人动员起来时,个人往往就显得微不足道。
3
作为政治象征的国家力量逐渐退场,散漫自由的社会力量也慢慢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无孔不入的经济组织力量。
更致命的是,作为复合型的高技术企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专家们整天吵吵着说中国要从人口红利变成人才红利,这不仅意味着竞争烈度变高,还带来了更可怕的问题。
不断涌现的新技术让人们的学习时间不断延长,而人的生育发育速度是赶不上资本萃取的速度的。二十多岁毕业,三十五岁报废,资源利用寿命仅为15年不到。

作为一颗小小的燃料,大家本来是有着成为灰烬的觉悟的,但若说多年的人口红利(人才红利)被一些人当成了理所当然,不加珍惜地竭泽而渔,用后即弃,那谁顶得住啊?不要说生育了,连生存都艰难。
工业化刚兴起的时候,珠三角每年切断十万根手指,到了后工业化时代,打工人被困死在996。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还能有所选择,后者在现代化网络的绞杀下,根本无处可逃。
农耕文明时代,农民被锁死在万古如长夜的土地剥削制度上,而工业文明时代,劳动力伴随着机器一起消磨成废渣。从一种循环到了另一种循环。

区别在于,在过去,农民的想象仅仅止步于小米粥和金锄头。到了如今,底层人也窥见了权贵与富豪们的生活一角,这当然会刺激他们冲破阶层桎梏,向往美好生活。
农业时代积攒下来的庞大人口,在资源不断集中、技术不断向前的工业化过程中,只能以过度的学业竞争、惨烈的就业竞争、自我绝育与自我消耗的方式,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
而嗜血的资本闻到了这股高烈度碰撞中的血腥味,不仅不会制止,还会推波助澜,不断筛掉那些不愿主动加班、不肯“拼搏进取”、身体素质较差的“劣质”燃料;而所谓的“优质”燃料,以为沾沾自喜获得了一点点劳动补偿,实际上已经和魔鬼签订了契约,将肉体和灵魂双双献祭。
所以,工业化固然是后发展国家想要成功的必经之路,但不是说单凭工业化就能高枕无忧。
相比于农业时代,工业文明提供了更充足的“安全感”,起码可以让绝大多数人免于死亡的威胁。但安全感的提供,往往也成了驯服最重要的要件,因为你必须被纳入某个体系内。
法国哲学家福柯敏锐地提出,一旦你进入这些体系,就必须被观察,监视,衡量,评估,打分,分类,矫正,训练,惩罚,优化。

想想现在很多公司不仅有周报、日报,甚至还有小时报,有晨会、午会还有晚会,通过把时间进行不断细化地切割,对员工完成不间断地监视。
这是技术和制度造成的,在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网络监控下,一不小心拍了张照片就被公司开除,在QQ上闲聊几句数据立马被抓包,HR小姐姐当场警告。
某种程度上,这样打工人甚至还不如过去的佃农,至少他们可以扯两句嗓子、抽抽烟解解乏。
这或许就是我们过早接近K值的代价,它来自于数学家韦吕勒提出的逻辑斯谛方程:dN/dt=rN(K-N)/K。

其中,N代表某种生物现有数量,t代表时间,r代表没有环境限制下的自然增长率,K代表这种环境可承载的数量上限。这个公式代表的含义是随着人口数量接近人口上限,人口增长率会不断下降,直到趋近于0。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K值会不断上升。不过,到了一定阶段后,以最低限度的生存来看,地球的人口承载量虽然大大增加,但人们想过上更舒适的生活,K值反而会缓慢下降。
在封建社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瘟疫、战争、屠城来主动消灭人口。

这种方式不仅很残忍,而且往往不受控。比如东汉末年,全国陆续爆发十多次大瘟疫,几十年间,全国人口由5600万减少一大半,到晋武帝时只剩1600万。哪怕连贵族都难以避免,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子,也在大瘟疫中死去。
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也没好到那里去,华盛顿、丘吉尔和希特勒都是著名的种族屠杀分子,在国家机器和现代技术的加持下,杀人如割韭菜,遍地人头滚滚。
另一种方式更加合理,而且副作用小。我们要知道,当资源不足时,不仅是羊太多了,也可能是狼太多了,太贪婪了,狼群越来越大,羊无法持续为他们输血,生态循环难以为继,帝国慢慢崩塌。
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君主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亲自下场,以雷霆手段杀掉一批狼,于是,帝国又可以重新焕发生机,这就是所谓的王朝中兴。
当我们在讨论人口问题时,不只是在讨论问题本身,而是在关注着我们将要走向何方。
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怎样的?现代性危机让全球性资本主义的扩张已到尽头,无产阶级可以预知的未来已经被资产阶级买断,羊群嗷嗷待哺,狼群虎视眈眈。
对中国来说,出路无非两种。
第一种是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在暴风雨来临前,将科技树全部点亮,用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和西方争霸,这就是所谓的“入关”。
第二种是创造出全新的制度,对内公平分配,在危机到来前守住防线,然后平稳地对外进行输出,和资本主义分庭抗礼。
未来如何走向,只能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乌鸦校尉整理编辑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乌鸦校尉(ID:CaptainWuya)
如需转载,请后台留言。
分享给朋友或朋友圈请随意
参考资料:
《城市与压力》,马兹达·阿德里
《新爱洛伊丝》,让·雅克·卢梭
《单向度的人》,赫伯特·马尔库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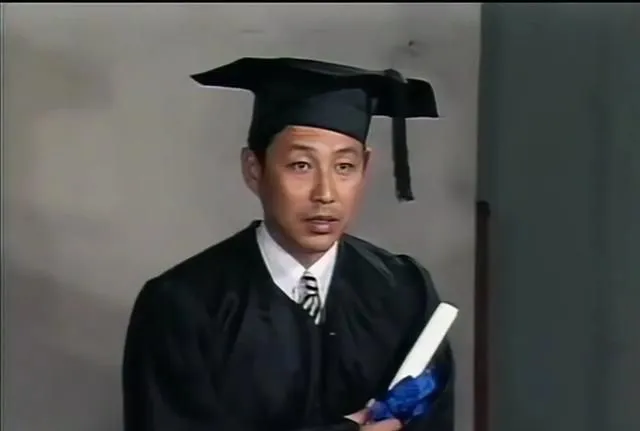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微信或手机浏览器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