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一首苏联歌曲《最美好的前途》,他的曲调非常优美,不过我今天并非冲着他的优美而来,而是昨天发表了《令宋词蒙羞的技术成因》,今天进一步阐述一些见解。先来个脑筋题:大家仅凭歌词,揣摸这首歌的主题?然后听曲调不看歌词,再揣摸一下。
因为技术上原因,我没法把视频下载到这儿来,好在网上一搜就有。不过小心!假如这首歌有画面背景,小游戏可能就失败了,可能被画面带偏了,再也回不到原来自己的经验主观了,我需要的正是这个。
有个声音来自最美好的远处,
它在黎明时分含着晨露。
绚丽灿烂的前景令人心驰神往,
我像儿时一样雀跃欢呼。
啊,最美好的前途!可不要对我冷酷,
可不要对我冷酷,不要冷酷!
我就从零点起步,向最美好的前途,
向最美好的前途,那怕是漫长的路。
有个声音来自最美好的远处,
它在召唤我去奇妙国土。
我听见那声音向我严正发问。
我为明天尽些什么义务?
啊,最美好的前途!可不要对我冷酷,
可不要对我冷酷,不要冷酷!
我就从零点起步,向最美好的前途,
向最美好的前途,那怕是漫长的路。
我发誓要变得格外善良纯朴,
誓和朋友分挑患难幸福。
我要飞快飞快朝那声音奔去,
踏上人们没有走过的路。
啊,最美好的前途!可不要对我冷酷,
可不要对我冷酷,不要冷酷!
我就从零点起步,向最美好的前途,
向最美好的前途,那怕是漫长的路。
啊,最美好的前途!可不要对我冷酷,
可不要对我冷酷,不要冷酷!
我就从零点起步,向最美好的前途,
向最美好的前途,那怕是漫长的路
我相信这个脑筋题:大家仅凭曲调去感受他的主题,虽然看法不一定相同,但大家的心灵体验高度相似――比如曲调是悲哀的、忧伤的、愉悦的、欢快的、愤怒的、滑稽的、谐谑的、神圣的…,但要大家再用文字将自己的心灵体验复述、描述出来,可能又有难度,呈现千姿百态,总感觉没法表达自己的心灵感受;如果仅凭歌词去感受,再用文字将自己的心灵体验复述、描述出来,那么他的千姿百态性肯定要远远大于仅凭曲调去感受。
我想这个结论大家一定会接受的,因为这有真实的生活体验。这个体验虽然很平常,但我今天要把他提升到一个重要理论:仅凭文字文本体验道德与仅凭音律体验道德,两相比较前者的道德水平一定要更低下――人的许多感情和道德体验是无法用文字文本去呈现的。当然这个世界不存在这样的古怪民族,他只有文字而没有音律系统,或者只有音律系统却没有文字系统;当今世界任何民族,既有文字系统亦有音律系统,我只是一种假设。但就人类文明一般规律而言,文字系统确实只是最近几千年才出现,而音律系统则出现的更早,音律系统一定与语言系统同时出现,而喜怒哀乐表达比语言出现得更早。
我这个假设当然是有原因的。昨天发表了《令宋词蒙羞的技术成因》,秦汉以后中国的文字系统进一步成熟,但是怪了!音律系统却莫名其妙丢失了,孔丘为之终生奋斗的“克己复礼”、“礼•乐”文明再也没有找回来,先秦时期的“六艺”到了后代变成“五经”,其中的《乐经》竟然丢失了,后世儒家只懂得用文字在“礼”字上捣鼓捣鼓。我以为秦汉以后华人(主要指黄河长江流域的汉族主体)对声音乐律的感受能力退化,也就表征了道德能力的下降,这是“种族逆淘汰”的重要证据。
我年轻时经历了“批林批孔”运动及其落幕,其后很久一段时间我总思索一个古怪问题:我们所批判的孔丘,他的话语中有个东西反复出现,就是“乐”,诸如“礼•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之类,可这个“乐”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在使劲批他时是否弄懂了?
忽然有一天我似乎感悟到什么:我们与孔丘可能已经分属两个“物种”,也许我们体内仍流淌着他的血液,但就文化意义上是无法“通约”的。我们是仅能文字思考的“物种”,甚至在批判孔子也只用文字,而孔丘以及那个时代的人,除了文字思考,还包括音律系统或其他复杂的系统――那时虽然还很原始,但与那个时代的文明进化是适应的。我们经常能在他那个时代的道家著作中知道有一类“神”人的存在,这类“神”人能从城门旁少妇的哭泣声中辨别她家到底发生什么灾难,需要什么帮助,想开口又难启齿之类心情。这类“神”人不用你说话,从声音乐律来辨别;这类“神”人甚至能从敌人的声音乐律来辨别他们的心理状况,判断最佳进攻时间,在将军的座上宾中,他们总是坐在最左边。
是的,至少孔丘那个时代音律系统还承载着道德规范和传播的作用,随着“种族逆淘汰”的演化,后代未能发展音律系统而是丢失了,仅靠文字文本系统去思考,无论批判和是继承。你想像一下,用无数个形容词去摹状那个“烫”,不如把他的手去火炉旁“烫”一下。西方人发明拼音文字后,音律系统的道德教化功能并未丢失,而是被保留到了宗教系统中,并且得到发展。
我们批判孔老二时也许真的疏忽了,德州扒鸡与章丘土鸡大眼瞪小眼是可能的,可怎么对话呢?当下中国有个特别有趣现象:对“文人”特别不顺眼,想尽各种办法嘲弄。我的理解中所谓“文人”就是仅能用“文字”思考的人,他们有发达的文字表达能力,但与社会分属不同“物种”。写完《令宋词蒙羞的技术成因》后我又想起了这个问题,想交待一下:隋唐特别两宋后,文字系统的功用盖过所有一切,“淫词艳曲”、“娱乐致死”、“垃圾文学”、“词人无用”、“宋词嫖妓”(参见辽宁王忠新的《蒙在宋词上洗不掉的耻辱》)从道德层面反映这件事,我则从智慧角度看这件事,他反映了隋唐特别两宋后中国精英人群只能用“文字”去思考,包括道德教化之类。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还多得多,包括他们的文学、诗歌、音乐、美学、建筑等等,其中相当部分是潜移默化的。苏联许多文化对我们这代人其实是双关的,比如他可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也可能是“超越的泛人道主义文学”。
比如就这首歌我第一次聆听时,他的背景画面诸如“镰刀斧头”、“列宁塑像”、“久加诺夫给孩子们演讲”、“佩戴红领巾队员们的整齐列队”等等。这首歌的主题似乎有关“共产主义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的荡气回肠、神圣感油然而生;再次聆听,背景画面变成 “采掘场”、“回旋的铁轨”、“潜望镜”、“拜科努尔发射场”、“高耸的发射塔”、“成排的控制按钮”、“加加林迷人的微笑和招手”。这个主题是苏联社会主义航天事业,似乎也很切题。我去网络搜了一下,词作者:由尤•恩津,曲作者:叶•克瑞拉托夫,译配:大名鼎鼎的薛范,前苏联科幻探索电视剧《来自未来的客人》主题曲,1985年播出。
我闭起眼睛聆听曲调,努力想象他的主题该是什么?共产主义神圣事业?强大的社会主义航天事业?科幻探索?似乎都很贴切。事实上我添油加醋,想象他的背景是“燃烧的原野”、“烧焦的坦克残骸”、“远处掩面而泣的背影”、“远处教堂的洋葱尖顶”、“教堂钟声的叮叮当当”,似乎也很贴切。事实上我们熟悉的前苏联“二战”影片,他的末尾处经常有这类背景和音律,并不因为苏联的无神论底色而屏蔽掉“教堂”、“洋葱尖顶”之类有神论标志。
事实上前苏联文化对华人的影响是双关的,修辞上的隐喻无所不在。既可当作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来品读,也可当作泛人道主义文学作品;既可象征共产主义神圣事业,也可象征东正教神圣事业;“十月革命”长诗《十二个》描写十二个革命勇士寻找真理的故事,他又仿佛十二使徒寻找耶稣基督的事迹。
是的!我以为我们华人自秦汉之际文明发展全面停滞,甚至有退化,许多文化现象丢失包括音律系统、数学系统、逻辑系统、形而上认知。孔丘时代“礼乐”还是同时出现的,秦汉之际只有“礼”不见“乐”;秦汉之际“诗歌”还是同时出现的,有诗必有歌,有歌必有诗,而到了唐宋之际,诗词成了官僚和老男人们玩弄文字的器物,两宋“淫词艳曲”、“娱乐致死”、“垃圾文学”、“词人无用”、“宋词嫖妓”(参见辽宁王忠新的《蒙在宋词上洗不掉的耻辱》)一种普遍现象,音律系统完全丢失。
音律系统的丢失不仅种族智力退化,也标志着道德认知水平的倒退;苏联“十月革命”对华人的输出是全方位的,也是双关的,可是华人音律系统的丢失,对“十月革命”的认知难免是偏颇和缺角的,很可能是个很大的“角”。
夏虫不可语冰,你怎么给他解释那个“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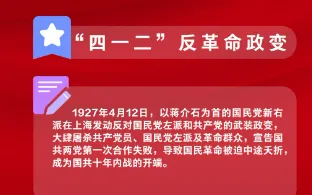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评论功能已恢复开放,请理性发表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