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巫吉
在这个时代,市场用物的尺度俯视众生,人不过是维持市场再生产的手段。但人的再生产总归不能如物的生产一般可迅即控制和支配,于是,人口就一直是一个甩不掉的问题。过去嫌人多,现在嫌人少,都是一个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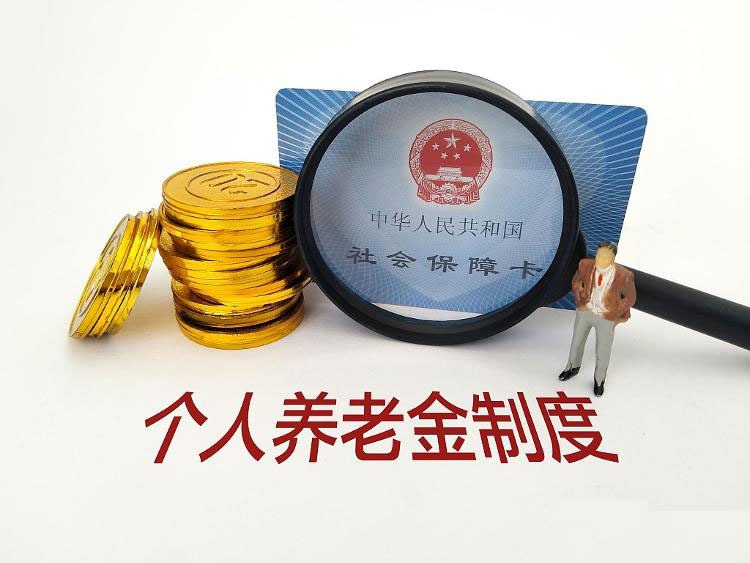
又是一年春天。万物滋长,生机盎然,鸟翔鱼游自在畅快,虫鸣蛙声不绝于耳。高尚的人们沐浴春光春景之间,睹物思人而反求诸己,又惦记起了人口问题。去年春末好容易推行了放开三孩限制的政策,却没见着什么效果,各种歪招也陆陆续续地被提了出来,各自热闹了一阵。今年则新推出了一个叫做“个人养老金”的政策,说是能够为“养老”锦上添花,然而还是引起了老百姓的警觉。无论政策初衷如何,出台相关的人口政策总是显得有那么点儿吃力不讨好。
三胎政策也好,“个人养老”也好,它们只是人口“问题”的导火索,只是大家发泄平时积压在生活中的种种不满的宣泄口。这些不满来自这个时代社会再生产的矛盾运动和它带来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的种种艰难。唯有理解现实,才能从这些表面的情绪进入问题本身,才有解决矛盾的可能。
孩子的生养问题和所谓养老问题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人口老龄化常常被作为鼓励提高生育率的理由,而这些年来的低生育率也使得老龄化问题好像变得特别突出。许多地方出现了所谓的养老金缺口,还有些人不停地鼓吹延迟退休年龄,养老问题也这样就刺目地悬在人们生命历程的前方。这些所谓的人口问题总是被作为一系列问题提出来,然而,它们总归是一个问题,即社会再生产如何进行的问题。
一
一个社会总是要再生产出它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出它的生产关系,否则这个社会就不能持续地存在下去。譬如说,在农业封建社会,农民要种粮食,每年都要留足种子,要喂养好耕牛,要修理和新造农具,否则,来年的收成便没有了保障,人也就活不成了。这是生产力的再生产。当然,要成为一个封建社会,它还要不断地生产出农民和他的剥削者地主阶级,还要使这样的统治关系和剥削关系持续地被生产出来。它要使地契、田租、衙门和差役继续存在,使这种“天道”持续下去。总之,要使得生产资料、劳动者和生产关系持续地存在下去,这个过程就被称作社会的再生产。
在任何社会,生产要继续进行下去,便要不断地再生产出劳动者、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并再生产出生产关系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以雇佣关系为基础,没有了劳动力和产业后备军,这种生产关系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没有了基础。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尤为重要。这样,资本便要为了劳动者种群的存续而向劳动者支付工资。这个工资看上去是发给劳动者个人的,但事实上,却要发放给整个再生产中的无产阶级队伍,包括那些处在脱离了劳动关系或处在没有劳动能力阶段中的无产阶级。前者能够维持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使工资在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处徘徊,后者则关系到劳动力再生产本身。
人的劳动能力如同一道波浪,幼时未有,随年齿而增,至青壮年达到峰值,再长则再衰,年老又归于无。它的两端是童年期和老年期。在人年幼、年老和疾病这些在个体看来显得无助的阶段,如果没有来自他者的扶助,便没有幼儿、老人和病残人的生存可能,他们便无法完全地经历生命旅程。
儿童的抚养问题涉及到劳动力的再生产,无疑是包含在再生产费用中的。没有儿童,便没有未来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要作为一个阶级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使社会再生产得以持续进行,就必须使社会上的儿童得到照顾。在家庭制度下,如果儿童由父母抚养,资本家就不得不按照包含了儿童抚养费用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向儿童的父母支付工资。
养老问题则离得稍微远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或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养老是由部落、家庭作为生产单位承担的。除开那些极端困苦的原始部族外,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并不因为他们丧失劳动力而被家庭放弃,这是因为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已经能够满足老人的赡养了。否则,“孝”就成了不可能实现的笑话,就成了阻碍社会再生产的迂见,而那些提倡孝道的社会就会在社会再生产的竞争当中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既然孝道能够在古代社会大行其道,可见养老在古代社会大概不是什么问题。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大可不顾老人死活,但工人不会答应,社会也不会答应。所以,对于养老问题,资本总是要被迫予以解决的,并能从解决中发现新的赚钱门道儿。
在各种家庭制度中,老人无非自己养活自己,或者依靠家庭养老。如果是家庭养老,那么,每个工人阶级都要从工资中支出一笔费用,用于自己双亲的养老。此外还需准备一笔资金,用于家庭可能的医疗支出。而他双亲的寿数几何,他却无法预期。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也就是他的工资当中便要包含这笔为他的双亲进行养老的费用,以及为了双亲未来疾病等情况预备的救急资金。
如果拆散这种家庭而采取核心家庭的制度,老人便与子女分居开,资本家看上去便把老人的负担从他的工资当中扣除了,实际上却并不如此。因为工人就要为他自己养老做准备了。如果是他自己养老,那么,每个工人阶级都要从工资中作一笔扣除用于储蓄,以用于自己未来的养老。而他自己的寿数几何,他却无法预期。这样,他就倾向于多储蓄一些,而资本家为了维持无产阶级的再生产,也就要在工资中包含这样一笔被储蓄的费用。
总而言之,无论他自己负责自己未来的养老,还是他赡养老人,他总要从工资中做出这笔养老金的扣除,还要多预留一笔应对意外开支的储蓄,两种制度的效果是一样的。
由于人是无法确定他的寿命的,所以这种扣除和储蓄在大概率上总会高于他的预期生命,从而使得社会上的“消费”不足。毕竟,谁都不愿意“人还没死,钱花完了”。而工人又总是要按照他的日常消费和储蓄的总额,向资本家索取工资,从而他们由于需要储蓄向资本家所要求的工资就显得比这种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费用来得高。尽管这些储蓄有可能变成“投资”转入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中,充作资本的材料,但这并不是必然的,而它加重资本家的负担却是显而易见的。资本家便要绞尽脑汁地减少这笔开支,甚或开发些新技术,以便能够从中牟利。养老的社会化就是这个减支增收技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二
今天的人们大多有个误解,以为自己在今天缴付的养老保险金就是未来社会向自己支付的养老金。如果是这样的话,哪里有养老金的所谓“缺口”呢?应当缴付养老金的那些老人在过去不都足额缴付了那些养老金吗?他们如果在过去按照比例交够了钱,为什么还会有空缺呢?在所谓养老金的制度当中,看过去好像是劳动者为了他自己未来的支出而预先支付一笔费用,然而事实上却不是如此。任何指向未来的费用只是构建了一个面向未来的社会关系,而不可能确切地对应什么实在现存的东西。任何货币总是对应着相应的商品,考虑养老金问题也应该将金额问题还原到实物消费品和服务中去,还原到社会总产品当中去。任何消费品和服务都是当期的:商品有保质期,存久了就要坏掉,而服务更是只能在当下提供。所以,一切流通中的货币只在用于消费当期的服务和商品时才实实在在地与消费品生产相联系,而社会的总消费品则是大致按照当期用于消费的货币进行分配的:工人总是用缴付养老金之后的实发工资余额来购买它当期消费品,而同期的老人则用他们领取的养老金购买他们当期所需的消费品。所以当期养老金的扣除只是使工人减少了当期的消费,并不意味着在将来按照这个数额用领到养老金购买相应份额的商品。除去资本家的消费外,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就要按照当期工人扣除后的工资余额总额和当期养老金发放总额的比例,分配给了当期的工人和老人。比如说,当期有1亿工人,有两千万老人。工人每个月工资1万元,上交养老金两千元。那么,养老资金每个月就会有两千亿的进账。这笔现金是被储蓄起来的,可以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这笔资金也就因此不再能够由工人用于购买当期的消费品和服务。如果当期的每个老人领取养老金5000元,全社会就会有1000亿的养老金发放,这笔养老金将用于购买当期的消费品和服务。那么,在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当中,当期的工人就消费了8000亿的份额,而当期的老人就消费了1000亿的份额,他们之间的消费品总价格之比是1:8。如果社会总消费品是一块蛋糕的话,当期老人拿走了一份,工人拿走了八份。这个时候,每个月的养老金当中就会有1000亿的盈余,但这笔盈余并不用于购买消费品和服务。此时,如果社会再生产的各部门按照工资总额将消费品和服务投入市场,便要出现消费品和服务的过剩。
可以看看另一种情形。如果这时候社会上的工人是一个亿,而老人的数量增加到4000万,在其他情况不变时,这时候老人领取的养老金数额是2000亿,和工人当期缴付的养老金数额相等。养老金刚好达到了盈亏平衡点,养老金和工人领取的工资数额就成了1:4的关系,当期的工人和老人就要按照4:1的总价格比例分配社会总的消费品。此时,如果社会再生产的各部门按照原有工资总额将消费品和服务投入市场,消费品和服务刚好平衡。
如果老人的数量增加到6000万,在其他情况不变时,这时候老人领取的养老金数额是3000亿,养老金便出现了所谓的1000亿透支,养老金和工人领取的工资数额就成了3:8的关系,当期的工人和老人就要按照8:3的总价格比例分配社会总的消费品。此时,如果社会再生产的各部门按照原有工资总额将消费品和服务投入市场,消费品和服务便要出现一定的供应紧张。
所以,当期养老金领取数额与工人扣缴的养老金数额应大致相等,才不至于对社会消费品和服务的供应造成影响。
当然,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例子。在不同的情形中,工人和老人总是按照当期的实发工资总额与养老金总额的比例分配社会消费品和服务的。因此,养老金是现收现付制的。所谓养老金的缺口,只是当期老人要消费的当期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所对应的养老金账目余额不足。今天老人在过去交付的养老金,只是按照过去赡养所需的产品份额对过去的收入所作的切割和分配。譬如,假设在2000年,劳动者平均要交纳工资的10%充作养老金,那么这至多只是意味着2000年的时候,用于消费的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中有10%要用于赡养老人,并不意味着这批劳动者在退休时能够领取任何份额的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他们在退休时能够占有的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的份额,将由他们退休时的总养老金发放数额和工人实收工资总额的比例决定。
以为自己现在缴费比例高,将来拿得也多?那属实是想多了。当期缴费比例高,只是因为当期老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比例高。你年老时拿到的是未来劳动者在工资中扣除的那份比例,那时候拿多拿少,只取决于那时候的养老政策。要不然,过去的劳动者都给自己缴足了养老保险,为啥现在还会有“养老金缺口”呢?

所以,从社会总产品上看,养老金都是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看上去是现在的自己保未来的自己,其实是当期的劳动者保当期的老人,只是推销时借助了市场条件下群众的自利心态罢了。
老人多了,原先定的比例不够了,就要使用各种手段解决问题。如果工资当中用于社会保障的那部分金额比例高一些,就能够养活更多的老人,使退休年龄相应地提前。然而这就要求提高工资,资本是不会答应的。他们总是要求降低这个比例、延长退休年龄,使他们购买的劳动力越来越便宜,同时使得大量还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作为产业后备军,进一步压低劳动者的工资。
所谓的延迟退休年龄并不是当期的工人被延迟了退休年龄,而是当期面临退休的那些接近退休年龄的工人不能够按时退休。延迟退休减少的是那些适龄工人领取退休金的份额。等到现在的工人年老之后,他们的退休年龄也将由他们那个时代的劳动者和被抚养人群分割社会总产品的比例来决定。

在“延迟退休年龄”问题上,这个退休年龄不是指失去工作能力或不再获得工作机会的年龄,而是能够从社会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延迟退休年龄,就减少了用于支付这批本该退休的老人用于养老的那笔费用,降低了社会总产品中由老人“免费”领取的份额。而这笔费用原先是应当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计算在工资总额当中的,并不“免费”。同样地,现在延迟退休年龄,针对的也只是当期即将退休的人群,减少这部分开支占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至于那些尚年轻的劳动者,他们的退休年龄将由未来社会的生产条件决定。
三
会有人问,我交养老保险时,国家或者保险公司不是承诺未来给付一定数额的保险金了么?然而,这个承诺并不与养老金的绝对数额挂钩,因为它要随着生活水平和物价水平的提高而适当提高。所以,与其说保险金是一定数额的金额,不如说是某种向未来的社会要求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
为什么会有这些社会保障或者保险呢?它们看上去是争取福利的结果,事实上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为资本服务的。社会化大生产也使养老社会化了。养老社会化的效果在于通过统计学的大数定律确定人的平均寿命,这样就可以在社会层面上统筹养老支出,精确地“以支定收”,减少工人原先用于未来支出的储蓄,从而将工资压缩到最低限度。个别人的长寿或夭寿,并不能够影响社会在这方面的总支出。如果60岁退休,有的人活到100岁,有的人活到60岁,但社会保险或者社会保障就使得社会能够按照人的平均年龄来估算劳动人群和抚养人群分配社会总消费品的份额,从而使得用于消费的货币“物尽其用”,减少前文所说的超额储蓄带来的“浪费”,刺激消费,从而一面为资本家节约工资的发放数额,一面减少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发生的机会。如果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70岁,原先的工人总是按照较高的寿命预期进行储蓄,实际只活60岁的工人也要按照100岁的预期进行储蓄,从而要求按照包含40年退休时光的消费总额发放其劳动期间的工资总额。现在则不一样了,资本家只需要按照平均预期寿命支付包含10年退休时光消费总额的养老金和工资,并将养老金在社会层面上进行统筹,使现有的老人拿到足额的消费品,就能使现有的社会保持稳定,从而“节约”了工资支出。这样的统筹,也只有在金融资本足够发达的社会条件下才可以进行。养老金的统筹收支本身又增加了金融资本支配的货币份额,加强了金融资本的力量。当然,这笔钱也因此还可以离开消费领域,用于各种投资,继续充实“市场”的力量。
四
资本和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处在对立的两极。在社会总产品当中,资本的份额增加了,劳动者的份额也就相应减少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总是通过各种宣传让劳动者减少消费,挤出份额来增加他们的投资,充实他们的力量,好加大马力生产,挤垮竞争对手。劳动者参加的投资活动,只要不支配生产过程,自然丝毫不能改变资本支配生产的事实,也丝毫不能增强自身的力量,反而减少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进而限制了工资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加强了作为对方的资本的力量。你吃得少了,省吃俭用交给别人投资,壮大他们的力量,最终拿自己的生活质量给他们做了件好嫁衣。
资本多吃几口,对资本自身也并非全是好事。消费减少了,投资增加了,虚假繁荣、波动和危机也就来了。资本吃多了几口,最后的结果不外乎是社会消费总需求的减少、危机的爆发和小资本的破灭。当然,危机之后,资本的力量也会更加集中。

劳动者节衣缩食让资本吃了个饱,这样的好事,资本自然要绞尽脑汁设计一番,开发出不同的产品,天花乱坠地包装一下。此次“个人养老金”事实上也是这样的设计。个人养老保险支出再多,也不能确定与未来社会产品份额之间的联系,反而缩减了劳动者自己的消费,充实了资本的力量。
所以,劳动者在市场条件下的再生产,不过是资本再生产的手段。他们当牛做马若干年,培养子女继续当牛做马,交了一辈子养老金,老来想着颐养天年,却还要服从资本的差遣来填补各种“缺口”,充实资本的力量。其实,说到底,劳动者的一生在资本手里都只是算计和买卖的对象。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评论功能已恢复开放,请理性发表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