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社会热点的许多声音,包括对情绪的宣泄、对错误的挞伐抑或对事态的分析,“官僚主义”作为一个“涉事方”总是反复地被提起。但与各个场域下对官僚主义的提及、批判和分析进行比对,笔者发现在不同的场景、语境和作者所提及的“官僚”和“官僚主义”实则是不尽相同的。同时,在所有这些提及“官僚”和“官僚主义”的内容中,似乎对“官僚”带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负面看法”。就此,笔者今天来谈谈官僚和官僚主义。
作为理性制度的官僚制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在抽象世界上的发展, 对于许多动物世界来说,可谓是登峰造极。如果说,人类摆脱自然的束缚、发明了火和耕种,为人类创造出持续的剩余产品,是社会形态的第一次演进,那么工业化以来人类摆脱农业生产的束缚完成工业化,则是社会的第二次演进。而至于信息化算不算第三次,倒还难说的很。
但不论社会形态算演进了几次,现今空前复杂的社会形态都已经高度分化,这样的高度分化与社会组成的功能化是充分相关的。而最早产生了大量社会剩余产品的中国,则自然最早出现固定化的社会功能分工,即键政人通常所说的文官制度,研究中一般称为理性官僚制(bureaucracy),这一制度构成了一个社会分工组成,同样也是一个组织。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曾这样说: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现代官僚机构的特征包括:因功能而分的官职需有明确专长、在界定清晰的等级制度中设立各级官职、官员不得有独立的政治基础、官员必须遵守等级制度中的严格纪律、薪俸官职只是谋生的职业。马克斯·韦伯定为本质上的现代特征,秦朝如果没有全部,至少也有很多。”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秦汉以来的官制(没有吏)以及到科举制大大完善以后,无疑是一种早熟的政治制度。
所以说,虽然科层化和官僚制是现代制度的基石,但它并不是突然在近现代出现,而是有其现实土壤源流,在西方中最早在行政系统中采用文官制度的英国,也是参考了中国的科举制度。

理性官僚制是“委托-代理”机制的一种体现。即权利人无法直接控制和掌管具体的事物,介入具体的每个流程,而具体流程中由无法“自发运行”,必须进行独立判断,那么这时就需要将权利人的权益执行进行委托,受托方则是代理方。实际上,规模较大的企业,其内部控制和管理运行也同样的具有官僚制的特征。因而理性官僚制已经是现代社会一种广泛应用的社会构造。它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是法定化,即理性官僚制的组织是依照明文或默示的规则体系运行,从成立之处就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一经确立,理性官僚制的成员必须在相应规则的范围内工作,不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而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程序是客观化的,责权利是分明的;
其二是科层化,科层一词对应的英语就是bureaucracy,也即上文所述的官僚制,在此处则指的是客观的等级化。这里的等级,在其诞生之初就借鉴了贵族和封建制的客观存在结构,形成了等级制,并依照等级制划分责权利,而在随后,这样的等级制也对贵族统治、封邦建国形成了等效取代;
其三是职业化,从古典中国到现代社会,理性官僚制的特征就是脱离其他工作,专职从事行政运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现代职能)等社会功能的运行职能。现代的理性官僚制更进一步要求官僚必须熟悉本部门业务技能,提高自身在其岗位上的技能水平,适应岗位变化、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现代社会职业精神的出现,也要求官僚要有忠于职守的觉悟;
其四,则是理性化。理性官僚制要求官僚在工作中不受个人好恶影响,而是以理性的方式行事,执行政治机关的决策,以理性人的身份严格依照规章制度行事,否则将受到相应规则的制度的约束。
从社会发展脉络来分析,当代的理性官僚制受到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与古典封建时期的官僚制存在以下的不同:
其一是分工深化,随着组织化的发展,作为工作人员们的职务活动,这些工作越来越固定于一定的专业范围之内,譬如主管高等教育事务的官僚、和主管社会治安的官僚,大概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其二是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这使得大量的剩余可以用以支付专业管理的费用,同时收入和支出得以用统一的标准量化。那么,在平等交换的前提下,一方面定期支付薪金相对于实物薪金制,可以更加有效的制约被雇佣的官僚,保证官僚的稳定收入来源,就能增加雇员对组织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它改变了世袭官僚制中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保证了官僚的自由人格和自尊,更易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
其三是理性精神的确立。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社会中确立了一种新的精神,即经济理性,因此理性官僚制的发展就需要一种能推动和支持理性经济行为的内在精神和伦理,而在西方国家,新教改革引起的信仰变化提供了理性官僚制所期望的精神基础。新教伦理鼓励勤奋工作与严格律己,号召对时间和劳动的理性使用以使成就和利润最大化,当这些价值观念成为工业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意识时,理性官僚制的诞生就有了可能。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说,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实际上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为适应工业化系统发展而发扬光大。非西方体系的工业化国家中自然也有不同根源但作用相同的理性精神。

官僚制和官僚主义
上述作为一个框架性认知,对现代社会的基石即理性官僚制进行了阐述。韦伯认为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而从卢曼的社会分化理论来出发,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里,各个社会分系统的功能彼此之间是不可替代的。既然如此,更有必要充分剖析官僚制本身与日常所抨击的官僚主义的迥异。
一般来说,官僚制当然是有其优点的,但同样存在着官僚制的弊端。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僵化。理性官僚制作为委托-代理的形式,追求的是委托方要求的效率,自然而然相对压制代理方的积极性,同时,现代官僚制规模极其庞大,制度、规章体系纷繁复杂,进一步让具体办事人员处于一-种崇尚“工具理性”否定“价值理性”的情景,即按照既定流程办事,绝不多事,绝不生事。在今天的情况,就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其次是信息失真和滞后。由于官僚制是科层化的,其信息传递是层层上传下达的,一般不会越级传输,这样在信息传输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层级的利益不同,侧重点会发生偏离、乃至发生对关键信息的扭曲,这样就会使总体信息产生失真的情况,进而导致决策不能依据真实信息作出,基层执行操作时没有认真领会顶层意图的情况出现。典型如西路军的失败,就是因为西路军提供给了错误的敌我情报信息,进而延安作出了错误的决策,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败。
而官僚主义,则是理性官僚制负面因素的集中派生。我们所经常谈论的官僚主义,在通俗语境下往往只是把它看作一种追求权势地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很少有人从总体角度来看待它。实际上,官僚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技术性的官僚主义(或者说局部的官僚主义),再就是体制性的官僚主义(客体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统治) 。
在我国王亚南先生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他把官僚政治分作两个方面,即技术性的官僚政治和体制性的官僚政治。所谓技术性的官僚政治,主要是就政治作风、工作方法而言的。
“比如说,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地、刻板地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诸如此类,都是所谓官僚主义的作风。”“这种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不但可能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存在”,“在政府机关存在”而且“在一切大规模的组织,如教会、公司、乃至学校中存在”。

所谓体制性官僚主义,主要是就政治机构,政治制度乃至一切需要科层化、行政化的机构而言的。一直所说的“大企业病”、“高校去行政化”,实则指的就是这种官僚主义弊病。
而从社会的意义上来理解官僚政治,就是说在官僚主义政治下,“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这种体制性的官僚政治,并非任何历史时代,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的。王亚南认为,这两个方面的官僚政治,人们都应当研究,但首先和着重研究的,应当是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
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伦理的视角中,如果国家作为一个外部客体,将公民从生到死无所不包,国家拥有全部的社会职能,无论是社会管理还是社会公共服务,都包含在内,这样一种体制叫做全能型政体。这里的全能,并非指功能强大,而是指职能全面。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独断性权力、社会权力和强大政府异常警惕和反感,因此发展出了复杂的理论体系论证这一客体的不合理性。应该说,通过其对前现代和现代的诸多政府的观察,这一理论中也同样有许多可取之处。
研究当代官僚体制的名著,应该首先提到的,是戈登·塔洛克的名著《官僚体制的政治》。戈登·塔洛克作为一个宪法学家和经济学家,通过对宪法的经济规范分析确立了他的学术地位,公共选择理论、寻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外部性理论等都是塔洛克的学术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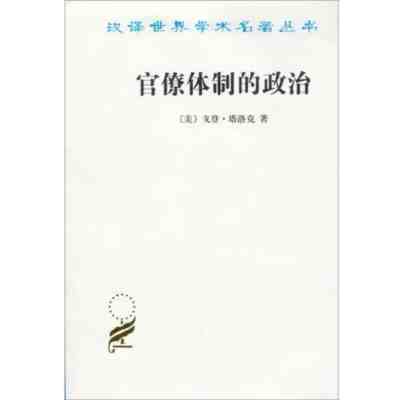
塔洛克假设了这样一个结构,即官僚组织由完全理性的“政治人”组成,具有政治理性(以晋升和攫取更多的政治地位与权力为目的),在内外约束条件下行动的逻辑机制。而无论如何推导,全能型社会必将导致的,是僵化、低效和无能。这是由信息传递机制、社会约束机制所决定的。
从数学上来说,一个组织的一般效用均衡函数,是组织中每个个体的局部效用均衡函数的加总,而官僚体制中每个个人的缺点,如信息不全面、个人私利(不论名或利)等是不可能通过加总而消除的。因此,除非全能型社会不使用官僚制(科层制),否则这些问题逻辑上是无法克服的。
而这,也因此就诞生了以革命意识形态灌输和动员的布尔什维主义,高度组织化的列宁式政党,赖以克服其庞大体制的惯性(官僚制惯性)的,就是革命化的意识形态,和动员式的不断洗刷体制惯性。毕竟,科层化的官僚体制已经是人类社会最现代化的组织方式了。
科层化,还是发包制
笔者在本号之前的许多文章,都曾提到要用更加“科层化”的模式来适应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现实。这或许会让一些读者产生疑惑,是不是在让官僚走上舞台,或者觉得这是官僚主义大乱斗。其实,这是将两种官僚主义、官僚制和发包制混为一谈。
关于行政发包制在我国产生的原因,对中国超大规模复杂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产生的问题,笔者在过往文章中多有论述,印象不深的读者请还请复习笔者之前的文章,如《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与结构》和《"一刀切"背后的深层逻辑》等,这里不再赘述。
上文提到,官僚主义有两种,局部的本位主义和整体性的统制主义。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如压情不报、纵容等情况,是基于发包制的现实而产生的。是发包制的存在,产生了这种超出一般的官僚主义的情况。因为一般来说,官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推卸责任、拈轻怕重,而至于直接的为恶,则超出了官僚主义本身的能力。
在美国,受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其城市治理产生了“经理人”模式。城市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一个7-11人组成的城市议会,拥有根本性实际权力,方向性的决策都需要城市议会作出,而市长和“城市经理”即行政机构负责人,则由议会任命。有些城市的市长拥有实际权力,即领导城市行政机构,但仍设有由市长提名议会任命“城市经理”,另一些城市的市长则是礼仪性的,“城市经理”直接对城市议会负责。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实际治理层面上美国也同样采取的是科层化。而日常键政人语境中所熟知的,美国(或者说西方)政治官与事务官两分,其具体演化情形就是这样高度分化的情况。

而把视角放回国内,一如笔者所言,发包制,实际上是理性官僚制在实际情况下的妥协和退让。这是一种名义与实际的妥协,是前现代化情况下,和超大规模国家信息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所共同塑造的。基于封建残余思想的官僚本位主义,诸如人身依附、人身控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是行政发包制带来的土壤所萌发,并非是官僚制本身的痼疾。因此,在实际分析时,不能将官僚主义的负面因素等同于封建因素,同样不能将前现代的官僚等同于现代化的理性官僚,因为两者的社会背景、文化土壤已经全然不同。
当然,这并不是说,理性官僚制没有缺点。正如上文所分析的,理性官僚制仍有其所需警惕的负面和缺点。也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如政府失灵,都是对全面官僚制的否定。因此,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际,提出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实属未雨绸缪。
而如何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三元并立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是对现今人类社会进步的贡献,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而有益的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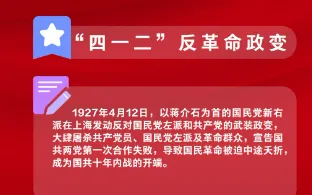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评论功能已恢复开放,请理性发表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