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袁久红在某微信群发“色情图片”的消息在网上引发热议。

群聊截图显示,该微信群共有332名成员,是多所高校马院院长的工作群。
经过了网友的讨论以及媒体的报道,东南大学回应称学校已经关注到此事;随后不久,袁久红的个人信息和简历在学校官网被下架,东南大学党委组织部发布通知免去袁久红职务。学校的一系列举动,说明网传消息属实。
近年来,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地被曝光出来:
2022年12月,已婚的北京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方岱宁,因为被曝光7月初参加在线学术会议时与一名年轻女子亲吻,被学校免职;

2022年10月,苏州大学教授鲍某某使用多媒体给学生上课,在给别人回复信息时忘记关掉投影,导致他与多名女子聊骚的内容被曝光;

2022年5月,网曝郑州轻工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在某工作群发表色情言论,随后谭某某及消防党政办主任声称谭某某被盗号,但很快被腾讯打脸,校方最终被迫对其停职调查。

在网络舆论的高度关切下,这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教授”一个个地被免除了行政职务,甚至丢了饭碗。
在网友纷纷指责袁久红的时候,笔者注意到网络上还存在着一种貌似“理性、客观”的说辞:“院长也是人,有欲望很正常,发个图就被革职,处罚太重了”,还有人指责“群众对知识分子的恶意越来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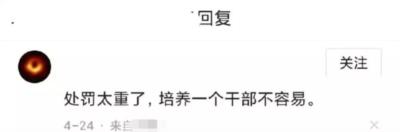
真的是中国群众对知识分子不够宽容、不够大度,恶意针对知识分子吗?我们不妨看看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美国会怎样:
2023年1月,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Mark Schlissel因与下属发生不正当关系,被校董事会免职;
2023年3月,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女校长在课堂上讲解米开朗基罗的代表作《大卫》后,被要求辞职,因为有家长投诉这是向学生传播“色情”作品;
2021年11月,肯塔基州的乔治敦学院校长Williams Jones因与学院女员工有不当行为被解雇;
2018年6月,波士顿大学下属的高中学院院长Ari Betof因喝酒后亲吻波士顿大学本科女学生被学校解雇;
2015年9月,斯坦福商学院院长Garth Saloner因婚外情自行决定辞职,尽管斯坦福商学院公开声明支持Saloner,但群众仍旧让他深陷舆论漩涡。
可见,即便在所谓“自由、开放”的美国,美国的人民群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行为也是“不宽容”的。
须知,在任何一个所谓的“等价交换”的私有制社会的主流观念中,权利和义务都应当是“对等”的。知识分子既然以标榜“社会良心”和“道德家”的身份,来承担“教化”社会的职能甚至是职业,就不要怪群众反过来以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知识分子。这与劣迹艺人被封杀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承担了“教化”社会的职能,他们的高收入与这样的职能是息息相关的。
人们对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的一个很典型的指责就是:“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以“道德家”的身份来替统治阶级要求底层百姓“存天理,灭人欲”,自己却“说一套做一套”,百姓能不骂你吗?百姓自然会由此现象意识到,让百姓“克制欲望”节省出来的资源,就是用来充分满足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
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同样需要标榜道德。亚当·斯密一手拿着《国富论》宣扬市场经济的“理性经济人”、鼓吹利己主义,一手还要拿着《道德情操论》鼓吹正义、仁慈、克己等美德。资产阶级一面污蔑共产党人“共产共妻”,一面“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然而,在马克思那里,他不仅强调了欲望具有“能动”与“受动”的二重性,更以两者的对立统一强调了“人的欲望”的特点。在人的欲望中,自然本能始终都与人的“本质力量”结合在一起。欲望问题同时就是欲望的对象化实现问题,欲望的对象既外在于人,同时又是他表现自身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对象。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个“实践”是以生产实践为决定因素的各种实践活动。
因此,马克思承认欲望存在的客观性,但更强调人的社会性;马克思批判的不是“一夫一妻”这样的婚姻与家庭形式本身,而是批判私有制父权社会的一夫一妻制,让妇女彻底沦为丈夫淫欲的对象和生育的工具。马克思对未来家庭的构想包括两个环节:一是消灭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家庭,二是重新建立以性爱为基础的、性别平等的新家庭。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有关主张,与资产阶级及其卫道士所空洞标榜的“道德”是截然不同的。
而更加让群众愤怒的是,这种空洞的道德标榜,不是用来“约束”、也从来不能“约束”资产者,只是用来“约束”无产者,成为统治工具的一部分。
对于资产者支配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的行为,无产者或是不敢反抗,或是在“贫穷可耻、致富光荣”的口号欺骗下认为是合理的;但是对于资产者豢养的、用于教化无产者的“知识分子”和“道德家”,群众却能直观地感受到他们的虚伪,也是敢于反对的。
这样的现象,完全扯不上“群众对知识分子不够宽容”,“群众对知识分子的恶意越来越大”——实在是在群众受苦的时候,某些知识分子的虚伪教化表现得太过恶心。
而更令人们担心的,一方面是“教授”们占据了道德高地,可以对受害者进行精神PUA,正如神父PUA修女、喇嘛PUA女施主;另一方面则是“教授”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暴力胁迫女学生,如成绩评定、论文审核、学位授予的权力,甚至是行政权力。
有些看到原图的网友,怀疑袁久红深夜发的不是网络上的图片,而是用微信拍照功能直接拍摄的图片;如果这种推测属实,那被拍摄的对象又是谁?当然,如果当事人不站出来,这样的推测只能停留在推测阶段。
也正是因为这样,网友才对教师及大学教授的类似行为表现得更加不“宽容”。
袁久红如果只是关起门来与自己的妻子“男欢女爱”,没有任何人会去指责他;而他却将图片发到工作群上,无论是故意还是无意的,这种行为即便按照资产阶级标榜的道德标准都是无法容忍的,重要的是,拍摄对象还很可能不是他自己的妻子。
袁久红还有一个身份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搞出这样的“下流”行为,则是典型的“红皮黄心”了,更加不应该被“宽容”、被原谅。马克思主义在普通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就是被这样的败类一步一步破坏的。
马克思主义本来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圣经”,无产者的战斗哲学,而今却沦为袁久红之流获取学术地位和权力的敲门砖。
笔者作为一个无名的草根网民,想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一些社会现象时,在B站就会收到这样的退稿通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暂停个人上传时政内容、新闻信息……”作为马院院长的袁久红总该有这样的权力,也该有这样的义务吧?
然而,笔者特意跑到知网上搜索了一下袁久红的“学术成果”,除了一大堆空洞无物的说教和粉饰,对无产者的现状、命运与前途没有只言片语、没有丝毫的关心;汕尾美团骑手的事,闹得沸沸扬扬,这本来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去关注的,而袁久红大半夜在干什么?
所以,对于袁久红之流的“社死”与翻车,笔者打心眼儿拍手称快,只想说一句:活该!这样的“鹿”倒得越多越好。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
通过这事,我想起一事:
我尤其不能容忍的是,现在遇到道德滑坡时,有人TMD好像顺口溜一样说什么“道德倒退了五十年”?
~~~~~~~~
我肯定!非常肯定!
道德倒退是现在,道德倒退是在“春天里”!
因为五十年前我活在那个时代,知道那个时代。
骗骗年轻人而已!
希望再看到什么“道德倒退五十年”云云,红友们要给予坚决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