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年前,有人把莫言比做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因为索尔仁尼琴也被叫做“俄罗斯的良心”,也是在文化上推动苏联解体的“公知”。
现在回过头看,索尔仁尼琴虽然魔怔抽象,但并没有脱离人的范畴,有血有肉有心肝。
莫言给索尔仁尼琴提鞋都不配,当年索尔仁尼琴虽然反苏联,但他忠诚于俄罗斯民族,他从来没有抹黑自己的民族,没有把自己的家乡说成是混乱邪恶的深渊。
相反,索尔仁尼琴反对苏联的理由是苏联打压了俄罗斯主体民族,对其他民族太好了,对俄罗斯不公正……四舍五入,索尔仁尼琴其实是个皇俄,他坚信俄罗斯的伟大和优越。
索尔仁尼琴从来没有歌颂过德国侵略者、盖世太保,也没有在作品中美化那些强奸苏联妇女、屠杀苏联人民的纳粹畜牲。
索尔仁尼琴是有骨气的,苏联在的时候他骂苏联,去美国的时候骂美国,苏联解体了他大骂叶利钦集团的腐败、无能、卖国,他还痛斥西方的贪婪、虚伪、不要脸……他不喜欢共产主义,但他更加痛恨伪善堕落的自由主义。
文人确实不该对政治指手画脚,无论左右,他们都很幼稚荒唐,比如索尔仁尼琴崇拜沙皇,他甚至希望勃涅日涅夫恢复沙皇时期的极权统治,停止建设城市并阻止科教和工业发展,并将苏联人口强制迁至农村以发展“俄国传统社会”……
他讨厌苏联的原因,其实是觉得苏联对“加盟国”太好了,觉得苏联的外交太软弱了,有这么强大的实力,为什么不干死西方那些狗东西?
他希望自己的祖国放弃那些高大上的“理想主义”,转向他想要的“现实主义”。
他骂苏联的同时,也不断指责西方社会的物欲横流、道德堕落。
1978年6月8日,他在哈佛大学发表的题为“一个分裂的世界”的演讲中,他大肆抨击西方自封的普遍主义,“西方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所有西方之外的世界只是被邪恶的政府、或严重的危机、或他们自己的野蛮、或不理解,暂时阻止他们采用西方多元民主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这是一个聊以自慰的理论,忽视了这些地方根本没有发展成跟西方相似的事实。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能转变为另一方。”
索尔仁尼琴是知行合一的,他骂苏联,他被开除出作协,被流放,他不拿苏联的钱,也不拿美国的钱,他说“我不能成为他们攻击我祖国的工具”……而莫言呢?一边阴阳怪气损自己的祖国,一边却舍不得体制内的地位和待遇。
苏联在的时候,索尔仁尼琴天天骂娘反苏,等到苏联解体了,索尔仁尼琴又后悔了,因为他发现买办寡头们统治的俄罗斯太烂了,对西方卑躬屈膝更让他忍无可忍,他晚年对于苏联解体极度痛恨、追悔莫及,他那本《重建俄罗斯》,就明确要求东斯拉夫三国不能分裂……后来他甚至连自己都骂——“你们这些傻逼,毁了伟大的苏联”。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怀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拖着76岁老人疲惫的身躯,在远东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他阔别整整20年的俄罗斯故土。
看到物是人非、满目疮痍、人民极度贫困的祖国悲剧般现状,令他的政治雄心折损大半,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联时代的看法。
后来他80大寿,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要颁给他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时,他以嘲讽的态度回应:“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权的巅峰,堕落到当前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
他内心开始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充满着无尽的惋惜:“是我害了祖国。”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他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
2005年6月媒体采访时,他公开指责俄罗斯政治现状,同时,强烈批评美国社会虚伪的民主,打着民主旗号,推行强权的做法。在《倾塌的俄罗斯》一书中,索尔仁尼琴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今天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他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
虽然他脑子不太好,但好歹他的脑子是自己的。
就连诺奖的颁奖委员会都很尴尬,因为他们不得不说那一句:“索尔仁尼琴自己也说过,除了在祖国,他不能考虑住在任何地方”。
如果给他颁诺奖的时候,诺奖委员会的颁奖词像莫言那样,把俄罗斯人形容成嗜血、疯狂、变态、愚昧、魔怔、猪狗不如的兽人。把俄罗斯国家和俄罗斯民族说成是肮脏黑暗的“猪圈”和劣等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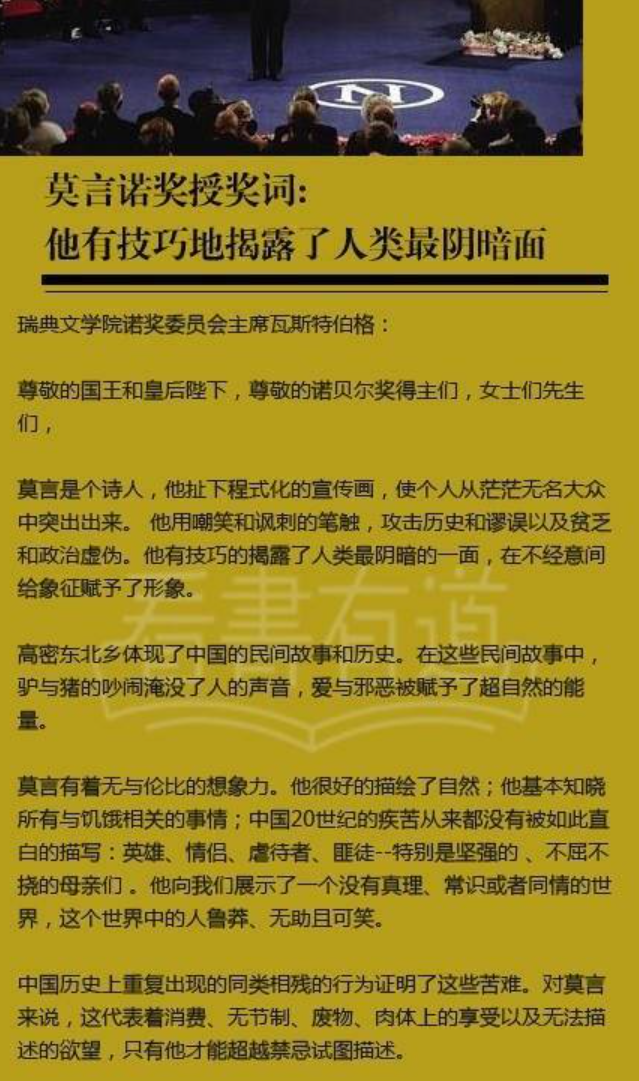
索尔仁尼琴能把那群孙子的屎都打出来,顺便把炸药奖的讲台都炸了。
而我们的莫言先生呢?穿着西方人紧巴巴的燕尾服,拘谨得像个亚裔酒保,老老实实带着微笑听完对自己祖国和同胞的侮辱,然后上台弯腰鞠躬。


民族主义者,和逆向民族主义者,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一个豪情万丈希望自己的民族称雄世界、引领世界,一个卑躬屈膝觉得自己的民族有原罪,希望被西方文明拯救……
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区别。
不,这是人和殖人之间的区别。
【本文原载“平原公子”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评论功能已恢复开放,请理性发表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