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蝇固然是可恶的,那些滋生苍蝇去围攻战士的家伙们,才是真正的罪魁!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这是鲁迅先生的杂文《战士与苍蝇》中的一段话。
后来在《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一文中,鲁迅先生又作了说明:“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
鲁迅先生关于“战士与苍蝇”的异类相比,放到上世纪捌玖十年代的文坛,亦是颇为贴切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牺牲了六位亲人,他老人家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战士,战斗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而面对刚刚逝去的毛泽东时代,年老的文坛精英们坐镇中军、派发粮饷,年轻的新秀们冲锋陷阵,如同苍蝇般对着战死的战士“营营地叫着”,用“岁月史书”篡改着历史、篡改着人们的记忆。

毛泽东时代有没有“缺点和伤痕”呢?当然是有的,如同我们第一次做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哪怕做好了再充分的心理准备,面对日常的各种琐碎,仍旧难免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从而对妻子和孩子造成各种各样的伤害……而放眼整个毛泽东时代更是如此,因为那毕竟是数千年来劳动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主的时代!
作为捌玖十年代文坛新秀的“杰出”代表,某作家最近正陷入被某网民“起诉”的舆论风波中。
虽然对于该作家的批评,笔者仅在这个公众号上就已经写了不下十篇文章,还因此被该作家盯上,不断地举报、投诉,但是,这个事件笔者本无意参与。然而,不断有读者发信息来,希望笔者谈一下这件事,于是,笔者便简单谈一下吧。
对于“起诉作家”的结果,笔者是完全不看好的,最终恐怕会以闹剧收场。毕竟作家的小说当年是经过审批、正式出版,小说的再版至今仍然在售;如果作家“罪名”成立,那些负责审批、出版的人,又该当何罪呢?
此外,笔者也并不认为“起诉”是解决思想文化论争的正确手段,即便成功了,又能对群众的觉悟起到多大作用呢?笔者认为,把该作家作为反面教员,允许群众一起来充分参与、充分讨论甚至争论,才是促进群众觉悟的正确方式。
正如笔者上面所说,捌玖十年代冲锋陷阵的文坛新秀们,之所以甘心做苍蝇,无非是冲着有人发饷罢了——这并非笔者的恶意揣测,被捧为“社会良心”的该作家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
2006年12月27日,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栏目播出了《“毛泽东热”经久不衰的秘密》的视频,这期视频请到的嘉宾是作家马未都和王斌。
王斌在节目中谈到了某作家的一段往事:

王斌所说的这张床现在就摆在井冈山八角楼的“茅坪毛主席旧居”。

“恶狠狠的说了一句话”、“恨不得在床上撒泡尿”——这些描述,将某作家对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切齿痛恨,生动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
即便王斌没有点名,但根据王斌的讲述,该作家“曾经在他的小说里用那泡尿酿出了高粱酒”,观众很容易推断出这位作家究竟是何许人也。
该作家在他那篇《毛主席老那天》(“老”——山东方言,死的意思)的文章里还只是暗戳戳抒发自己对毛主席“老”的幸灾乐祸,而在王斌所讲述的这段往事里,该作家对毛主席的痛恨可谓是极其露骨、毫不掩饰了。
那么,王斌讲这段往事,算不算给某作家“抬轿子”的人所说的“告密”呢?显然是不算的!王斌曾被称作张艺谋的“御用编剧”,还是余华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活着》的副导演,2011年他还出版过一本“反思”毛泽东时代的小说《六六年》。应该说,对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主席晚年的态度与立场,王斌与那位作家基本是相同的。只是王斌没有某作家那么下作,他对毛主席还没到全盘否定以致切齿痛恨的程度。而且王斌也不过是想要借“一位作家”的话,在节目中描述当代对毛主席的“质疑”是什么样的场景。
凤凰卫视的节目是2006年录制的,而王斌回忆说是“20多年前有一次和一帮作家到井冈山去,就去重新凭吊当年的革命先烈在那如何战斗的”。笔者查了一下相关人士回忆,著名作家去井冈山的具体时间应该是“1987年秋天”这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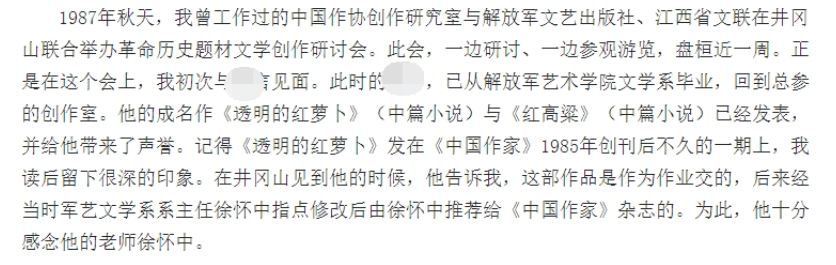
也正是1987年,王斌所说的那位作家“撒泡尿酿出了高粱酒”的小说由导演张艺谋搬上了荧幕,那时的作家已经靠着1985年发表的抨击人民公社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以及1986年发表的解构革命、“呼唤人性”、向往“蓝色文明”的《红高粱》,一时风头控诉无两,获得无数殊荣。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解构革命与反毛,与其说是一种突破,不如说是在向老的文坛精英纳“投名状”。
所以,该作家面对作家同行所表现出来的“恨不能撒泡尿”的“切齿痛恨”,更多的是一种刻意“表演”——谁“表演”得越极致,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地位。
况且,看看该作家的人生经历,笔者实在想不出彼时的作家能与毛主席有什么“深仇大恨”:
作家8岁时拍了人生第一张照片,穿着虽不光鲜却干净得体,更是被人民公社养得白白胖胖,与作家的“饥饿记忆”文学描写形成了很大反差;
作家在学校“造反”、调皮捣蛋退学,却能在毛泽东时代入伍当兵,后来又在部队考上大学、成为作家,实在看不出毛泽东时代怎么亏待了他这样的农家子弟;
而作家的两个哥哥,一个上了大学当了教师,一个读完高中成了正式职工,这是解放前的农家子弟不可能有的境遇;
作家病危的母亲是毛主席的626指示发出后被先是“省里的巡回医疗队”后来又是“县里的医疗队”救治的,而且是“义务看病,不要钱”(引号里面是作家自己的文字,当然他写这些文字主旨并非讲母亲被救,而是要讲时代和封建观念带给母亲的苦难);
反倒是作家的堂姐在80年代赤脚医生制度被废弃以后,遭遇了“意外之死”。
所以,该作家为了个人出人头地,不惜去歪曲历史、编造谎言,背叛自己的阶级,诋毁、咒骂本阶级的“救星”、“恩人”,这算不算“忘恩负义”呢?
不过,更加令人不齿的是,该作家表现得如此痛恨毛主席,却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领衔百位作家亲手誊抄“延安讲话”。
在其获得国际大奖之后,法新社记者问起了他为何要抄写“延安讲话”,显然一个老外都知道著名作家的作品与“延安讲话”精神是完全背离的。
于是,该作家为了不损害自己在教父面前的形象,又把被撕去一角的“投名状”补了回去,就回答说:
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讲话》,会感觉到它有巨大的局限,这种局限就在于这个《讲话》过分的强调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过分的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我们这一批作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后来所有的创作都是在突破这个局限。我相信有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如果他们看过我的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也就是说我的作品是跟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样的……
好家伙,从《红高粱》到《丰乳肥臀》,我们看到的是从解构革命、到咒骂革命,层层递进、步步为营,这哪里有一丁点儿“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影子?明明是越写越离谱、越写越过分、越写越嗨、越写名气越大、越写越赚钱、越写外国人越赏识,好吧?
而在获奖次年4月,国内的一次活动中,该作家的回应更加令人瞠目结舌:
现在有很多人在否定毛泽东,在把他妖魔化,把他漫画化,但我想这是在蚍蜉撼大树。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你能否定得了吗?他的《论持久战》你能否定得了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诗歌,但他的那种胸襟,那种气势,你能写得出来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书法,但你能写出他的那种龙飞凤舞、狂飙一样的字体吗?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现在有些人去把他丑陋化、漫画化、魔鬼化,是缺少理智的。现在谁要肯定毛泽东,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该作家太能给自己加戏了,污蔑毛主席和肯定毛主席都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然后该作家还敢堂而皇之地“一鱼多吃”、正反通吃!在该作家给自己立的光鲜牌坊底下,正是碎了一地的节操。
又如,作家曾跑到香港演讲,说什么“文学从来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的确,该作家从来不给中国的劳动人民和人民领袖唱赞歌,作家的笔下,穷人中也有恶棍,富人中也有圣徒,革命队伍里处处是“不堪”,但他却在《北海道的人》一文里给屠杀过中国人民的日本民族献上了极尽谄媚之词;作家的《红高梁》里的中国人是野蛮、丑陋、落后、胆小、愚昧的,作家的《丰乳肥臀》中,明明是侵略者的日军却是军容整齐,骑着高头大马,坐得端正,腰挺直,日本军医救了母亲和孩子,纪律严明,富有爱心;还有,已经落马的贪官张本才、赵志刚,都是作家曾高调歌颂过的对象……
所以,苍蝇终究是苍蝇,所为者也不过是一己之私,哪有什么“良心”,哪有什么节操?
不过,苍蝇固然是可恶的,那些滋生苍蝇去围攻战士的家伙们,才是真正的罪魁!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