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自《红凤凰》
【原编者按】2021年9月3日,美国劳工党(APL)机关刊物《红凤凰》刊发了美国南部研究生尼古拉斯·凯德·爱德华兹(Nicholas Kade Edwards)的来信,讲述了他在南部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如何跨越“红州/蓝州”(美国大选中,红色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界线而变得激进。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的左翼人士和记者震惊地发现,工人阶级反警察运动在南部小城镇蔓延。在所谓的极度保守和信仰宗教的“红州”,这些抗议活动,即使是那些打着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意识形态和旗帜的行动,是怎样办到的呢?我自己的故事深深植根于该地区工人阶级的苦难中,在政治发展的这一更大的时代背景下,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对这些动态感到如此惊讶。
在争取人类解放和战胜资本力量的斗争中,教育和组织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就像人的家庭的基础一样,教育能维持并确保人们对建立在家庭之上的组织的忠诚。
在这方面,通过国家教育机构,世界上的老板们比工人运动更占据关键优势。特别是,美国南部的潜在同志在公立学校受到无数的伤害。对美国教育体系的典型批评也适用——它的历史被净化,它的哲学被不加批判地复制,它的科学是教条的。
然而,在南部的文化氛围中,教育体系和反抗力量往往会重叠,他们聚在一起,试图创造一个完全不受质疑的无产阶级者。正如马克思曾经所描写的德国那样,在美国南部公立学校体系中,“一切都遭到强力的压制;真正的思想混乱,即极端愚蠢的统治突然来临”。
这种综合结合了南部盛行的基督教情绪和恶毒的反共宣传。正如资本主义的许多有害方面一样,这种环境是可以自我复制和自我延续的。由这些条件创造的公民和思想家在错误意识下工作,重新建立创造他们的条件,并实行紧缩政策造成今天德克萨斯州的家庭供暖不足,以及整个地区爆发新冠疫情。这种情况下的学生成长为对应的老师。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经常接触到这类老师。在我十几岁政治觉醒之前,我的老师们的保守政治思想让我觉得很奇怪,有时也觉得生硬粗鲁。毕竟,我是在一个相对非政治性的家庭中长大的。
当被问及此事时,我的父母告诉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共和党“只关心富人”,所以他们把票投给了民主党人。
当我有足够的勇气反对我的教育者的观点时,我的同学们感到震惊,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面前。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标签蕴含着危险。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民主党人——意味着你支持更高的税收、更少的“自由”和“杀婴”。更进一步讲,一个民主党人甚至可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这个词对一个南方腹地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显然,电视和电影教会了我把这个词和邪恶联系起来。
“共产党杀害的人比希特勒多。”这句话我一定在我小学和高中历史课上听过十几次了。
“俄罗斯人憎恨基督教和上帝,”我四年级的老师认真地对25个易受影响的孩子说。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我周围的世界对共产主义有一种说法:它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没有未来的选择,除了痛苦就是苦难。这种意识灌输一直持续到我十五岁那年夏天。
在2012年大选的高潮时期,南部局势非常紧张。随着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连任在即,茶党(Tea party)保守派倾向于给对手扣“赤色分子”帽子进行政治迫害,试图增加商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取代现任总统的机会。紧随着“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对资本主义有效性进行的更加公开的攻击“共产主义者”一词突然成为美国政治用语的一部分。
在我生命中的这个关键时刻,我住在祖父母土地上一个破旧的拖车式活动房屋里。在美国的另一个地区,它肯定会受到谴责。地板下垂,墙壁向后剥落,暴露在户外。隆冬时节,拖车的电气系统出现故障,使我们陷于寒冷之中。我父母分居了,我母亲靠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和三个孩子。我从八岁起就患有糖尿病,成了家里花销最大的。
受疾病和家庭贫困困扰的我无法摆脱这一感觉:我所生活的社会出现了问题。我无法理解,在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我们被允许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开始寻找答案。
一开始,我转向了自由意志主义——许多美国白人男孩走上激进道路的第一站。然而,我对激进政治的爱是短暂的。我很清楚,这个社会不需要被一个“更纯粹”的版本所取代。相反,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世界渴望重生。
慢慢地,这个想法进入了我的脑海: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它们真的那么糟糕吗?这个问题一直潜伏在我的脑海里。毕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际社会主义的化身——打败了纳粹,结束了大屠杀。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用生日时收到的20美元买了《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和《共产党宣言》。也许毫不奇怪,《宣言》给予了我最清晰的解释。事实上,这本小册子似乎呼吁革命性暴力,但我国的创造者们也是如此。我想,马克思似乎是对的。
我被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世界吸引住了。我急切地加入线上交流,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左派理论。我在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立场之间摇摆不定,最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热切地与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分享我的新政治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成了家乡的马克思主义者。

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抗议者
我经常问自己,我是怎么开始相信这些事情的?我的经历绝非独一无二;每天都有无数的儿童在同样的条件下受苦。然而,他们中很少有人因为贫穷而选择纪律严明的意识形态。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发现既快又混乱。然而,有了组织,工人运动可以触及更多的心灵和思想。
资本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无数传播其信念的机会。在南部,阶级意识正在上升。在阿拉巴马州,工人们反对亚马逊存在的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工作条件,并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抗议活动中奋起反对国家暴力。工人阶级中存在着一种愤怒——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这一点。将这种愤怒转向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获得解放的最大希望。
(编译:伊晨晨,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来源:“WorldCommunistParties”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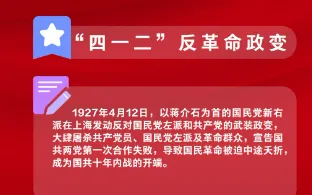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评论功能已恢复开放,请理性发表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