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收入早期恩格斯的书信来看,在不来梅1838至1841年的四年时间里,恩格斯与格雷培兄弟共进行了19次通信,其中17次通信都是恩格斯借助科学武器批判宗教。在与格雷培兄弟通信中,恩格斯实现了从宗教神秘主义到超自然主义、黑格尔的现代泛神论的根本性转变,最终走向了无神论。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自我革命,科学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在与格雷培兄弟的通信中就是运用了科学这一重要武器,不断地批判宗教,最终实现了走向无神论的自我革命。因此,基于恩格斯与格雷培兄弟的通信考察,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恩格斯如何运用科学这一武器彻底地批判宗教,最终促使他走向无神论。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和新时代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科学与宗教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
1820年11月28日,恩格斯出生在德国巴门市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中。恩格斯的家乡巴门市虽然是当时德国的纺织业中心,但是弥漫着宗教虔诚主义的浓厚气息。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位思想极其保守的基督教徒,严格要求子女接受正统的宗教思想。而恩格斯的母亲思想开明,不仅不反对恩格斯接触异于宗教的思想,更是引导恩格斯阅读歌德的作品。正是因为与理性主义文学作品的初步接触,恩格斯一开始就形成异于宗教的世界观。幸运的是,恩格斯在中学接触到了科学教育。在人文素养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双重影响下,恩格斯初步意识到宗教虔诚主义与科学相对立。1838年8月,中学肄业的恩格斯来到不来梅进行商业实习。相较于伍培河谷地区,不来梅具有更加自由开放的气息。在长达四年的经商期间,恩格斯并没有对商业投入全身心的热情,而是如饥似渴地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基于对科学与现实的关注,逐步意识到科学与宗教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
首先,恩格斯通过理性批判发现宗教的非理性特征。1838年9月1日,恩格斯就迫不及待地给格雷培兄弟写了第一封信,并且告诉他们在不来梅能够印刷许多具有“十足的自由主义思想”[1]的书籍。正是因为接触到了许多被宗教虔诚主义视为异端邪说的理性主义书籍,恩格斯开始通过理性批判审视虔诚主义。在1839年2月19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就将矛头直指虔诚派牧师:“这些家伙还自夸掌握了真正的教义,还咒骂任何一个并不怀疑圣经……的人。”[2]显然,恩格斯用理性视角剖析虔诚派牧师的宗教狂热行为,意味着他坚持理性而反对非理性。事实上,恩格斯初来到不来梅就被青年德意志派所吸引。1830年,在法国革命的自由气息吹拂下,德国文学创作团体开始用“青年德意志”名称,借助文学作品弘扬自由精神。青年德意志派十分关注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主张反对蒙昧主义以及一切落后思想。恩格斯高度赞同青年德意志派反对宗教强制的唯理主义观念。在1839年4月8日—9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就将这种唯理主义观念称为“时代观念”[3]。在恩格斯看来,自由精神与理性原则是批判蒙昧主义的利器。“这些观念正在渗入我的诗篇,并且嘲弄那些头戴僧帽、身穿银鼬皮裘的蒙昧主义者。”[4]因此,恩格斯对蒙昧主义的批判向度是基于科学的理性。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意识到宗教所具有的非理性主义色彩与科学的理性完全相悖。
其次,宗教具有反理性本质。在1839年4月24日前—5月1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就揭露了正统派反理性的极端思想:“正统派所讲的并不是要理性听从基督,不是的,他们是要扼杀人身上神圣的东西,而代之以僵死的词句。”[5]一个月后,即1839年6月15日,恩格斯在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更是直接将宗教批判的对象聚焦于圣经:“圣经教导说,理性主义者要永入地狱。……一个真诚的理性主义者,难道因为他有所怀疑就有罪吗?根本不是这样。”[6]在恩格斯看来,正统派一方面根本拿不出任何现实依据来支撑“理性主义者要永入地狱”[7]这一教义;另一方面利用宗教权威阻止理性主义者用理性检验教义,“甚至害怕纯科学领域的斗争而宁愿去诋毁对手的人格。”[8]因此,宗教正因为反理性,因而“害怕纯科学领域的斗争。”[9]毕竟科学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完全经得起理性的检验。但是与科学相悖的宗教却反理性。因此,批判宗教的最好武器应该就是理性的科学。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明确强调:“应当坚持用不可抗拒的真理去影响他。”[10]
再次,宗教根本经不起理性的检验。恩格斯在1839年6月15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强调:“只有能够经受理性检验的学说,才可以算做神的学说。”[11]但是建立在非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神的学说,根本就不可能经受理性的检验。之所以经不起理性的检验,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圣经的内容是虚假的、不可信的;另一方面,圣经“作者中的很多人甚至自己也对神性无所要求。”[12]因此,对宗教的信仰只能建立在盲目服从的基础上,因为圣经的绝对权威依赖于全盘接受。对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是谁赋予我们盲目地信仰圣经的权利呢?不过是在我们以前就这样做的那些人的威望而已。”[13]因为圣经内容存在大量的真实矛盾。而正统派将这些矛盾归结于文字形式的习惯问题。对此,恩格斯认为这种解释是建立在非理性的依据之上,“以致这种解释根本不能叫解释。”[14]正因为如此,宗教根本就没有与科学的理性进行论战的能力,更无法经受理性的检验。
最后,宗教信仰无法用科学理性来支撑。恩格斯在1839年6月15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面对圣经的谬误时,强调:“如果这里有什么矛盾,那么,对圣经的全部信仰就被毁掉了。”[15]正是因为认识到理性的科学与非理性的宗教是根本对立的,恩格斯不满足于屈从一种非理性的信仰。诚如胡大平所言:“时代处在激烈的思想变迁过程中,而青年恩格斯又如此迫切地希望占据真正的时代精神。”[16]一方面,圣经中的真实矛盾动摇了他的宗教信仰。在1839年7月12日—27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宗教信仰的基础进行质疑。在恩格斯看来,宗教在与科学的论战中面对教义中存在的真实矛盾,只能“做点思想分类工作、做点解释、辩论辩论”[17],而不能拿出任何的依据来进行科学论证。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强调:“谁要满足于这种状况并且炫耀自己的信仰,那他的信仰就没有任何基础。”[18]另一方面,恩格斯迫切寻求先进思想以实现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此时恩格斯受到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的深刻启发,将宗教批判聚焦到上帝的实存问题。在恩格斯看来,宗教信仰不是以理性为基础,而是以感觉为基础。而“感受当然可以证实,但决不能作为依据,正如耳朵不能辨别气味一样。”[19]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上帝。
总之,恩格斯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已经认识到科学与宗教之间实际上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宗教从根本上说是非理性的,因而不仅经不起科学理性的检验,也不能进行纯科学的研究。
二、科学与宗教是现实与虚幻的对立
如果恩格斯仅仅在理论层面认识到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关系,那就远远不够,不足以促使他完全放弃自己的有神论。而要彻底地批判宗教虔诚主义,就需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现实出发来彻底批判宗教虔诚主义的伪善性和神秘性。只有这样,恩格斯才能彻底清算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走向无神论。
首先,对宗教虔诚主义展开批判需要由理论转向现实。虽然恩格斯就读的爱北斐特理科中学弥漫着浓厚的虔诚主义气息,但是他学习了地理、数学和物理等自然科学,因而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素养。特别是,恩格斯在母亲的引导下阅读了大量歌德的著作并且非常崇拜歌德。而歌德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尤其钻研了博物学。因此,恩格斯虽然怀着文学梦来到了不来梅,希望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对现实自由的向往,但是在科学理性的影响下,逐步认识到了宗教虔诚主义的愚昧,不仅在理论层面与科学处于对立,在现实中也是如此。恩格斯在1838年9月17日—18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附录的《贝都英人》中,就直接表明了他对打开现实自由大门的向往。此外,恩格斯在学习经商和文学创作之余也接触到不来梅的现实,因而充分认清伍培河谷地区被宗教虔诚主义笼罩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就促使恩格斯认识到仅仅沉浸于文学的揭露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恩格斯深刻认识到,进行文学创作并不能改变社会现实:“仿佛思想正从我的头脑中消失,仿佛我的生命正被夺去,我精神之数的叶儿正在纷纷飘落,我的风趣都是矫揉造作,它们的内核已从壳中脱落。”[20]可见,恩格斯已经不满足于从文学层面谈论神学问题,而是转向了现实,试图清晰地揭示宗教产生的现实基础。
其次,从现实层面揭露宗教虔诚主义的伪善性。恩格斯在1839年2月19日致弗里德里希· 格雷培的信中就强调:“宗教上的东西通常都是胡说八道。……这些都阻碍人们精神上的发展。”[21]宗教总是宣扬完全脱离现实的虚幻天国和来世,因而宗教教义与社会现实完全相悖。之所以恩格斯能够形成这样的认识,从根本上说,伍培河谷地区就是宗教信条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典范”。1839年1月—3月期间,恩格斯撰写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伍培河谷来信》就是基于现实生活的考察,揭露了宗教虔诚主义的伪善性。毕竟当时的恩格斯一直生活在交织着浓厚的工业气息与宗教氛围的环境中,因而他能够透彻地认识到宗教信条不仅不能够引导人们走向幸福,反而还给人们带来现实的压迫。罗燕明研究认为:“《乌培河谷来信》仅仅是恩格斯摆脱宗教世界观的起点,其着眼点放在虔诚主义对乌培河谷造成的社会恶果上,还不是对神学理论和整个宗教的批判。”[22]因此,为了对宗教教义的现实基础进行批判性解读,恩格斯持续地研究自然科学与关注社会现实。“随着在实践中接触更多的社会现实,……他的认识超越了纯粹的文本批错与哲学思辨,必然地要涉及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层面。”[23]在1839年10月29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就直接揭露了宗教中“原罪论”的现实基础:“罪恶是由尘世生活的各种条件引起的。”[24]在恩格斯看来,罪恶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人类发展的阶段产物。因此,恩格斯将“罪”归结于尘世生活的各种矛盾,反映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理论思路去揭露宗教教义的虚幻性。朱传棨也指出:“这时的恩格斯已不是站在宗教唯心主义立场上理解宗教教义了,而是以社会现实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来批驳宗教教义。”[25]
再次,要摆正宗教教义与现实的关系。恩格斯在认识到宗教虔诚主义与社会现实相脱离之后,进一步动摇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为了完成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恩格斯用科学作为理论武器,围绕神学世界观展开批判。恩格斯在1839年6月15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写道:“如果地质学作出的结论不同于摩西的创世史,它就会遭到诋毁……如果它作出的结论似乎和圣经所讲的相同,就会被引以为据。”[26]在恩格斯看来,宗教总是垄断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甚至将自然科学规定在神学体系的界限之中。实际上,科学是现实世界本质及规律的反映,神学则用现实服膺于信条。因而神学的世界观是颠倒的世界观。在1839年10月8日致威廉·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就进一步揭示了神学世界观的颠倒本质:“把人所共有,众所周知的事实仅仅局限于教徒。”[27]可以说,宗教总是颠倒现实与教义的关系,将“现实世界支配于某个神灵观念,试图让现实符合教义。”[28]因此,厘清宗教教义与现实的关系是恩格斯树立科学世界观的前提,也促使他基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审视宗教。而之所以恩格斯能够坚持运用科学分析方法,是因为他始终致力于批判现实关系的内在矛盾。毕竟“青年恩格斯并不想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他是想成为批判现实生活中各种具体关系的理论战士。”[29]因此,恩格斯不满足于用神学视角看待尘世生活,而是倾向于用现实的眼光批判神学。
最后,宗教虔诚主义的宣扬完全是虚假的,与科学完全相对立。1839年3月—4月期间,恩格斯在阅读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后就被其中的宗教批判思想所折服。恩格斯认识到,圣经故事不过是不同作者所编撰的神话故事集;宗教的历史不过是一部煽动宗教狂热的教会史。在1839年4月29日前—30日致威廉·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进一步驳斥了正统派的虚假宣传,即:“地球是不动,太阳围绕地球旋转。”[30]显然,宣传虚假教义的宗教与反映现实的科学是根本对立的。恩格斯基于科学理性,揭露了宗教教义的虚幻本质。恩格斯在抛弃宗教信仰之后,就放弃了对宗教自由的追求,而是关注现实的人的解放。1839年10月29日,恩格斯在致弗里德里·格雷培的书信中就直接认为,宗教是维护腐朽制度的“华丽的外表”[31]。宗教精神麻痹人们的心智,将人的思想禁锢在神学世界观中。而科学理性则给人呈现了另外一种世界观,即人类相信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实现尘世生活的幸福。因此,宗教的宣传违背了科学与现实,因而具有伪善性。
总之,恩格斯在科学理性的影响下,不但认识到宗教的非理性特征;而且揭露了宗教的虚幻性。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立足社会现实,既从理论层面批判宗教学说,又从现实层面揭露宗教的虚伪。
三、科学与宗教是真理与谬误的对立
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但是始终对科学保持着强烈的兴趣。从恩格斯的《中学肆业证书》的评语可见一斑:“该生不仅资质很高,而且表现出一种力求扩大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值得赞许的愿望。”[32]正因为对科学技术的持续关注,恩格斯日益意识到宗教思想矛盾重重。在1839年4月29日前—30日致威廉·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就强烈鞭挞虔诚派牧师宣传地心说的行为:“这个家伙竟敢在1839年4月21日公开地宣扬这种货色,同时断言,虔诚主义不会使世界返回到中世纪!”[33]地心说早已经被科学摒弃。但是宗教虔诚主义竟然公开反对科学。因此,在恩格斯看来,科学与宗教就是真理与谬误的对立。
首先,恩格斯揭露了宗教随处可见的谬误。在1839年4月24日前—5月1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围绕圣经内容的真实性,向当时就读于神学系的格雷培提出质疑:“所有这一切怎么能同真实性,即同福音书作者的文字的真实性一致起来?”[34]而格雷培将恩格斯对圣经内容的质疑归结为“咬文嚼字”。显然,恩格斯并不赞同这种解释。他认为,圣经的矛盾是真实存在的。圣经不仅没有科学的理论依据,甚至反对寻求科学真理。面对圣经与科学真理之间的冲突,恩格斯一方面进一步质疑了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急切地寻求真理。在1839年7月12—27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写道:“你不了解一个人随着最初的怀疑而开始感受到的那种负担即旧信仰的负担是何等沉重,他必须决定是维护还是反对、是承担还是摆脱旧信仰。”[35]在恩格斯看来,圣经的内容都是编造出来的,并不具有真理的成分,是十足的谬误。而圣经的谬误直接促使恩格斯质疑宗教信仰。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力图寻找科学真理来摆脱宗教的束缚:“我每天甚至整天都在祈求真理;我只要开始怀疑,我就这样做,但是我不能转向你们的信仰。”[36]正因为 “教义中的矛盾相当多,同圣经的作者一样多。”[37]恩格斯就放弃了用科学理性重新解读圣经的想法。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圣经根本就不值一读。因此,恩格斯有了与格雷培兄弟决裂的想法:“如果你是照圣经办事,那就根本不必同我打交道。”[38]至此,“借着《圣经》的矛盾这条绳索,恩格斯使自己摆脱了过去对《圣经》的沉湎。”[39]
其次,恩格斯揭示了宗教教义直接与真理相对立。恩格斯正是依据自然科学知识,认识到宗教教义与真理是直接相对立的。在1839年6月15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依据地质科学,指出《圣经》中关于上帝创造宇宙的说法并不符合地质学。因而上帝的“创世史”是虚假的,且与科学根本对立。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强烈反对宗教通过扼杀科学来维护教义权威:“如果某个地质学家讲,地球和化石证明曾经发过一次洪水,这就会被引用;但是如果另一个地质学家发现了疑点,认为这些化石属于不同地质年代,……地质学就会遭到谴责。”[40]宗教卫道士总是将《圣经》作为解释现实世界的根本依据,并将自然科学视为支撑宗教权威的奴仆。对此,恩格斯直接质问格雷培:“这样做难道正当吗?”[41]在恩格斯看来,对教义的信服必须建立在基本的理性之上,即必须符合科学。因此,恩格斯强调:“凡是科学屏弃的东西……在生活中也不应当继续存在。”[42]毫无疑问,宗教教义是与真理相对立的谬论,根本经不起科学理论的检验。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反对盲目信服宗教教义,并驳斥将《圣经》视为评判一切的标准。
再次,恩格斯揭露了宗教与真理在认识论上的对立。在恩格斯早期批判宗教的过程中,科学不仅是恩格斯批判宗教的最锐利武器,而且强化了恩格斯的批判思维。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强调用科学的批判精神去考察宗教,反对盲目信服神学。在1839年7月12—27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就反驳了格雷培关于不能对宗教提出质疑的言论:“你说,不能怀疑就是最大的精神自由吗?这是最大的精神奴役。”[43]一方面,宗教自称教义是永恒的、不容置疑的真理。而科学真理强调任何科学认识都具有相对性。对此,恩格斯认为,自称是绝对真理的宗教就应当用科学理论进行验证。但是神学根本就无法与科学真理进行论战。因此,恩格斯总结道:“我不能承认你们的真理是永恒真理。”[44]另一方面,追求真理需要具备科学的批判精神。但是宗教不仅反对它,而且还要人们放弃它而盲目地服从宗教神学。因而宗教根本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当格雷培面对恩格斯的质疑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并要求恩格斯盲目服从上帝信仰时,恩格斯直接反驳道:“教条式的信仰对内心的安宁并无任何影响。”[45]因此,恩格斯正因为意识到宗教根本不是真理而是谬误,进而放弃盲目信仰宗教。
最后,恩格斯坚持科学真理、反对宗教神学。面对宗教与科学的根本对立,恩格斯曾经陷入剧烈的内心冲突中。但是,“正是在信仰的困扰中,在紧张、激烈的自我反思、自我斗争和自我否定中,恩格斯才找到一条走出信仰迷宫的通道。”[46]1835年出版的《耶稣传》帮助恩格斯进一步认清宗教的本质。恩格斯在1839年4月24日前—5月1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说,他正在研究施特劳斯的宗教批判思想。不到半年,即1839年10月8日,恩格斯在写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就坦言自己已经是施特劳斯派,并且强调自己已经完全抛弃了宗教信仰:“大卫·施特劳斯像一位年轻的神一样出现了,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永别了,宗教信仰!”[47]在恩格斯看来,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提供了从历史视角驳倒宗教的方法。恩格斯认识到,神学世界不过是神话故事的堆砌;因为神学的历史基础根本不存在,宗教的宣传违背科学。在金民卿看来:“恩格斯在这里把施特劳斯幻化成理性的化身,他崇拜的实际上并不是施特劳斯这个人,而是被他放大了的,附加到施特劳斯思想中的自由、理性和科学精神。”[48]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出场语境。在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写道:“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所以,我加入了莱奥和亨斯滕贝格所谓的‘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49]虽然此时恩格斯还没有完全形成无神论思想,但是从恩格斯与格雷培兄弟的通信分析,他一直崇尚科学、批判宗教。因此,在1841年2月22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最后一封信中,恩格斯用“再见”[50]两个字向友人作出最后的告别。这也是恩格斯向格雷培兄弟秉持的正统派信仰进行告别。而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完成艰难的自我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他始终崇尚科学、坚持真理。
因此,恩格斯正是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认识到,宗教将教义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将神迹视为事实,将自然科学知识曲解为谬误。恩格斯看到了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进而借助科学这个强有力的武器批判宗教虔诚主义,最终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
四、结 语
恩格斯不是一个天生的无神论者,他经历了由宗教神秘主义到现代泛神论,最后走向无神论的心路历程。恩格斯之所以最终选择抛弃宗教信仰,主要是因为他在关注科学与现实的过程中发现了宗教与科学存在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恩格斯在与秉持正统派神学观点的格雷培兄弟的通信中,清晰展现了他借助科学武器批判宗教的思想历程。虽然在通信中并没有明确的表述说明恩格斯已经成为了无神论者,但是他以现实考察教义、以科学反击神学,就已经表明他正在朝着唯物主义的方向上迈进。恩格斯正是在用科学和现实考察宗教的过程中开启他的自我反思、自我革命、自我超越之旅。因此,只有了解恩格斯早期宗教批判思想,才能更加准确地理清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肇始、发展以及贡献。这对我们依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首先,要崇尚科学。可以说,恩格斯与宗教愚昧作斗争的过程就是他崇尚科学的过程。在信息爆炸时代,借用科学名号欺骗大众的“伪科学”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科学文化素养,以科学改变无知。其次,要关注现实。青年恩格斯能够抛弃宗教信仰与他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而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激荡澎湃并给社会带来革命性变化。我们也应该像恩格斯一样关注科学技术,并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最后,要树立科学信仰、抵制愚昧落后。恩格斯正是在驳斥宗教谬误的过程中,加深了科学信仰。我们也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弘扬科学精神。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4-18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4页。
[16]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
[22]罗燕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1833~1844)》,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90页。
[23]蔡鹏飞、汪小丽:《恩格斯早期宗教批判的理性化与人本向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8年第2期。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3页。
[25]朱传棨:《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论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28]王贝特、陈天嘉:《恩格斯宗教思想批判的理论定位》,《科学与无神论》2022年第3期。
[29]唐正东:《青年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4-17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
[39][澳]罗兰·玻尔:《尘世的批判——论马克思、恩格斯与神学》,陈影、李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10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5-186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0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
[46]牛苏林:《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51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48]金民卿:《青年恩格斯告别:“乌培河谷时期信仰”的历程及启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4期。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8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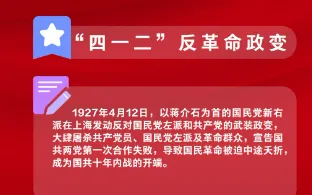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评论功能已恢复开放,请理性发表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