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日,正好笔者最近了解到卢卡奇的思想观点,就顺便看了看卢卡奇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所作的纪念小册子。想从同时代的人那里看看:“列宁”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最为重要的一点莫过于列宁对革命现实性的把握了。
(一)革命的现实性
什么是革命的现实性?革命的现实性就是对革命是否到来的认识和对革命发展形势的判断。正如卢卡奇所说,革命的现实性是“列宁思想的核心,是他与马克思的决定性联系”。一般而言,革命的现实性这一条或许称不上“核心”,但其重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

图1 列宁在十月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以及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理论也逐渐在实践中展开。从今天看去,所谓历史上的革命形势自然要明朗得多:俄国革命怎么能成功?——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等等。欧洲其他各国的革命何以失败或根本没出现?——这又要归咎到策略问题、工人贵族问题、修正主义问题等等。但在当时看来,革命的现实性却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而与列宁论战的既有机会主义者,又有修正主义者,还有带着幼稚病的“左派”。
(二)机会主义者
机会主义者,他们既害怕资产阶级的力量,又害怕无产阶级的力量,只不过前者是后者的原因罢了:他们害怕无产阶级力量的兴起会遭受资产阶级的打击,在实际上却表现为害怕失去当前的地位。一旦无产阶级群众上街了,开始战斗了,他们反而退缩了,甚至咒骂群众不懂形势云云。他们自然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不是还曾告诫巴黎工人们不要在国外敌人兵临城下时贸然起义吗?不过,马克思与机会主义者截然相反,他虽在巴黎起义前告诫工人不要轻举妄动,但是当在工人群众奋起行动之后,他便以参加者的态度密切关注这场运动。他同工人们一起前进,同工人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打官腔或者教训他们。即使失败,他也是认真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他更重视的是工人阶级英勇地、奋不顾身地、积极地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可是机会主义者呢?他们只是在失败后表现出一种“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的庸人般自鸣得意的姿态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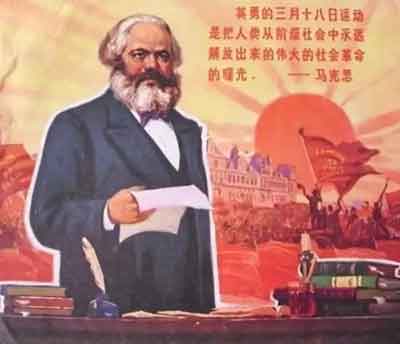
图2 马克思对巴黎起义的热情称颂
当然,机会主义者本来也会去指出马克思的“错误”。尤其是,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不是成功了吗?——马克思的预见,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发达国家爆发”,并没有应验。但这也并不能成为机会主义者们抛却预见、像列宁一样积极参与运动的理由,因为在他们看来,列宁的“历史局限性”正是“他不加鉴别地就把俄国现实中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一般化,普遍地加以应用”,正如某些人责备马克思将对英国的观察“一般化”地应用到其他国家一样。
可是,无论是列宁还是马克思,都没有对俄国和英国的特殊经验做机会主义者所说的“一般化”。只不过,对列宁的指责和对马克思预见错误的指出,恰好为机会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在自己紧绷的思想里避风的港湾而已。在这里,机会主义者可以暂时脱离令他们苦恼的现实而在空虚的思辨中畅想——他们尽可以在这里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批判社会;他们或许希望,在这样的思辨中就能提出超越马克思和列宁的更“完善”的理论——至少是能使他们的“想象力”或“批判力”满足的理论;不过非常可惜,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仍然要回到苦恼的现实中来。
(三)修正主义者
修正主义者比机会主义者更直白而不加掩饰——他们的经济利益相对机会主义者有更为稳固的地位,他们的理论也采取了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更稳固的形式。卢卡奇谈到,修正主义“试图克服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性’”,希望“单单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解释所有的社会历史现象”,其结果则是修正主义最终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作为其立场。不同阶级的矛盾在他们的理论中似乎消解了(当然也仅仅是在理论中),于是辩证法也立刻失去了其作用——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就失去了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或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或者是将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移到“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去解决(“遥远”,也就是永远达不到的地步),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方法了。
但是,修正主义者本来是这样产生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帝国主义的发展,垄断资本可以把利润中的一部分用来收买一小部分的工人,从而使得工人阶级中的这一小部分集团可以暂时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同时这也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教育和自身发展水平等等,因此他们可以更加容易地进入工人组织或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并进而可能“代表”广大革命群众。他们所推崇的“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实际上也只能表现为维护一部分集团的利益,具体地讲,则首先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然后是他们自己的地位。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一战时期列宁、卢森堡等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不断呼吁下,第二国际中的修正主义者们喊出的正是嘹亮的“保卫祖国”呵!可是,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源源不断地将无产阶级送上战场,让他们为资产阶级和自己的利益拼死拼活,仅此而已。哦,不对,他们可能还会为战场上不小心殒命的人们而悲痛;可是毕竟殒命了: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整个社会”的利益呵!

图3 伯恩施坦、考茨基与赫鲁晓夫
但修正主义并未在这里停下脚步——在列宁身后的苏联,“全民党”等概念也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思想中孕育而生,也许这里的用词比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更“马克思”,也更“实际”(因为至少俄国革命曾经夺取了政权),但实际内容没什么不一样。正如很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内部形成的脱离群众的利益集团成了修正主义的沃土一样,苏共党内腐化的高层们自然也心照不宣,他们的不同点或许只在于:后者因为一度解放的群众所创造的伟大生产力而握有更大的力量。当然,这样下去的结果也就是退一步到资本主义,毕竟资本的力量更适合于完全成为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者去掌握。我们自然希望无产阶级能在经受这沉痛的教训之后“退一步,进两步”。总之,以史为鉴,更进一步。
(四)带着幼稚病的“左派”
实际上,卢卡奇自己就承认,列宁对他的文章《论议会制问题》的批评,也就是对“左派幼稚病”的一种批评,恰恰“指出了决定性的差别”。
在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卢卡奇流亡维也纳并成为了《共产主义》杂志的核心成员,这一时期他与所谓“左派”接触很多。他们往往相信这样一种“流行”的信念:“伟大的革命浪潮将推动整个世界,至少是欧洲,一直到达社会主义,它决没有因为芬兰、匈牙利和慕尼黑起义的失败而中断。”卢卡奇自言他们“有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的抱负”,看上去似乎是“唯我独革”、“唯我彻底”。
这种思潮仅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是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反动,有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感觉。但从经济现实来看,这种极端的“革命性”又是怎样产生的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量的小资产阶级被抛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带来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正是被大工业、被所谓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打击成这样的,因此他们反而产生了这种极端的“革命性”。

图 4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正如卢卡奇所描述的自己的二重性那样,他们往往在理论上夸夸其谈(即使某些深入的思考对于理论本身有重要意义),但是一到实践里面就往往变得盲目,要么是只取理论的预见作为想象而不加以考察实际和实现的路径,要么是完全脱离科学理论地实践——因而也必然脱离了群众运动发展的实际境况。他们也可能形成十分严密的组织,但这种组织往往是以脱离经济基础的“同志情谊”和单纯却不够坚定的理论信仰为基础的(如前所述,理论在实际上只就其预见来说形成了信仰)。因此,在革命的实践中,这种组织在反动势力的镇压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很有可能一触即溃,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这些人空有“一腔抱负”却一事无成(甚至完全倒戈为替反动势力辩护的“好分子”)——更坏的结果则是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使得正在兴起的群众运动受到严厉打击。
(五)列宁
我们可以看到,前述三者其实都是“教条”的,只不过机会主义者与修正主主义者陷入的是现实的教条——这使得他们在实际上陷入了为资产阶级社会作看起来是暂时实际却是永恒的辩护,而带着幼稚病的“左派”却秉持一种革命的教条——这使得他们往往陷入小资产阶级式的理想主义而缺乏对革命现实策略的有效把握。这样,他们不仅没有真正地发展理论,而且也没有真正地发展实践。但列宁不是这样的,正如卢卡奇所说:“对列宁来说,即使最普通的哲学范畴,也从来不是抽象的思辨上的一般性:作为理论上准备实践的工具,它们总是适合实践的。”

图 5 列宁
对列宁来说,因为革命的现实性已经如此明显,所以无论什么理论都应该落实到实践中去思考——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间,他也优先选择实践,毕竟“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这首先要求一点,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正是俄国革命得以在列宁的领导下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率先在发达国家爆发的预见早已是为人所知的,但只有列宁清楚,这本来不过是马克思依据由当时的现实情况形成的理论所做的一次模糊的预见而已。如果把这个预见奉为教条用来指导不断有新的事变发生的现实,那么显然就会回到资产阶级的超历史的观点中去了。因此,既然列宁已经在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中看到了革命的现实性,那么就去把握它,而不是拱手让与羸弱的俄国资产阶级。
可是,当俄国革命成功后,“革命”本身又成为了反抗的教条,似乎所有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人都应当立即联合在一起发动最为激烈的革命。列宁在此时仍然是清醒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列宁妥协了,列宁居然向同盟国妥协了——苏俄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因俄国革命几乎胜利而“憋屈”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在这里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妥协是与列宁的妥协一样的,这样,他们甚至可以抬举列宁,说他是“非教条的权力政治家”。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派”自然也反对这种妥协,这从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几经波折就可以看出。
我们要明确的是,列宁的妥协本就是一种政治策略,它是建立在革命的现实性及其具体环境上的——也就是说,它首先是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而且是在为其进一步发展做准备的,是通过“退一步”来“进两步”的。但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做了妥协。这种妥协,要么建立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否定态度上,要么建立在不顾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已经大大地发展起来而仍然盲目悲观和“谨慎”的基础上——都已经脱离了革命的现实性。
总之,列宁总是与革命的现实性紧密相连的:列宁的理论因切中革命的现实性而深刻;列宁的实践因革命的现实性而具体;理论与实践,这二者因对方的彻底而彻底。
(六)昨日与今日
可惜的是,“天才”般地把握革命现实性的列宁终究是走了;可喜的是,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庆祝伟大人物的诞辰。当然,我们不应该把列宁当作一尊用以祈祷未来的神像——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无害化的神像从来只有愚弄被压迫者的作用而已,仅此而已。
我们应当去学习列宁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更重要的则是懂得其实践——这本身也已经成为了理论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总是要把理论视作更高尚的东西的话。我们应当不断地自我教育,深入社会,始终接受新的经验教训,就像列宁不仅能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取得知识,而且也能从一个工人对面包的意见中取得认识一样。我们应当学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做超出现实客观环境的贸然想象——卢卡奇提到的一个例子让我印象深刻:在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捷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列宁被询问关于捷克问题的意见;但是列宁由于国事繁忙还没有仔细看相关的资料,因此他想推脱,可是众人仍希望他给出一些意见;于是,列宁掏出了口袋里跟捷克问题有关的报纸,开始就相关文章的记述做分析——可是“这种即兴而作的概述变成了对捷克形势和捷克共产党的任务最深刻的分析”。
列宁并没有看到昨日世界的落幕;它在今日还存在着。可是,新冠疫情下,它已经显示出了其千疮百孔的窘态;已经有群众运动起来,与它的秩序相对抗了。而今日,正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我们又会交上怎样的答卷?不是拭目以待,而是积极参与。
主要参考文献:
[1]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
[2]列宁《国家与革命》。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版序言。
[4]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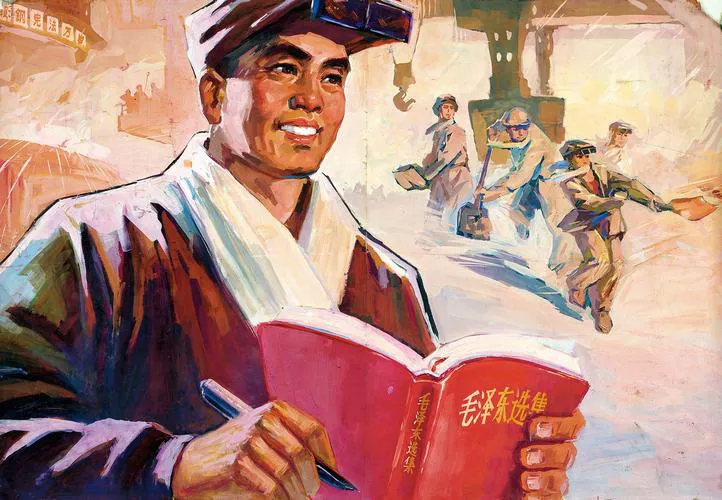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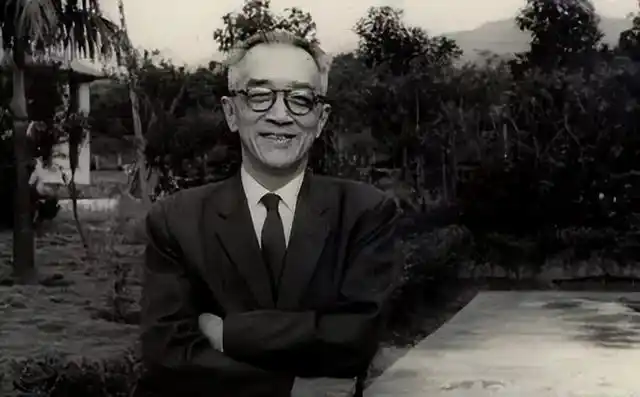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微信或手机浏览器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