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整整百年曲折而辉煌的历程,百年考古就“中华文明独特文化基因”这一重大问题建构与实证了什么?回顾以往,从丰富的考古资料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出发,可以形成一些初步认识。
持续发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
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一个包含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的长期进程。就中原地区而言,综合百年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大体在距今6000年左右庙底沟文化的相关聚落中开始出现社会分化与不平等,是该区域文明起源的开始,是各种文明要素起源并不断聚积的阶段。之后社会不断发展,历经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等阶段,在距今43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晚期出现了明显的“国家形态”,进入了文明社会。如都邑性质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具有城址、等级墓地、铜器、礼器、宫殿及礼制建筑等齐备的文明要素。经过距今4000年以后新砦文化时期的国家形态的早期发展,至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文明中心地位形成。后经商周时期的巩固与进一步的迅速发展,华夏文明逐步走向辉煌。
长江下游地区至少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早期社会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层现象,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的新发现就反映了这一点,该地区自此开始迈入文明化的进程。崧泽文化之后该区域在经济、文化、政治结构方面不断发展,社会等级分化不断加剧,历经距今5300年开始的良渚文化早期,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中期始,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都实证此时良渚社会已进入文明时期。良渚文化晚期,文化日渐衰弱,社会结构和权力趋于分散,该地域的良渚社会逐渐走向衰亡,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社会复杂程度不高,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在这一时期进入了低谷。马桥文化之后,这一区域随着周人的南下而逐渐被纳入中原地区文明和国家一体发展的历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黄河下游的海岱文化区也是在大体距今6000年左右的北辛文化末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开始出现分层分化的现象,是该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肇始时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后,进入了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其晚期时,聚落群至少形成了大、中、小三层的金字塔式布局结构;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城址的大量出现、聚落群的复杂分化、山东泗水尹家城和临朐西朱封遗址超大型墓的发现等,表明社会等级分化严重,社会组织和结构复杂,王者雏形出现,礼制初步形成,社会进入了国家形态,海岱地区古代文明社会形成。需要注意的是,整个海岱地区内的社会发展并不平衡,也未出现像良渚社会一样绝对的文化与社会的中心区域。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时期文化急剧衰退,商周时期海岱地区逐渐为商周文明所辐射控制。
红山文化在距今6700年左右出现于西辽河流域,延续发展到约距今5300年的晚期才开始出现社会分化;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其文化末期社会分层加剧,进入文明时期。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文明化进程是从距今6000多年的大溪文化中晚期开始的,而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该地区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关键时期,尤其在距今4500年左右形成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遗址群和整个文化区的中心,然而在距今4300年左右的峰值期将要迈入文明社会门槛时却逐渐衰落了下来。之后中原文化逐渐南下,该区域进入夏商文明直接影响的发展阶段。近些年,在晋陕高原地区发现了距今4200~3800年的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石峁城址所代表的文化与社会也应该进入了文明阶段,但其前身文化发展还有待探索,而之后石峁城址废弃,这一文明在其演进过程中中断,一些文明遗产在与周边地区其他文化互动交流中被吸收利用。
中华文明是一个经历了起源、形成以及连续发展的独特文明,有着较为明显的“文明化”的过程,虽然存在复杂多样、非单线的进化,甚至某些文明进程的“断裂”,但整体上仍是“螺旋式”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个别断裂的区域文明并非彻底消失,其中一些重要的文明因素多被其他区域文明吸收、融合、改造,作为文明基因传承下来。
海纳百川与务实创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绵不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深层原因是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在今天中国的地域范围内,史前时期每一个地理单元或地区如燕辽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中原地区等都有着各自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区域文化各有特色,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而且这些不同区域在各自文化或连续、或间隔、或中断的演进变化的同时,文化之间存在互动交流。对于某一考古学文化而言,文化互动的结果直接表现为周边诸考古学文化先进因素不断汇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良渚文明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及礼制系统,显然与早于良渚同样玉器发达、宗教色彩浓厚的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且相邻地区的二者之间明显存在着一兴一废。此外,良渚文化发现有数千里之外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特征的玉器也是学界的共识。中原地区这种兼收并蓄的特点更为明显,尤其到了距今45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文化间的融合与交流在中心或都邑性遗址中的表现达到一次高峰,甚至形成一波浪潮。晋南陶寺文化中更是同时存在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东北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或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重要因素。龙山时代的晋陕高原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之间在陶器、玉器、铜器、乐器、建筑技术等各方面存在互动交流已是不争的事实。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最新发现的石雕图像对东北地区石雕传统的吸收十分明显,而一些石雕的兽面与人面饰却又与远在江汉平原的后石家河文化多有相似者。至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汇聚融合四方先进文明因素再次达到一个顶峰,并且二里头礼制文明传播辐射到了周边以及更广阔区域,这一点已成常识,不再赘述。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与多元,使得不同文化在互动、交流与传播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开放、融合的文明特质。
距今约5000年明确进入文明形态的良渚社会宗教色彩极其浓厚,墓葬中满目祭祀礼神的玉璧、玉琮及繁缛复杂的神性纹饰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红山文化晚期辽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庙、坛、冢结合的宗教特征及其聚落结构,包括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如玉人和各类动物形玉器以及非实用陶器,虽然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墓主的身份地位,但其主要作用当为沟通人与神的宗教法器或巫仪神器。将文化统一到对神的认同上,信仰与神性是统一的,这种社会可以迅速积累财富与集中资源,实际上是投入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把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在虚无缥缈的神灵之上,长期来看十分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而在距今4300多年,经历之前神性“务虚”的阵痛与冲击后,世俗的“务实”品质成为文化与社会的主流。这一点或许在更早些的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已经表现出来,最能反映文化与社会务实特质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尤其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中少见宗教性大型建筑,却舍得耗费力量修建城池,“筑城造郭”,用于防御外敌入侵。在陶寺遗址中期小城内考古发现了具有系统“观象授时”功用的大型夯土建筑,该建筑经过多年实测与研究,推测当时可以观测20个节气。所谓“观象授时”,授的是与物候密切相关的“农时”,主要用于指导当时的农耕种植,发展农业经济。而农业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经济形式,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支撑。显然,陶寺文化时期,重视农业生产就是最大的“务实”。陶寺社会集团的统治者们似乎在宗教祭祀方面的投入与经营相对较少,而将主要力量放在生产性劳动领域,作风务实,并致力于礼制的建立,这就在客观上有利于其实力的积蓄和可持续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史前区域文化对外来文明因素的吸收融合大多不是简单的复制性效仿,而是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多有创新。良渚文化玉器最具特色的神人兽面纹之外的鸟纹及变体鸟纹应是源于大汶口文化,进入良渚社会后与神人兽面纹组合相融成一个整体。之后,进入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与社会扬弃式吸收外来先进文明因素,例如创造性使用范铸铜容器,成为辉煌的夏商周三代青铜铸造技术之始。日常用具也有经改造的情形,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更少见与原产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现象,而是创新出多璜联璧、组合头饰、组合腕饰等新的象征物以凝聚族群。
中华文明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海纳百川与务实创新的特质,这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独树一帜的深层原因。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模式
中华文明在其文明发展历程中复杂多样,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古老文明,难以用任何一个已有文明模式来概括与比附,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文明社会形成的最突出标志。他在论述国家兴起时指出了雅典形式、罗马形式和德意志形式等主要形式。就百年中国考古实际而言,这三种形式的任何一种都难以适合中华文明的内涵。目前已知进入了文明时期的陶寺社会既有“氏族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也有“平民和贵族斗争”。而依据属于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考古材料,二里头社会显然既有内部阶级对立,又有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还有明显的对外扩张,至少是此三种因素相结合的结果。
从中国考古材料出发,苏秉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把中华文明起源归结为裂变、撞击和熔合三种基本形式,这就是对中华文明形成模式的一种探索,而且似乎与恩格斯所言三种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妙。近些年,李伯谦撰写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中华文明演进的“三个阶段两种模式”,以红山、良渚为代表的神权国家模式和夏商周军权—王权国家模式。目前比较清晰的神权模式为良渚古国,王权模式有陶寺、二里头乃至商周王朝。
文明呈现的模式与文明最终形成的内在原因密切相关。关于文明的形成内因,国外学术界曾有过冲突论、融合论、宗教管理论、贸易论等各种各样的理论,还涉及人口增加、农业强化、交换贸易、战争、环境、资源、技术等众多因素。中华文明的形成显然复杂得多,众多因素几乎是兼而有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严文明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提出了“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模式,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同时又是一体的。
理论与思考源于实际材料。随着各个区域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看到中国各区域文明形成过程中社会形态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有“红山模式”和“良渚模式”,也有“陶寺模式”“石峁模式”等。从中华文明长期发展轨迹和最终结果来看,这些“多元文明”最终走向了“一体”。需要强调的是,“多元”与“一体”是一个多元演进并逐渐走向一体的过程。就中原地区而言,庙底沟文化时期是中国早期文化历史上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时期。龙山时代是第二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时期。龙山文化末期,周围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相继衰落或中断,其文明化的进程遭遇挫折,而中原地区的文明脱颖而出,至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中心的地位开始确立,二里头文明开始向周围地区广泛辐射,周围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方向,从原来以自己独立发展为主的轨道,改变为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共同发展,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开始初步形成,再经商周各地逐渐融入了以中原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之中。所以,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体”,这或许正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演进的最大特色。
总之,百年中国考古实践,尤其史前考古事实告诉我们,中华文明在宏观上是持续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文明。在其起源、形成与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渐展现海纳百川、务实创新、多元一体等特质与风格,这些都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渊源和宝贵财富。对于延绵5000年的中华文明而言,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创新、发展是高度文化自信的“基因”。无论是炎黄传说,还是尧、舜、禹、夏、商、周之早期中国,文化基因从未中断,祖先认同绵延至今,就此而言,“古”是今人的“史”,“祖”是今人的“先”。
作者:高江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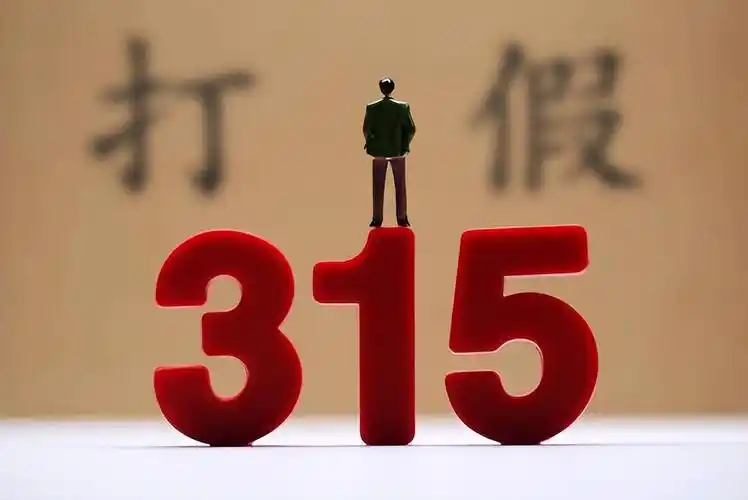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微信或手机浏览器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