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后装枪杀人已嫌不够快了,于是便用多管炮去成百成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进行的,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立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却雄辩的证人,说明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
这是巴黎公社二十周年之际,恩格斯写在《〈法兰西内战〉导言》的怒语。
3月18日,巴黎公社一百五十二周年。
距血染拉雪兹神父公墓,已逾一个半世纪。
这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变幻,从阶级专政演迁和国际共运潮变的视角,大致可分为前四十年、中间七十年和后四十二年。
前四十年即1871-1911年,全球范围内资产阶级逐步建立垄断统治秩序,而在其过程中,渐趋被吸纳进剥削体系的无产阶级同样在积攒着怒火并积蓄着革命力量;
中间的七十年即1911-1981年,则是人类国际共运史上不折不扣的革命高潮。其中以分别带领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列宁同志、毛泽东同志,为20世纪波澜壮阔的人类共运长史永远的领袖导师;
而后四十二年,共运陷入空前低潮,帝国主义垄断集团的蓝色消费文化在全球各地域以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取代了红色生产文化。
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的苏联被内部的修正主义势力和外部的帝国主义力量合力抹去,右翼势力蚕食了欧洲和拉美,非洲大陆则在全球化体系里重新陷入落后与弱势。
至今天,绝对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全球政治版图已近完全消亡。
“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还有多少人记得这句话?
这是毛主席在20世纪中叶重读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给出的深远评价(后来还由力群同志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
毛主席同时还针对包括邓力群、田家英等的讨论给出补充批注: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你们)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启幕之前曾随主席重登井冈山的王卓超,有过极为深刻的感悟:
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
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
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
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
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
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
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1965年的春夏之交,毛主席时隔三十八年重上井冈山当然不是单纯的怀旧革命,而是在追求继续革命。
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行动,绝非踏青赏景一般的闲情雅致。
当时间来到60年代中期,主席更加不再迷信党内,愈发转而发动他最信任的孩子们,即阶级斗争的「革命接班人」。
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同胡志明谈话时曾忧心吐露:
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他曾还尖锐地指出:
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就在那一年多前,1965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转批陈正人给一波同志“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信,主席做了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的老战士,1964年10月上旬时,时任八机部部长的他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研究。
当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纪大,要给他开招待所。而他拒绝了,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同吃同住。
陈正人在信中感叹道:
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与群众生活的距离如果不缩小,群众必然是会离开我们的!
主席的批示则如下: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做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主席那几年时常与秘书、警卫员等谈起,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而是做起了“老爷”……
回望1871年的公社运动,以及以其作为起始性坐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唤醒了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与阶级认同。
对巴黎公社的工人阶级政权性质,马克思当时敏锐地作出过揭示: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在此之前,历史上的国家政权历来是少数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专政的工具,因而不管怎样改朝换代,都会维护、强化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
在一阵阵从巴黎市中心传开的鼓噪声中,纺织工、泥瓦匠、烧煤师、医师、记者、教员、牧人,所有人都被一股力量从社会的边缘地带拉拽到城市的舞台中心。
在当时巴黎一百八十多万市民中,有一半以上均为工人和工人家属。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是12-13小时,煤矿工人长达15-16小时,女工、童工境遇则更惨,阶级矛盾已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因为,当超过1/3为体力劳工的公社市民们走到城市政权的核心位置时,发现这里早已为他们摆好了话筒、纸笔、旗帜、粮食、枪炮,以及等待他们签字的解放条约,这种阶级团结的鼓动是难以想象的。
如恩格斯所言:
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突出而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
决议规定了武装人民自卫部队取代反动的资产阶级常备军,规定所有官员均可被罢免,规定取消资产阶级当政时的特权待遇和高薪福利,规定宗教势力远离各大学校教育,规定提高教师/医生/工人的薪酬。
权力,不再是被工人们远远地看着、看着从一群人(封建贵族)手里转移到另一群人(资产阶级/买办/普鲁士侵略者)手里的遥不可及之物,而是可以实打实被夺取和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革命成果。
权力,第一次成为了工人阶级的工具,而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主人。
权力,第一次属于所有人,属于全体巴黎人。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说过一句话:
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
作为执政组织,当你掌握权力仅意味着要承担起保障公众的利益和一切满足,当人民所要求你承担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会不会不足——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
相反,如果权力意味着能够给个人及个人背后生成的「门阀」带来好处而社会责任处于次要地位时,那么其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
列宁曾辛辣批判美帝国主义:
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
然而自1954年开始,苏联却一步步走上了这条美式的道路。
如毛主席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毛主席的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阶级实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以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幌子为政治掩饰,对苏联人民实行反动专政;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辞下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和所有苏联卫星国家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1962年8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做过一个补充讲话:
我想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谈一谈。第一,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
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也就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了,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的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了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
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对于巴黎公社伟大斗争的总结,恩格斯精准颂扬过马克思的天才:
其天才就在于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他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
一如列宁所言: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是整个资本主义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必然伴侣。暴力将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时期,是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国内战争、二者相互交织着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各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的解放战争)的整个时代。
约半个世纪后,循着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旗帜,面临着如梯也尔般无能、向敌媾和的北洋政府,面临着如巴黎工人般需要被解放思想、挣脱枷锁、抛弃幻想的中国工人阶级,面临着如法兰西二帝/三共般亡国之危的中国(列强结束世界大战卷土重来)——中国人迎来了1919,而1919造就了1921,1921奠定了1949。
当然,也如巴黎公社遭遇初试战火的失败,中国的革命同样在1927年春天经历了一场不亚于法兰西白色恐怖的血腥屠杀。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教训时深切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巴黎公社存在的七十二天,很大程度上是武装起义、武装斗争、武装自卫的七十二天,是战斗硝烟弥漫的七十二天。最使资产阶级政权恐惧丧胆的,正是巴黎工人阶级拥有手握枪杆子的人民武装——而巴黎公社的一个重大错误,恰恰是对敌对势力表现软弱和仁慈。
恩格斯当年就有痛惜:
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列宁同样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中指明:
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旧政权并存的条件下,在反对旧政权的斗争中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握有武器和政权机关的暴徒,就不能把人民从暴徒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中国的幸运正是在于,我们在拥护一个勾勒出中国道路的人民领袖的过程中,革命队伍始终不仅善于团结工人,也会拥抱农民;纵使追求城市,但率先解放农村与农民阶级;既能紧握共产纲领,更能明晰“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
相比于巴黎公社自卫队在法兰西国家银行面前的唯唯诺诺、犹豫不决,毛主席的队伍果断掀起土地革命、变更了农民与脚下这片土地的生产关系;
相比于巴黎公社自卫队(受布朗基派的干扰)未能完全信任群众战争的力量,毛主席的队伍果断发动最广大的工农阶级、要求农民和工人必须是红军的主力军;
相比于巴黎公社自卫队(受蒲鲁东派的干扰)对凡尔赛国防军的放逐,毛主席的队伍果断喊出“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最后一道跨江战令。
所以,巴黎公社成为了20世纪初革命者的先驱,但毛主席则在20世纪中下叶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崛起的意识形态图腾,从非洲大陆席卷欧洲腹地,从拉丁美洲刮进北美心脏。
巴黎公社是永垂不朽的,其丰碑价值在于它以一种磅礴的悲剧力量为世界被压迫阶级提供了坚定的勇气,也给予了后世端坐于全球各处的剥削集团以沉重的历史威慑。
约百年之后,1973年10月16日的人民日报刊出文章《永远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提出:
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这句话恰是引述于前文提及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
《法兰西内战》二十年后的1891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又作了进一步阐发,强调指出了两项规定:
一、取消资产阶级的等级授职制和官吏的一切特权,所有公职人员均由选举产生,受人民群众监督,工作不称职时可以随时撤换;
二、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只付给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
而在《人民日报》刊文的当年年底,就有一位工农兵学员在其《退学申请报告》中联系马克思有关“巴黎公社取消国家官吏的一切特权使社会公职不再是官吏私有物”的论述,对党内干部子弟的特权提出公开批评,并得到了广泛支持。
其时,已濒晚年的毛主席亦有悲叹:
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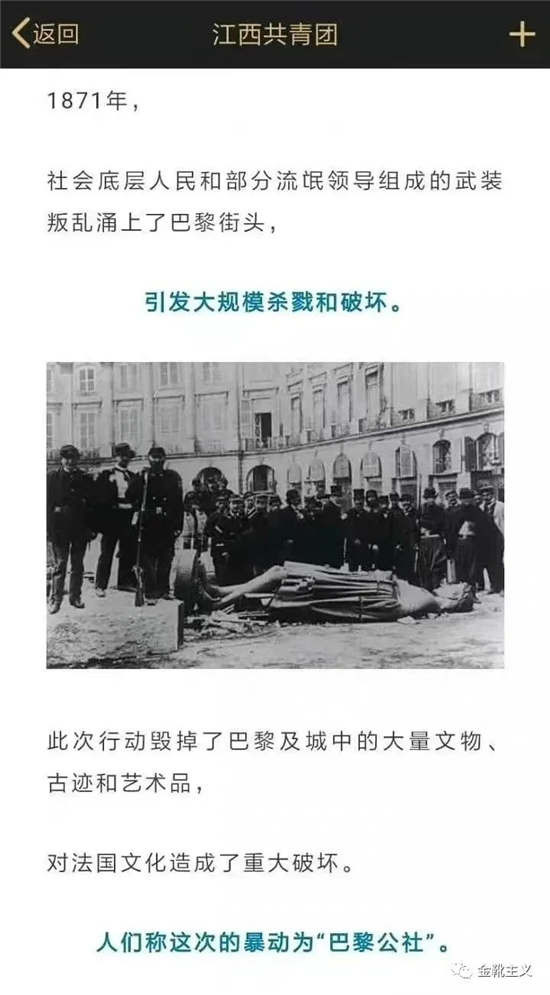
某地共青团泼污巴黎公社。鄙视巴黎公社的侧面,是潜移默化中形成的维稳主义秩序与精英主义倾向。
巴黎公社失败了,但它不应该被忘记或抹黑。
这场光辉的运动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并为这种思路所蕴藏的价值以鲜血和歌声浇灌出了果实。
滚滚热血,沸腾了无数后来者在沉重枷锁面前的热忱。
《国际歌》在一定程度上描述的就是巴黎市内最后时刻的战斗场景:皇帝和社会上层都已投降外国,“神仙皇帝”都已背叛,市民们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而自己也明知“这是最后的斗争”,最后除了牺牲几乎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但却仍然别无选择,为了自由和解放只能战斗到底……
公社检察长里果被捕后,在押往法庭的路上,押解他的匪徒逼迫他呼喊“打倒公社”,他却高呼“公社万岁!打倒杀人犯!”最后,他被打裂了头颅,壮烈牺牲。
公社副检察长费雷在敌人法庭上,义正辞严地揭露敌人的滔天罪行:“你们要我的头,尽可拿去!”临刑前,他鼓励战友说:“咱们都应该相信,社会主义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令人感到必要!”
公社女英雄路易斯·米歇尔在法庭上豪言宣布:“我的身心都属于社会革命!我们所有这些1871年的人们无比热烈的迎接死亡,视死如归!”
1871年5月25日,巴黎公社委员、自卫军最后一任指挥官路易斯·查尔斯·德勒克吕兹在巷战中阵亡。两天后的下午,自卫军最后的炮兵阵地布特肖蒙高地被法国外籍兵团第一团攻占。傍晚,由两百名自卫军守卫的据点拉雪兹公墓被凡尔赛军攻占,当时还活着的一百五十名自卫军伤员在公墓外墙边被集体屠杀,巴黎公社的抵抗宣告终结。
而5月21日至5月28日这一周,也被称为了法国历史上的“流血星期”(semaine sanglante)。
2016年,法国国民议会依据法国《宪法》第34-1条款通过决议:
为所有遭镇压的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平反。
毋庸讳言,这场运动的精神内核和运动者勇敢呐喊出的政治梦想,永远刻在那面神圣的公社墙上,激励着全世界无产者为了彼岸的胜利而奋斗。
不论现在的你是在流水工厂中流汗,还是在街头马路上奔波,或是在教室里苦读、在田野里耕作、在格子间里码字——请记住马克思的话: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1926年,刚及而立的毛主席高亢演讲:
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
巴黎的斑斑血墙,涅瓦河畔和风诉史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北京披尘沐月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都还矗立在那里,披尽风雨,岿然不动。
资产阶级,永远不可借尸还魂。
巴黎公社万岁!人民万岁!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