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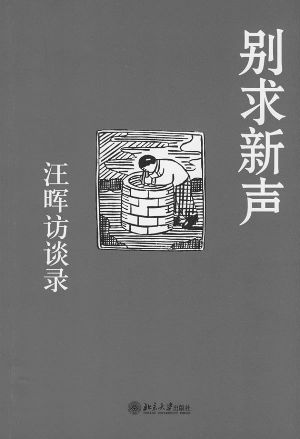

汪晖,自《反抗绝望》出版以来一直是学术界一个风向标式的人物。尤其是1996年,汪晖受聘成为《读书》执行主编后,更成为知识界颇具争议性的焦点人物。今年,《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汪晖在近十年来发表在各重要媒体上的访谈记录,领域涉及当下思想争论等,可看成是对世纪之交诸多嬗变问题的个人记录与回顾。日前,汪晖接受本报专访,就其个人的思想转型和学术争论谈及他的看法。
谈个人学术 学术转型,是偶然也是必然
【编辑提示】 汪晖的学术始于文学评论,以鲁迅研究开始,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兴趣是在和同学之间的讨论中渐渐形成的。
新京报:您的文章所提供的信息量很大,提出的问题也很复杂。无论是之前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还是新近出版的《别求新声》都是这样,您是如何阅读与写作的?
汪晖:研究工作大致是一样的,先阅读基本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而后随着对问题的深入再去阅读新的资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写作的时间很长,涉及的问题和方面较多,经历反复修改。只是不管遇到什么状态,都要求自己持续不断地阅读和思考,也在寻找不同的对话对象。
新京报:您最初的学术方向是文学评论,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对鲁迅很多问题的讨论,至今仍被认为是典范作品。但上世纪90年代后转向了社会政治经济批判和历史研究,当下这本《别求新声》,也都集中在此,这和您的学术背景相去甚远。
汪晖:是的,博士毕业之后,几乎没有再做鲁迅研究。博士论文写鲁迅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他所处时代的思想和社会变迁。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是研究鲁迅难以绕过的人物,后来也的确成为我自己的研究对象了。除了中国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对鲁迅有很大影响的西方的和俄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如德国的尼采,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我在中国社科院读博士学位时,我们这个博士班20多人,居住在一层楼内,分属不同专业。哲学、宗教、文学、历史、社会学等,其中一半人的专业与经济学有关。同学之间讨论很多,互相学习。我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兴趣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氛围中被激发的。
谈社会思潮 思考中国,要理论也要辩论
【编辑提示】 汪晖认为,中国思潮的变迁到了80年代中期就开始改变了,理论性辩论变得越来越弱了。
新京报:您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从各种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入手思考20世纪,你有什么心得?
汪晖:每个时代都有社会思潮,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时代有着最为丰富和深刻的表现。从“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讨论、东西文明的辩论、社会主义论战和科学玄学论战,到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随之展开的历史研究和理论讨论,几乎每一次理论辩论都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反响,而这些反响也会进一步促进新的理论讨论。这个潮流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新京报: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
汪晖: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情况开始改变,这之后理论性辩论不再那么强了。大概到80年代中后期以后,社会主义历史发生了重大改变,在那个很大的社会范畴内的理论辩论和政治、社会变迁的关系似乎发生了变化。我并不是说理论讨论消失了,事实上,80年代中期之后,对西方理论的大规模译介和相关的思潮是很多人注意的现象,但和先前的理论争论相比,理论性要弱很多,思想变迁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异。
新京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异呢?
汪晖:20世纪的理论辩论是在特定的政治进程中展开的,在经历了深刻转型的今天,思想讨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政党和国家的框架之下。要理解思想讨论的变迁,不能忽略社会转型中实际上已经发生的政治转型。九十年代的思想辩论在这个意义上也完全不同于前面提及的那些辩论。但这并不等同于说意识形态强度降低了。意识形态有其隐蔽性,如果意识形态一望而知就是“虚假的意识”,那就构不成真正的意识形态。
谈思潮终结 两次危机促使思潮转变
【编辑提示】 汪晖觉得,从1997年的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上世纪90年代思潮到了2008年已经终结。
新京报:您也介入了90年代之后意识形态的论战。《中国当代思想界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7年在《天涯》发表,曾经引起了很大的讨论与争论,您现在回头看还有什么想法。
汪晖:《中国当代思想界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这篇文章,我分析了中国思想界的所有派别,诸如启蒙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后现代等,主要是说明这些貌似非常不同、经常相互对立的思想所共享的一些前提,尤其是它们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关联。我认为这种关联使得当代中国思想失去了思考当代问题的能力。我也特别指出当代中国已经处于全球化进程内部,需要重新调整视角才能把握现实。这篇文章对于全球化和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态度(不能等同于否定性态度),撕开了一个重新思考当代问题的缺口,我预料到会引起反弹,却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响。
新京报:《现代性问题》受到大规模的讨论与批评,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有关系吧?
汪晖: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化刚刚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热门话题,金融危机就到来了。我和黄平在编辑《读书》杂志时,努力发掘有关的讨论,但国内学术界那时似乎有些晕头转向,我们不得不找国外和香港的一些学者撰写文章,引发讨论。至少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没有给出很有力的分析。该文引发讨论,也许与此有关吧。
金融危机刚刚过去,1999年爆发了科索沃战争,2001年“9·11”事件爆发,随即引发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上世纪90年代思潮不得不发生一个大转变。因此,我觉得2008年是上世纪90年代思潮终结的一年。
新京报:您怎么看媒体在这场持续数十年争论中的作用?
汪晖:从总体上看,媒体是主流的。但报纸的思想论坛往往为少数作者把持,他们很快就将诸多社会问题归入到他们的框架之内进行讨论,这也使得报纸的“思想”与“事件”脱节。
谈思想争论 争论促进公共政策的调整
【编辑提示】 汪晖认为,如果没有这样持续的争论,公共政策的制定就有可能被某些利益关系所主导。
新京报:这场思想辩论持续了十年,知识界做出了哪些贡献?
汪晖: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大辩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但在这场讨论中提出了真正问题的人是那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我说是“批判性的”,因为他们不居于主流的地位,提出的是“另类的问题”。从全球化到帝国主义战争,从三农危机、医疗体制改革的危机到生态危机及对发展主义的批评,这些问题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是哪些知识分子提出了这些问题呢?在回顾过去十多年的思想讨论时,这个问题值得问一问。
新京报:那么,哪些是争论留下的遗憾?
汪晖: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国企改制问题在2005年前后成为热议的话题,但此时改制的大格局已经完成。其实,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崔之元就以俄国的自发私有化为例,分析了私有化过程在俄国已经造成、在中国可能造成的问题。但当时知识界主流崇拜的正是俄国模式(稍后改为东欧模式,比如捷克或波兰模式),根本不愿意倾听这样的分析。另一个例子是对生态危机的重视和对发展主义的批评。我记得那时有位我很尊敬的先生说,《读书》没有必要发表这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但短短十年,生态危机及相关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为大家熟知。
新京报:知识界单向度的舆论加重了改革的曲折?
汪晖:过去十多年中,围绕三农、医疗体制、孙志刚案件、生态危机、国有企业改革等等产生了一系列讨论,改变了公共舆论的话题。从一个较长时段看,这类讨论促进了公共政策的调整。公共舆论与政策调整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意味着中国社会存在着民主的潜能和某些不稳定的机制。两年前,我离开《读书》时,三联书店的前任领导对我说,《读书》引发的争论太多,不是好事。这大概也是许多领导者的心态,就是担心争论。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争论,公共政策的制定就有可能被某些利益关系所主导。
新京报:你认为90年代知识界对全球化、市场化等乐观看法的根源是什么?
汪晖: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方面特别突出。第一个,这种盲目乐观遮蔽了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危机,第二个,将一切问题归结为“过去”,尤其是前三十年,以致中国在二十世纪的试验完全不能作为思考的源泉,也就不能解释中国在改革中取得的成就的历史基础。
二十世纪的历史中出现了许多悲剧,需要认真思考和分析,但简单地否定二十世纪这个历史进程,只能导致基本历史评价的混乱。在知识界的讨论中,那些为殖民主义历史辩护、为帝国主义战争张目等的论调,几乎全部与此有关。
谈金融危机 危机提供新的思考与选择
【编辑提示】 汪晖认为,金融危机也不都是不好的,如果能够激发更广泛的讨论,就有可能让我们从中得到更多的东西。
新京报:您对本次金融危机有何看法?
汪晖:全世界都在讨论金融危机,我的一些朋友对此有比我深入、全面得多的分析和观察。我不是合适的讨论者。金融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危机,也涉及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现在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救市问题、增长问题、出口问题、外汇储备问题、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问题等等方面,这些都很重要,但这场危机是否还会提供其他的可能性,是否会提供新的政治思考和方向性选择?
将危机简化成数据和市场问题,忽视危机的结构性特征,也意味着把市场的逻辑彻底地合法化。能源问题、生态危机、土地问题、劳动权利的受损、,教育投入不足及教育领域的不平等、由经济和社会不平等而引发的民族矛盾以及全球经济关系的变化等等,都意味着经济危机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危机不见得都是坏事。
比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农民工被迫返乡,土地作为农民的基本经济保障和社会福利支持的意义凸显出来了,土地私有化的主张在现实面前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了。如果金融危机能够激发更为广泛的讨论,而不只是一些经济专家的对策性讨论,就有可能让我们从危机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谈中国问题 动态理解中国的成就与困境
【编辑提示】 汪晖觉得,成就和失败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从动态的关系中理解中国的成就和困境。
新京报:你在争论中,一再反对盲目复制国外经验,强调从中国———世界联系的角度看问题。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汪晖: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和历史传统。要观察中国的变迁,需要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力量和历史传统的互动关系。在改革的前期,国家能够超越特殊的利益网络,有效地推进改革,但这个所谓中性化的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在社会主义历史中、一点也不中性化的历史中产生的。没有在这个历史地基上产生的国家以及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就没有改革的前提。在金融危机中,中国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但总的表现好于许多国家,除了一些应对措施的及时外,也由于在危机之前,中国已经开始了若干方面的调整。三农问题、医疗体制问题,以及金融体制方面的一些改革,都是在危机爆发前就开始了的。这些调整是现实的需求,也是争论的结果,或者说不同力量、不同历史传统博弈的结果。换句话说,成就和失败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从动态的关系中理解中国的成就和困境。
新京报:你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从唐宋一直做到现代,这是不是你努力在历史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资源?
汪晖: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东方主义》中批判了西方对东方的重构。在知识领域,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是非常多的。但萨义德也曾指出,如果非西方世界不能够产生新的知识,我们就总是在殖民主义知识的框架内观察世界和我们自身,也就没有进步。因此,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和其他知识领域的工作就不只是在既定框架下梳理和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还需要通过研究和对话,让有关中国的知识变成观察世界和中国社会的活的方法、活的文本。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可能摆脱旧的知识状态。但所谓有关中国的知识不是孤立的,不能限定在中国/西方的框架下;中国从来就在历史的变动之中,充满了不同的张力。我做得很有限,但探求的努力是连贯的。
90年代以来的思潮
1990-1992,检讨新启蒙运动和一轮学术杂志创办热。
1993年,第一波“国学热”以北大的《国学研究》集刊为代表。
1993-1995,人文精神大讨论,涉及《上海文学》、《读书》、《东方》、《十月》、《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持续3年之久。
1996,《中国可以说不》出版,标志着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
1997,现代性之争。汪晖在《天涯》发表《中国当代思想界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引发思想界关于现代性大讨论。
1998-1999,左右之争,崔之元、汪晖、甘阳、朱学勤、徐友渔都参与其中。
2000,长江读书奖事件。《汪晖自选集》获首届“长江读书奖”“专家著作奖”。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由此在学术界、文化界热烈展开。
2001,哈贝马斯访华风波。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应邀访华,哈贝马斯离开之后,历史学者雷颐发表文章称,在一次小型聚会上,哈贝马斯谈到“他们(汪晖、黄平)的观点有为极权、专制服务辩护的倾向”。汪晖在《读书》编者按回应称,雷颐撒谎,他向哈贝马斯当面询问,哈贝马斯称并无此事。
偶然照面中的汪晖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 2009-09-05 作者:张晓波
【记者手记】
星期六,早晨,10点。刚下过一阵雨,马路灰白相间点缀着雨水,清华北门,到了。联系数月,终于到了。
汪晖家中,摆设极其简单,而我关心的是藏书,但我只看见餐桌后面一个书柜。我拟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新书《别求新声》的,结果,我的第一个问题成了“汪老师,你家的书并没有我想象的多”,于是,这个访谈竟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注释开始了。
汪晖对我最生猛的冲击就是来自四大卷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读书有时候就是一场战斗,对于没有挑战性的论著,一个晚上就被轻松缴械了,甚至还来不及回想前晚的敌人是谁。《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固执的敌人,我从2004年到2005年,花了将近几个月的时间,却始终无法击倒这个望而生畏的庞然大物,至今仍是读书中的一场梦魇。
但汪晖当天的兴奋点,显然并不是解释如何制造《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他关心的是意识形态。整场谈话,贯穿始终的,都是关于意识形态的批评。我知道,这是他工作的另一部分,也是最锋利的部分。以批判形象出现的汪晖,往往是事端的制造者与被制造者。按汪晖自己的说法,被批评总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是越是经久不衰的批评,越是证明言论的生命力。
我本以为,汪晖应该是怒目的,但见面时的汪晖却是平静的。汪晖谈话的方式,一如他的论文,不紧不慢,条分缕析,即便是对于他参与的争论,也仿佛看待早已尘封多年的历史般平静。偶然,汪晖会蹦出一些激烈的词语,比如,“这是缺乏思考能力的表现”,但大多数时刻,汪晖一如磐石,稳健、妥当。我想,这是一个偶然照面中的汪晖,光与影,明暗交替,摇晃不定。
汪晖似乎喜静,夏日的中午,只微微打开窗户,这是照顾我,汪晖说,马路上有吵闹声。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