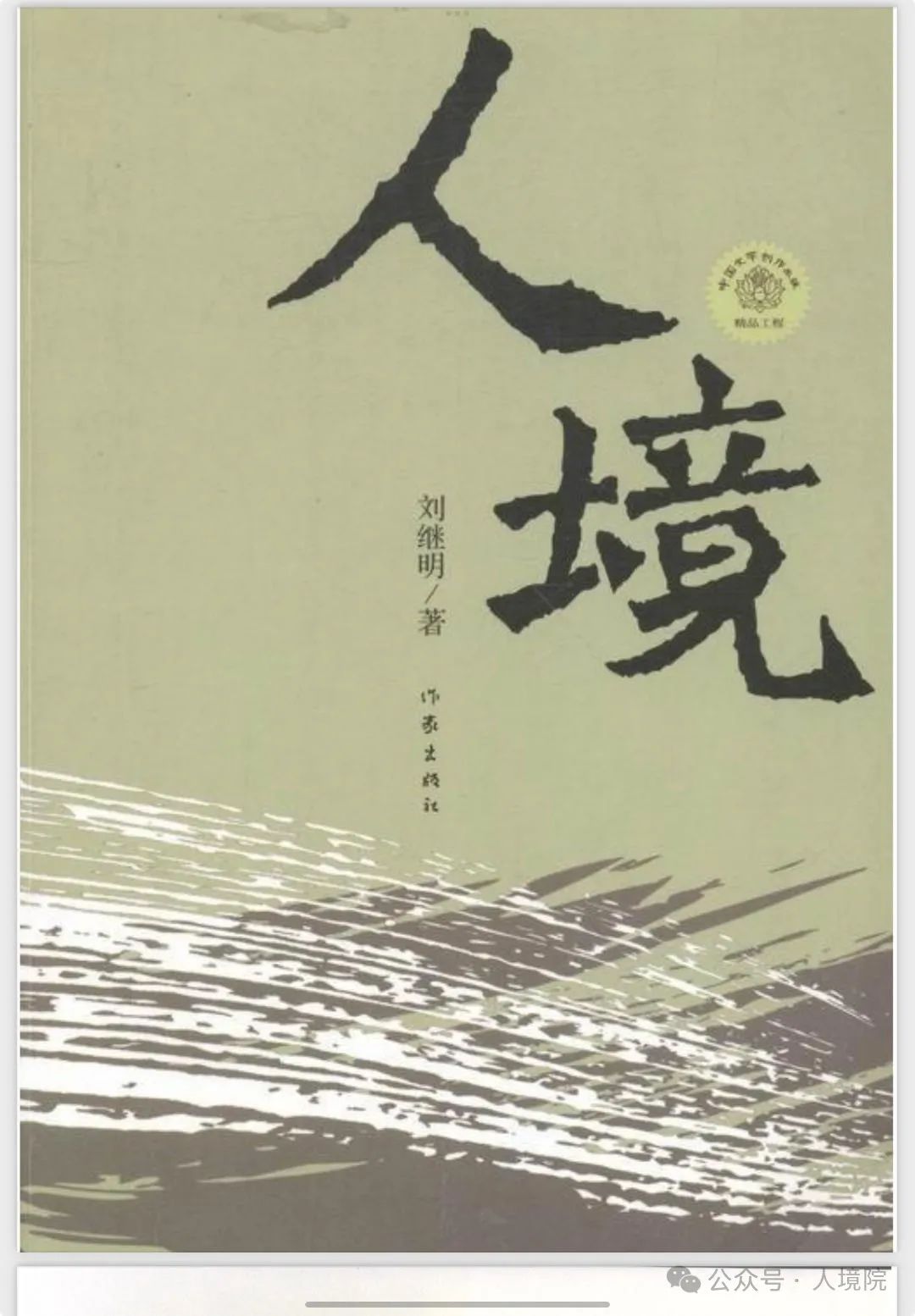
第三章
马垃脑子里纷乱如麻,仿佛置身在缥缈的梦境,
一时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这还是我记忆中的神皇洲吗?那个秋天的下午,当马垃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土地上时,忍不住这样想。
一切都令他如此陌生。千疮百孔、泥泞难行的道路;这儿一块、那儿一块,像补丁一样良莠不齐的庄稼,大片大片长满蒿草的撂荒的土地,臭气熏天、荒芜干涸的水渠和废弃颓败的水闸,新建的楼房和破败的土墙屋交相陪衬,显得极不协调;整个村子仿佛被刀剃过一样光秃秃的:村道边和房前屋后几乎看不到几棵树,或者即使有,也是又瘦又细,连一只鸟窝也承不住。实际上,村庄的天空也几乎看不到一只鸟儿。小时候,村子里可是遍地绿荫,长满了粗壮的桑树、柳树、椿树、杨树、苦楝树、泡桐树以及桃树和李树,这些树又高又大,春天绿树红叶,果实满枝,夏天给人们带来阴凉,冬天替人们抵御寒冷,还引来无数的鸟儿,成群结队地在房前屋后和林子里飞来飞去,不仅在大树上,就是庄户人家的屋檐下,也都筑满了大大小小的鸟窝……
村子里除了老人就是孩子,几乎看不到几个青壮年人,一眼望去,满目荒凉,仿佛电影中遭受过战争洗劫之后的场景。在村子里偶尔碰见几个人,但面对那一张张表情木然和呆滞的面孔,马垃却一个也不认不出来。也难怪,离家这么多年,差不多隔着整整一代人哪,可他们怎么用那种充满警惕和敌意的眼光瞅着自己呢?马垃越往前走越感到疑惑和不安,似乎他走错了路,到了一个他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马垃原以为,乡亲们一定像报纸上说的那样,早就过着小康日子了。可眼前的一切,同他在南方沿海地区见过的那些经济发达的农村,仿佛隔着两个相距遥远的时代。
在村口的闸坝上,几个妇女在一家小卖部门口的棚子下面围着桌子打麻将,小卖部简陋的货架上,除了食盐、酱油、牙膏、牙刷和廉价香烟之类的日常用品外,空荡荡的;水泥砌成的柜台上,放着几块豆腐和两条已经不新鲜了的猪肉,几只苍蝇在上面爬来爬去。一群孩子在旁边的空地上玩跳房子的游戏,看见马垃走近,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脸来打量他。马垃朝他们弯下腰去,想抚摸一下其中一个小男孩的脸,但他往后缩缩身子,一偏脑袋,机灵地躲闪开了。“你是谁家的娃儿?上学了吗?”马垃伸出去的手停在空中,问那个孩子。
“我不告诉你。你是谁?”那孩子睁着乌黑的眼睛,用脏兮兮的手背揩了揩鼻涕,很不客气地白了他一眼。
“呵,好厉害哟!”马垃直起身来,笑了笑,“你不认识我,可你爸爸没准认识我……”
“你骗人!”那孩子尖声道,“我爸爸才不认识你呢!”
“那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肯定认识他……”马垃认真地端详着那孩子,似乎想从他身上找到儿时某个伙伴的影子。
“我不告诉你。”那孩子警惕地瞅着他,“他到广东去啦,你莫想抓住他!”
这孩子怎么会认为我是要抓他的爸爸呢?马垃疑惑地想。这当儿,一位坐在桌子边打麻将,约莫30来岁的妇女扭过头,对那孩子呵斥了一句:“蝌蚪,你瞎嚼些么子,小心割你的舌头!”说罢,瞥了马垃一眼,用冷漠的口气问:“您是……要找人吧?”
马垃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觉得那个女人有些面熟,于是,努力在记忆中搜索着:“你是不是谷雨家的……茴香?”
那妇女停止了打牌,诧异地看着他,忽然眼睛一亮:“哎呀,你不是马……马老师么?您回、回来哒?”
总算有人认出他了。马垃心里感到些许宽慰。谷雨是他当年在河口镇中学的学生。
“谷雨不在家么?”马垃打量着茴香,试图从她脸上找到当年那个俊秀水灵的新媳妇的影子来,可眼前的这个女人面孔黄瘦粗糙,显得那么憔悴。
“他出去打工了,过年都没回家。”茴香瞟了刚才的那个孩子一眼,欲言又止。
马垃又问起村里几个儿时伙伴的近况,结果大部分都和谷雨一样,到广东打工去了。
“马老师,你难得回来一趟,到家去坐一会儿么。”茴香说。但她仍旧坐在麻将桌边,并没有真邀请的意思。
“不了,谢谢。大碗伯呢,还有东生,他们一家还好么?”马垃说,“我刚才从村子那边过来,见他家的房屋不在了,是不是做了新房子?”
茴香说:“你是说郭爹吧?他早就搬到堤上的哨棚去住了……”
马垃哦了一声:“他不跟东生住在一起么?”
“东生?你是说郭支书?他现在住到了镇上,郭爹不愿意跟他儿子去享福,有么子办法。”茴香一边熟练地码着麻将,一边说,“其实郭爹守哨棚也不错,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不说,每个月还有工资领,要不是他儿子是村支书,这么好的差事能到他派身上?”
马垃听出茴香话里有话,想问什么,但一见她闪烁其词的表情,只好沉默下来。
天近傍晚,暮霭同农舍上空的炊烟深深浅浅地交织到一起,起初像一块块布片似的挂在树枝间,然后,便像大雾一样渐渐汇聚到一起,悄悄弥散开来,四周的景物变得影影绰绰、迷迷蒙蒙。空气中散发着谁家的饭熟了的锅巴香味,直往马垃的鼻孔里钻,他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肠胃好一阵激动。哦,好多年没有闻到这种用铁锅和柴草煮饭的锅巴香味了。小时候,每到傍晚,他们这些在村外洲子上的野地玩得忘了形的孩子们,一听见大人叫唤吃饭的吆喝声,就像晚归的牛群争先恐后地跑回家,捧起堆得冒了尖的大米饭狼吞虎咽,虽然饭桌上也许只有两碗青菜罗卜,却比满桌的山珍海味吃得还香。多么遥远的童年啊……马垃脑子里浮现出娘领着哥哥和他从遥远的洞庭湖流落到神皇洲时的情景。那时的神皇洲还是一片苍苍莽莽的洲子,洲子上水凼密布,长满了芦苇、灌木荆棘和数不清的野花野草,是野兔等鸟兽栖息和藏身的理想之地。听人说,更早以前,洲子上人烟稀少,曾经还有过狼和野猪,后来,一场浩浩荡荡、规模盛大的平整土地运动,把这片荒芜空旷的芦苇荒洲开发成了平坦无垠的庄稼地。就是从那时候起,一些外地人陆陆续续迁移到这儿,在洲子上筑堤开荒、繁衍生息……
村庄离江堤只有一里多路,穿过一条沼泽似的烂泥路就到了。
前面不远的堤坡上,有一幢宽敞高大的砖瓦房,一溜五大间,远远看上去很有些气派,但走近后就发现,由于风吹雨淋和烟熏火烤,房子的墙壁和屋顶黢黑斑驳,显得颓败不堪,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它刮倒。面朝江提的墙上,一行字迹漫漶褪色、缺胳膊少腿的防汛标语,依稀可辨:“严防死守、人在堤在!”
像这样的防汛“哨棚”,江堤上每隔一公里就有一座,由各村派人驻守,负责看管沿江的防浪林,汛期来临时,就成了上堤防汛的干部和民工的抗洪指挥部。小时候,马垃和小伙伴到防浪林里砍树枝回家当柴火,经常被哨棚看守人撵来撵去,如果不幸被抓住,就会被关在哨棚的某一间黑屋子,等着大人来领人。在马垃和小伙伴们心目中,这幢高大的砖瓦房是那么威严,令人望而生畏。
房子前面有一棵粗壮的泡桐树,婆娑的树枝延伸到屋顶上,枯黄的秋叶落满了屋顶,风一吹,落满一地。不远的坡地上有一块不大的菜地,上面种着辣椒和豆角之类的蔬菜,由于节令已过,大都已经枯萎下来,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干。
马垃站在哨棚面前,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门没有关严,生锈的铁褡子上别着一根树枝,透过很大的缝隙,屋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马垃正贴着门缝朝里面观望,身后忽然传来一声狗吠,他刚来得及转身,就看见一条浑身沾满草屑的矮脚狗向自己扑过来,他仓皇地后退一步,本能地用拎在手里的那只黑皮箱去挡,没想到那狗比人还机灵,绕开皮箱,迂回着从侧身再一次向他猛扑上来……
这当儿,有人低沉地断喝一声:“社员!”那狗就像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拽住了似的,重重地跌回到了地上。马垃转脸一看,一个满头霜花似的发茬,裤子绾到膝盖,赤脚上沾着泥巴的老人,胳膊下夹着一捆被雨淋湿了的枯树枝,从房子后面走了过来。
马垃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大碗伯。
大碗伯已经明显地老了,不仅头发胡子和眉毛全白了,腰佝偻着,整个人似乎比从前矮了一截,满脸的皱纹像桑树皮似的纵横交错、又深又密,走路时腿脚迟缓,显出了龙钟的老态。这与马垃记忆中那个说话声如洪钟、走路双脚生风的大碗伯,已经判若两人了。这会儿,他漠然地打量着马垃,口气硬梆梆地问:“你找……谁?”
马垃说:“大伯,我是垃子啊!”
垃子是马垃的小名。
“垃……子?你是垃子?”大碗伯胳膊下夹着的树枝哗啦一下掉落到了地上,他摸出钥匙,抖抖索索地去开门,“快进屋吧,垃子,瞧你身上,都快湿透了……”
马垃提起皮箱跟着走了进去。屋子里杂乱无章,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漆皮剥落殆尽的老式抽屉外,什么像样的东西也没有。石灰刷的墙壁早已剥落得千疮百孔,一张过了塑的神皇洲村防汛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倒还十分清晰。他在一串人名中看到了郭东生的名字。
大碗伯手忙脚乱地收拾着到处乱放着的杂物,“你还没吃饭吧?我这就做饭……”说着便去厨房准备饭菜。
大碗伯身子骨虽然远没有从前硬朗了,干起活来倒还利索,不一会儿,就洗好了刚从地里摘来的新鲜萝卜菜,还从墙上取下一条风干得像块化石的咸鱼,剁成几大块,然后便圪蹴到灶门口去生火。连日的阴雨使柴禾有些潮湿,大碗伯鼓着腮帮用吹火筒吹了好一阵子,火也没燃起来,灶膛口冒出一股股浓黑的烟雾,顷刻就灌满了整个屋子。马垃被呛得咳嗽不止、涕泪横流,差点儿窒息过去。那条叫“社员”的矮脚狗也受不住,汪汪地叫着逃到门外去了。
等灶火终于哔哔剥剥地燃烧起来后,烟雾才慢慢消散。马垃在一条跛脚的凳子上坐下来,瞧着大碗伯像个农家主妇那样在灶台边忙活,脑子里一阵恍惚。
近四十年前,不满三岁的马垃和哥哥马坷跟着娘刚到神皇洲时,无处落脚,多亏大碗伯将生产队的一间仓库腾出来,让他们一家三口总算有了个临时的栖身之所。很长一段时间,娘靠给村里人缝制衣服养活养活着她自己和两个儿子。娘的裁缝手艺在老家时就很有名气。老家在洞庭湖边,到处都是芦苇,每到春天,白色的芦花漫天飞舞,落在地上、屋顶和草丛中,白茫茫的,像下了一场鹅毛大雪。一望无际的洞庭湖绿汪汪的,春天开荷花,夏天结莲藕,一年四季总有捞不完的鱼虾。马垃的爹以捕鱼为生,凭借一艘小小的渔船不仅娶到了方圆十里既俊气又会裁缝手艺的姚家幺姑娘做堂客,还养活了一大家人。马垃是在哥哥马坷快上小学时出生的。就在那一年的夏天,洞庭湖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那年的八月中旬,村里进湖捕鱼的男人们还不见踪影。那段日子,娘每天都要带着马垃和哥哥马坷去村头的湖码头,看爹是不是回来了。一连半个月都是如此。直到后来,爹和村里好十几个渔民葬身湖水的噩耗传来……
爹死后,娘就带着马垃和哥哥外出逃荒,一边靠给人缝补衣服糊口,几经辗转,终于在神皇洲落住了脚。娘的裁缝手艺很快在神皇洲有了些名声。久而久之,人们开口闭口都把娘叫“姚裁缝”,反倒不知道她的真名了。每年冬天,忙了大半年的人们终于有了空闲,尤其当春节临近时,再拮据的人家也要想方设法去河口镇上扯几尺布回来,给大人和孩子添置几件像样的衣服。娘每天都有缝不完的衣服。娘缝衣服的行头很简单,一把尺子和一把剪刀,再加上一双巧手,娘成了神皇洲最忙的人,请她缝衣服的人家排成了长队。娘白天晚上都回不了家。哥哥马坷在神皇洲村小学读书,经常只有马垃一个人在家。那间临时借住的生产队仓库是老鼠们的天下,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它们都成群结队地在房上房下四处奔跑,发出的吱吱声让人头皮发麻、心惊肉跳。有时马垃睡着了,它们还会爬到这个孩子的头上,直到把他惊醒,吓得大哭。大碗伯的家离生产队仓库只有不到百米远的距离。有一天他从门口路过,听见独自一人在家的马垃哇哇大哭,便将他抱回家里。大碗伯的儿子东生比马垃只大半岁。两个孩子很快成了一对亲密的玩伴。到后来,马垃去大碗伯家玩儿成了家常便饭,如果娘回家太晚,哥哥马坷放学后来大碗伯家找弟弟,索性也跟他们在一起玩开了,这时,大碗伯便做了一大锅饭给他们吃。那股亲密劲儿,真像一家人,大碗伯坐在一边抽烟,一边看着孩子们大口大口地吃饭,咧开胡子拉茬的嘴巴笑呵呵的。那副慈祥的神情,使马垃不禁想起了死去的爹……
大碗伯的女人是误吃了有毒的蘑菇死的。每年春天,神皇洲江边的树林子里长满了雨伞状的蘑菇。那几年闹饥荒,村里人吃不饱肚子,便靠野菜和蘑菇充饥。那年四月,接连下了几天的大雨。江边林子里的蘑菇比往年长得更加旺盛。村里的大人小孩都争先恐后地跑到林子里摘蘑菇。大碗伯的女人把才回家的蘑菇洗的干干净净,还杀了一只过年都没舍得杀的鸡,炖了满满一砂锅,打算给一家人好好补补身子。那天,大碗伯去公社开会了,儿子东生前两天到外婆家玩儿去了,家里只有三岁的小女儿安安。那天雨下的好大。大碗伯的女人炖好蘑菇鸡汤,守在灶门口一直等到天黑,还不见大碗伯和东生回来。安安饿的哇哇直哭。大碗伯的女人只好盛出一碗蘑菇鸡汤跟女儿,自己也顺便喝了半碗汤。当大碗伯冒着雨从外婆家把儿子东生接回家时,看见的是口吐白沫躺在灶门口的女人和孩子……
从那以后,大碗伯一个人拉扯着儿子东生,既当爹又当娘,日子过得比一般人家艰难得多。
大碗伯从小父母双亡, 8岁就开始给大户人家扛长工,也许是长期忍饥挨饿,他的饭量比一般人都要大,每次吃饭总是用特大碗,“大碗”这个名字就是由此得来的。东家见他人小饭量大,总觉得自己有些吃亏,便想方设法让他多干活,完不成指定的活路,就罚他饿肚子,说是“干多少活吃多少饭”,所以经常只能吃个半饱,偷偷地啃萝卜充饥。大碗伯家吃饭用的碗比一般人家的都要大。他饭量大,力气也大,二百多斤重的石磙拦腰一抱,绕生产队的禾场走一圈,脸不变色气不喘,人人见了直伸舌头,没有谁不服气的。正因为这个,大碗伯在神皇洲颇有威望,农业合作化那阵子,当过初级社的社长,人民公社以后,又当过好些年的生产队长。在马垃的记忆中,大碗伯走起路来总是那么快,一般人小跑着才跟得上,他一年上头除了冬天似乎都打着沾满泥巴的赤脚,肩上扛着一把铁锹,在神皇洲的田间地头和沟沟垴垴上转来转去,扯着洪亮的嗓门指派社员们做活路,看见谁偷懒,便沉下脸毫不客气地训斥一通,从早忙到晚,也不知道他身上哪儿来的这么多精力。后来,马垃的哥哥马坷当上生产队长以后,大碗伯才“退居二线”,当起了神皇洲大队的贫协主席……
没过多久,一顿简单的饭菜就做好了,天也完全黑下来了。屋子里散发出一缕咸鱼蒸熟后的香味儿,闻起来格外诱人食欲。大碗伯点燃了搁在灶台上的煤油灯,又从床底下摸摸索索地找出一瓶本地酒厂生产的高粱酒,对着暗淡的油灯光晃了两下,笑眯眯地瞅着马垃道:“这瓶酒都搁了大半年了,我一直不舍得喝,垃子,今儿咱爷俩喝了它……”
马垃多年没有在这样的环境吃过饭了,一时还有点不习惯,但他见大碗伯的兴致挺好,就拿过酒瓶子说:“大伯,我也好长时间没沾过酒了,今天就陪你喝两杯吧。”
马垃往碗里倒酒时,大碗伯忽然咕哝了一句:“‘社员’呢?它又野到哪儿去啦?”说着,转身走到门口,把手卷成话筒状,对着漆黑一片的野外吆喝起来:“‘社员’,回来吃饭啊!社~员~~”吆喝声传得很远很远,响起一阵一阵的回音。那副熟悉的口气,使马垃心里不由一动。小时候,他和东生一起在洲子上玩得忘了回家吃饭,大碗伯也是这么吆喝的;不同的是,现在大碗伯的嗓门像一口生锈了的铜钟,比从前喑哑多了……
大碗伯吆喝了好几遍,“社员”才披着一头雾水回到屋子。它一进门就看见了搁在灶台上的那碗咸鱼,伸出爪子正要去抓,大碗伯一下子将它拔拉开,顺手从碗里拿了一块,扔到“社员”的脚下,像对小孩那样虎着脸呵斥道:“一边去!没见来客了么?”
从门缝里灌进来的夜风,把煤油灯吹得晃晃悠悠、扑朔迷离,昏黄的灯光将大碗伯和马垃的身影投射到粗糙的墙壁上,一大一小,飘忽不定,仿佛他曾经历过的那些难以捉摸的岁月。马垃恍然又回到了小时候,娘和哥哥死后,作为孤儿的他在大碗伯家度过的那几年,他和东生合挤一张床、共吃一锅饭,大碗伯一天到晚在生产队忙活,顾不上管他们,东生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孩子王,经常对马垃指手划脚,马垃每次挨东生欺负后,便哭哭啼啼地向他大碗伯告状,马垃为此不止一次地和东生打过架;一旦打不过马垃,东生便以主人的身份威胁要把他赶出去。有一次马垃真的赌气出走了,在洲子上躲了整整一夜没回去,大碗伯知道后,用扫帚条把东生的屁股抽得血迹斑斑,以至后来他们俩好长一段时间都没说话……
在马垃的记忆中,大碗伯的酒量像他的饭量一样大,村里没几个人能喝过他。但看得出,他现在的酒量已大不如从前,没喝多少,就有些上脸了。马垃劝他少喝一点儿,可大碗伯抓住酒瓶子,嘟嘟噜噜地说:“你大伯半年多没沾过酒了,垃子,今儿是你回来我高兴啊!这么多年只听说你在外面干着大事业,大伯替你骄傲哪。要是你娘和你哥还活着……垃子,大伯没你娘有福气呀,再怎么她有你这么个有出息的儿子,我呢?唉,也不晓得前世造了么子孽……”马垃本来想问大碗伯怎么不跟东生一起住?但一瞅大碗伯的神情,就把话咽了回去。
大碗伯仰起脖子又喝了一口酒,用手背抹了下枯瘦的下巴,说:“垃子,前几年听村里人说你出了么子事,给抓进牢去了,我横竖不肯相信,把那个嚼舌头的人臭骂了一通,可还是有点不踏实……”
马垃怔怔地望着大碗伯,低沉地说:“大伯,这是真的。”
“管他(蒸)真的还是煮的,你现在不是好好的么?”大碗伯一愣,但很快岔开了话题,“垃子,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总该多待几天吧?”
“我是要多待几天……”马垃含糊地说。他心里其实还有另一句话:我想留在神皇洲,再也不走了。可他注视着大碗伯那张皱纹密布的脸,喉咙哽了一下,没说出口来。
外面起风了,刮得屋顶上的枯枝败叶飒飒作响,滔滔江水像奔逃的野兽吼吼直叫。也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马垃脑子里纷乱如麻,仿佛置身在缥缈的梦境,一时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