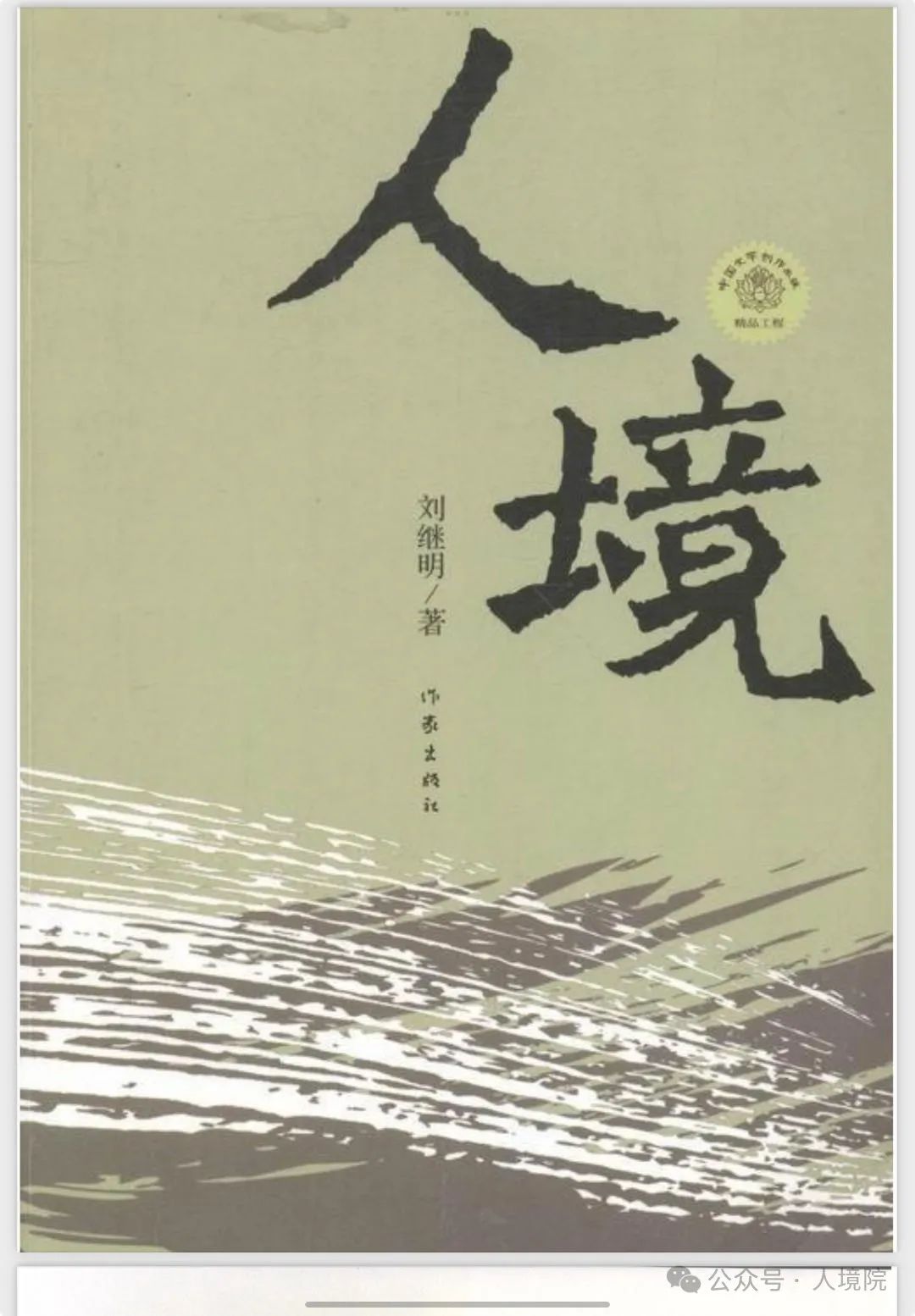
第九章
如果说他在青年时代喜欢保尔,进入中年后,他就更喜欢列文了。
那场漫长的秋雨过后不久,平原上又连续刮了几天干燥的西北风,气温也骤然下降了好几度。神皇洲村头路边的树木和庄稼地里尚未摘完的棉花,枯枝败叶纷纷落地,只剩下了一根根光杆儿,看上去仿佛脱掉了身上的衣服那样,一夜间变得光秃秃、赤条条的了。
霜降过后,天气就一天比一天冷起来。冬天像个性急的汉子,不等人们把庄稼收割干净,就迫不及待地来临了。
这天早上,当马垃像往常那样带着“社员”在江边荒滩上溜达时,一个满头白发、身体有点佝偻、下巴有两撮胡须的老头,肩挑一副拾粪的箢箕,牵着一头牯牛,慢悠悠地翻过了堤坡。
两个人在防浪林边上相遇了,还没有说话,“社员”已经冲那头牯牛汪汪地吠叫起来,往前一窜一窜的,不停地作出进攻的架势,牯牛高大壮实的身体岿然不动地立在那儿,两只铜铃样的眼睛冷冷地睥睨着虚张声势的“社员”,显得有些不屑一顾。“社员”似乎被牯牛的派头激怒了,停止吠叫,悄悄踅了几步,绕到牯牛屁股后头,试图去咬它的尾巴,但牯牛一眼识破了“社员”的阴谋,掉转屁股,横起两只往上翘起的牛角,虎视眈眈地盯着”社员”,潮湿的鼻孔呼呼地往外喷出一股股雾状的气体,仿佛在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社员”见状,发怵地往后缩了缩身子,颇识时务地夹起尾巴,回到了马垃身边。
马垃认出了那个老头,微笑地招呼道:“广富哥,你这头牯牛养得可真壮实咧!”
那个人也嘿嘿笑了笑,却没有说话,松开牛绳,让牯牛去吃草,自己放下箢箕,在林子边的一棵树蔸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掏出一支向马垃示意了一下,见对方摆摆手,便自己叼到嘴巴上,用打火机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眯缝起眼睛,望着沉寂空旷的荒滩,像在沉思着什么。
赵广富快六十岁了。在马垃的印象中,当赵广富还是个小伙子时,头发就花白了。据说赵广富从小很聪明,上小学时每年都在班上考第一,可由于他家成份不好,念完小学就没升中学,回生产队种田了。赵广富劳动积极,人又本分老实,再加上他脑壳灵敏,算盘打得出奇的好,所以他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家庭成分又不好,却当上了四队的会计。他跟过两任生产队长,先是是大碗伯,后来是马垃的哥哥马坷。生产队长走到哪儿,胳膊下夹着算盘的赵广富就跟到哪儿,像个影子似的,人称“赵算盘”。每年秋后生产队分红时,赵算盘总是稳稳地坐在队屋靠窗户的一张办公桌后,面对着一摞摞工分本,手里的算盘珠子被他拔拉得像炒豆一样,让马垃心里羡慕不已,觉得长大后要是能像赵算盘那样当一名生产队的会计该多好……
现在,马垃打量着这个前生产队的会计,觉得他比以前老了不少,脸上像树皮一样皱巴巴的,布满了横七竖八的皱纹,乍一看上去,跟他那个死去多年的富农父亲几乎一模一样,变成一个地道的老农了。
“嗯,马垃、垃子,企业家么!我早听说你回来了,”赵广富瞄了他一眼,喉咙里含糊不清地咕噜了一下,“你是干过大事的人呢……你回神皇洲究竟想干什么呢?”
赵永福的话听起来像是在质问。马垃不禁笑了起来。“我的家在这儿,我不回来能去哪儿呢?”
赵永福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你的家可不在这儿。别以为我不晓得,你们全家都是外来人!”
马垃听到这话,脸上的笑容顷刻消失了,他抿着嘴巴,严肃地说:“广富哥,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娘,还有我哥,他们都长眠在神皇洲的土地上了。你却说我的家不在这儿!”
赵算盘见马垃有点儿生气了,便堆起笑脸,改口道:“对对,瞧我这脑筋,你哥还当过我的领导呢。老实说,我这辈子除了你哥,还真没服气别的人……说到底,你和你哥一样,都不是等闲之辈哪!”
马垃缓和了一下口气:“你过奖了,广富哥,要论种田,我还得向你学呢。”
“莫讲面子话喽!”赵算盘鼻子里哼了一声,“我听东生说,你想回神皇洲……种地?”
马垃老老实实承认道:“是有这么个想法。”
赵广富尖下巴上的胡须跳了跳,说:“分田单干这么多年了,村里可没有多余的地等着你来种吧!”
马垃呵呵一笑,伸出手臂在面前画了一条大大的弧线,“没关系,把外滩开垦出来够我种的了。”
“你真的想开荒么?”赵广富半信半疑地说,“只怕不等你种上庄稼,一场大水就给淹了。”
“我就不会种些不怕水淹的作物吗?”马垃顺口道,“再说,神皇洲还有不少撂荒的土地嘛。”
赵广富听了,神色警惕地盯着马垃,足足有一分钟之久,忽然咕哝道:“不愧是当过企业家的,你野心可真大咧!”
赵广富的话,让马垃有些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想解释两句什么,但对方已经抽完了一支烟,把烟屁股扔到地上,挑起拾粪的箢箕,用钉耙打了一下正在吃草的牯牛屁股,牵着牛向江边走了。
马垃望着赵广富的背影,愣了好一会儿。
在江边转悠了一会儿,马垃回到哨棚,见大碗伯正在剁猪菜。他养的猪快一百斤了,从来不用饲料,全是从江边外滩野地上剜来的猪菜。马垃曾问他干吗不用猪饲料,他说饲料成本大不算,肉也不好吃,咬在嘴里里像嚼木渣。马垃想想也是,大碗伯炒的咸肉,吃起来就格外香。他每年杀一头年猪,一半给儿子郭东生一家,另一半就留给自己吃,腌制好后,基本上可以吃大半年的。
趁大碗伯歇下来的工夫,马垃把遇到赵广富的情形讲给他听了。大碗伯蹙起眉头说:“要论种田,广富的确称得上是神皇洲的头号能人,他把他那个富农爹的秉性全给传下来了,他大儿子在城里又是开店,又是办厂的,发了财,按说他也可以进城去享福了,可他死活也不肯进城去,和屋里人守着他和儿子丫头名下的十几亩责任田不松手。这几年,他还嫌自己的田不够,把别人撂荒的责任田捡来种,一来二去,他种的地只怕有了大几十亩,村里大多数人都给他家做过雇工。这要是在解放前,不就是名符其实的地主么?”
马垃似乎明白了什么:“这么说,永福哥是担心我跟他争夺那些撂荒的庄稼地啊!”
“可不是,赵算盘精明着呢。你这边还只是放了点风,他就把你当对手了。”大碗伯瞅瞅马垃,“垃子,你可得防着点儿。”
马垃嗯唔着,心里却想:我只是想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可没想把谁当什么对手,也绝不会再跟别人争夺什么利益……我已经不是什么企业家或资本家啦。当然,在这个时代,资本已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了,土地也不例外。他想起了列文,那个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农场主。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外表笨拙、内心丰富的人,并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朋友,就像他曾经狂热地喜欢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如果说他在青年时代喜欢保尔,进入中年后,他就更喜欢列文了。他喜欢列文那种质朴、内敛、注重内心生活,同时又具有行动能力的性格。马垃说不清其中的原因。难道仅仅因为列文跟自己那样,也有一个早逝的哥哥吗?
这天晚上,马垃偎着被子坐在床上,又拿出了那本不只看了多少遍的《安娜.卡列尼娜》,借着昏黄的电灯光看起来。他一边看,一边不时从枕头边摸出一本浅蓝色的塑料壳本子,用圆珠笔在上面记几笔,或者在书籍的空白处写一行文字……
在心爱的哥哥临死的那一刻,列文第一次用所谓新的信仰──在他二十到三四十岁期间逐渐形成,代替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信仰──来看待生死问题。自从那时起使他惊异的主要不是死,而是生。他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他的目的是生么,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生物体和它的灭亡、物质不灭定律、进化──这些术语代替了旧的信仰。这些术语和有关的概念对科学很有用,但对生命却毫无作用。列文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脱去暖和的皮袄,换上薄纱衣服,一到冰天雪地,不是凭理论而是通过切身感受,觉得自己像赤身裸体一样,因此必然痛苦地灭亡……
这些思想折磨着他,苦恼着他,时而轻微,时而强烈,但从不离开他。他读书,思索,读得越多,想得越多,觉得离追求的目标越远。
……整个春天他都茫然若失,精神上十分痛苦。
“要是不知道我这人是什么,我活着为了什么,那就无法活下去。可是我无法知道,因此无法活下去,”列文自言自语。
马路在劳改农场时,就曾经不止一次地面对过列文的这些问题。回到神皇洲的这些天,面对着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那种幻灭感,以前在他看来显得虚无缥缈的那些关于生和死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起来。他觉得自己仿佛被两种完全对立的力量剧烈的撕扯着,让他寝食难安。马垃想起谁说过一句:性格及命运。这话真是说的太好了。中学时,他明明念的是理科班,却狂热地喜欢文学,无论上课下课都捧着一本小说看得聚精会神,这使原本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的他结果只考了个师范。后来呢,又莫名其妙地辞职,下海经商了。用老同学丁友鹏的话说,他的行为总是让人出乎意料。当然,背后还有更刻薄的说法,比如“不靠谱”什么的。就像眼下一样,他捧着泛黄的《安娜.卡列尼娜》,读得那么专注,以至全然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