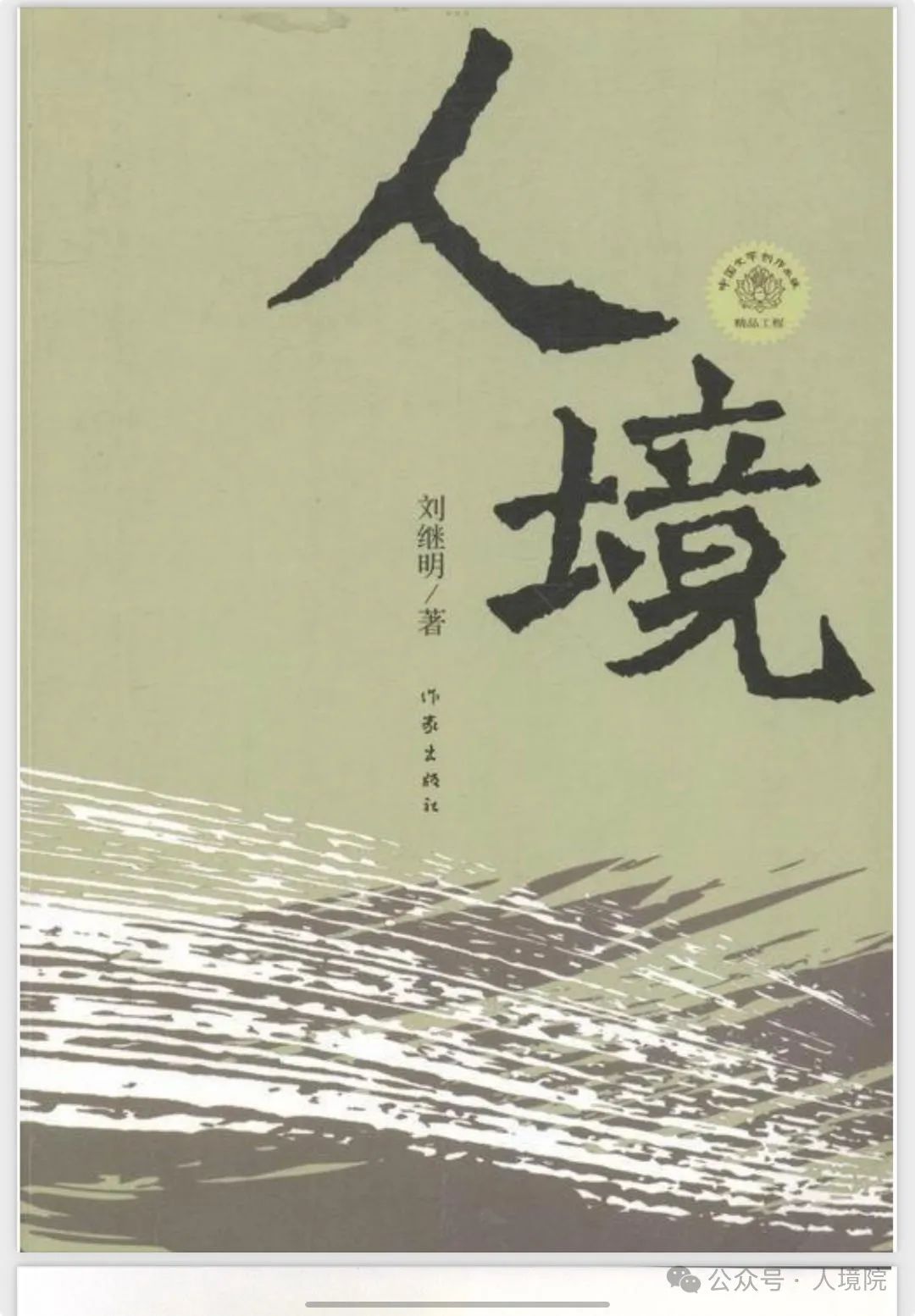
在众多到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中,喜欢《平凡的世界》的人当然远不只是谷雨。
同心合作社成立不久,旱田改水田的改造工程就大张旗鼓地开始了。两台从河口镇雇来的推土机,冒着七月的酷暑,在合作社几个农户刚收割完麦子不久的旱田里不分白天黑夜地施工。沉寂的神皇洲多年没出现过这种闹腾的场面了。
为了赶在节气前种上一季晚稻,马垃和谷雨要去长沙买稻种。
神皇洲人买种子都是去河口镇和县城的种子站,那里的种子品种够多了,他俩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宁愿多花路费爬到外地去买稻种呢?
马垃有自己的盘算。他想要买的可不是一般的稻种。按照他为合作社制定的水稻种植计划,不光产量高,还得好吃,只有这样,才能“保质保量”,实现他那个“翻两番”的目标。河口镇和县城的种子站他都去过,但没有哪一个品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后来,马垃从他订阅的那一堆报刊上发现了一条信息:湖南长沙一家农科研究所最近培育了一种名叫“两优2611”的杂交水稻,产量可以达到每亩900多公斤,比其他水稻高出了三百多公斤。培育出这种高产水稻的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一看到这名字,马垃眼里就一亮。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可一点也不陌生。二十多年以前,神皇洲大队就开始种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第一年亩产就达到了450公斤。据说沿河县农村那些年经常发生的春荒缺粮问题,就是因为全面推广了杂交水稻才解决的。从那时起,马垃心里就牢牢记着了“袁隆平”这个名字,所以,当他从报上见到那条关于杂交水稻的消息时,几乎凭着对“袁隆平”这个名字的信任,就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去长沙买“两优2611”稻种的决定。
长沙距沿河县有五百多公里的路程。马垃和谷雨先搭短途车到县城,在汽车站乘上了去岳阳的长途班车。
长途汽车驶出县城不到一个小时,就进入了与湖南交界的桃花山区。桃花山绵延四十多华里,横跨湖北省的沿河和湖南省的华容两县,是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之间唯一的山脉,境内山高林密,尤其以盛产楠竹闻名湘鄂两省。当年,马垃就曾跟逯老师到桃花山做过贩运楠竹的生意。据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贺龙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曾经在桃花山打过游击,著名的红军将领段德昌就是在这里牺牲的。马垃上中学时,学校还组织他们参观过烈士牺牲的遗址。
长途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缓慢地行驶着。两边是起伏的山峦,每一道山坳和村舍旁都长满了修长茂密的楠竹,每经过一片绿荫,就有一股阴凉扑面而来,其间,还经过了一座镜面一样的水库。马垃觉得自己的身心不知不觉变得轻盈起来。他索性把车窗全部打开,将半个身体伸到外面,让凉爽的山风尽情地吹拂着。长途车转过一道山岗,前面是一片平坦的谷地,一块块梯田连缀成片,田里的稻秧绿油油的,已经长到了膝盖那么深,风儿从远方吹过时,空气中飘过来一缕稻秧的清香……
马垃还是在多年前跟着逯老师跑生意时去过一次岳阳和长沙,距今过去了十几年。十几年的变化可以让他产生足够的陌生感,就像他从未到过这两座城市一样。谷雨呢,则是对于这趟行程熟悉不得不能再熟悉了。以前在广东打工,每年的春节,他都要走两趟来回的,在哪里转车换乘,从岳阳始发或路过,经长沙到广州的火车几点几分发车,他都了如指掌,所以,这一路上都是他给马垃当向导,让他的马老师省了不少心。一开始,马垃还打算一个人来的呢,当他看见谷雨一路上跑前跑后地买车票、占座位,轻车熟路的样子,不禁想,幸亏自己临时动念叫上谷雨……
当马垃和谷雨到达长沙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了。
出了火车站,就是长沙最宽敞也是最长的五一路。正值城里人下班和出行的高峰期,马路上熙熙攘攘、到处都是车和人,尽管太阳快要落山了,但暴晒了一天的热气丝毫也没有消散,而是渗透进了柏油马垃里,然后变本加厉地从脚下钻进人的身体,直到变成汗珠从毛孔里一丝一缕地蒸发出来。
天色已晚,去农科所买稻种只能明天再说了。两个人合计了一下,决定先就近找个旅社住下。五一路距火车站很近,旅社招待所多如牛毛。他们没费多大的工夫,就找到了一个既便宜,又还干净整洁的旅社。
天热得让人失去了食欲。两个人在旅社旁边的小吃店吃了碗凉面,就回到了旅社的房间。房间里没有空调,天花板下面的大吊扇,呼呼地旋转着,卷起一股鼓气流,把室内的热气从敞开的窗户驱赶出去。
经过一整天的旅途颠簸,马垃已是人困马乏,看了一会儿电视,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大概是第一次跟马垃出差,对面床上的谷雨却毫无睡意。他先是把出火车站时买的一张长沙交通图在床上铺开,寻找农科所的位置。那张交通图的比例尺太小,字号又小,谷雨睁大眼睛,找了好一会才找到;他摸出一支铅笔,在旅社和农科所之间划出一条最近的线路以及乘坐的公交车车次。然后,他又把交通图小心翼翼地折叠好,装进口袋。精力充沛的谷雨做完这一切后,伸了个懒腰,却仍然没有一点倦意。于是,他就从那只装着换洗洗衣服的旅行包里拿出那本《创业史》,接着在旅途上看过的那一页,继续看起来……
对于这部反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农村生活的小说,谷雨还说不上有多么喜欢。比起那部描写跟自己同时代农村生活的《平凡的世界》,《创业史》描写的时代毕竟离他很远。可因为是马垃郑重地向自己推荐的,他不能不认真地看。他信任老师的鉴赏能力,如果不是特别出色的书,老师绝不会专门推荐给自己的。尽管如此,谷雨还是无法否认自己读这本书时存在的隔膜。五十年代,不单自己,就是马老师也还没有出生呢!包括小说中写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谷雨也觉得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可《平凡的世界》就不一样了,小说里的生活跟他的经历差不多,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农村,主人公的欢乐和痛苦,成功和挫折,处处都能在他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就好像小说写的并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一样!谷雨狂热地喜欢上了这部小说。在广东打工的那些年,他换了不知多少家工厂,搬了多少次“家”,但这部他刚到广东买的《平凡的世界》,却直始至终被他带在身边,他记不清自己看过多少遍了,书页翻得稀烂,连封面都只剩下了一半。直到前不久回家时,他才忍痛割爱,送给了一个同样喜欢这部小说却买不起书的工友。
在众多到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中,喜欢《平凡的世界》的人当然远不只是谷雨。他到广东没多久就发现,差不多每一个像自己这样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工友都喜欢《平凡的世界》,有的原本素不相识,可一提起《平凡的世界》,话题就像开闸的水一样滔滔不绝,并且很快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后来,谷雨还参加了一个“《平凡的世界》读友会”,每逢放假,他们这些分布在不同工厂的书迷就聚集在简陋的工棚交流读书体会,有的为了喜欢孙少安还是孙少平,田晓霞还是田润叶争得面红耳赤。那次,当他们从报上得知《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病逝的消息后,不约而同地聚到一起,点亮蜡烛,为他们敬重的这位作家默哀,有的泣不成声,眼珠都哭红了。
工友中有个聂石生,是从河南来的,长得其貌不扬,却因经常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很受注目。“我们这些农村青年不仅要像孙少平那样为了追求美好生活和爱情不屈不挠地拼搏,而且要将它当做向一切不公平的现实抗争的有力武器。《平凡的世界》就是我们的圣经!”聂石生这句话曾经让许多工友热血沸腾。谷雨没读过圣经,但他懂那句话的意思,觉得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所以对聂石生很佩服。聂石生组织过一次抗议黑心老板超时加班的罢工行动,虽然不了了之,却让他在打工青年中名声大振。许多工友把聂石生视为他们这些打工仔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后来,聂石生学起了写作,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不少新闻媒体采访他,称他为“打工作家”。听说他靠写作挣钱买了房子,还调进了当地的一家报社,正式脱掉“打工仔”的身份和农村户口,变成真正的城里人了。有一次,谷雨在报上读到聂石生的一篇文章,竟然是呼吁打工仔多替老板着想,分担一下他们的“艰难”。
谷雨就是从那一刻起产生离开城市回老家的念头的。他说不清是向城市告别,还是向自己的青春和梦想告别。但无论怎样,《平凡的世界》作为打工生活的见证,永远镌刻进了他的记忆深处。任何时候想起来,都会百感交集、五味俱全……
天花板下的大吊扇呼呼地转个不停,扇起的风渐渐有了些凉意。对面的床上,马垃已经睡熟了,发出一阵阵均匀的鼾声。谷雨见老师光着上半身,担心他电扇吹感冒,就放下那本《创业史》,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将一块毛巾给老师搭在胸前。
谷雨回到自己的床位上,重新拿起书时,脑子里总是走神,怎么也看不进去。细想起来,他看小说的爱好,其实也跟马垃有关系。那时他还在念初中吧,马垃从县师范毕业分配到河口中学教书,谷雨正好在他任班主任的那个班上。有一次,谷雨从学校阅览室借来一本长篇小说,语文课时放在抽屉内偷偷地看,被马垃发现,当场收走了。谷雨吓了一跳,虽然这个新来的年轻老师跟自己是同一个村子的,但对学生很严,上任没多久,已经体罚过好几个同学了。在课堂上头看小说可是件很严重的事儿,谷雨想,这本借来的小说肯定会被没收,自己得按定价的双倍向阅览室赔偿了。孰料当天下午放学后,刚吃完晚饭,马垃就让人叫他去办公室。他一阵忐忑,边走边嘀咕,不止这个班主任老乡会怎么处罚自己。可出乎意料的是,马垃见了他,平时在课堂上的一脸严肃神情不见了,而是和颜悦色地问他学习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末了,把那本收走的小说还给了他。谷雨愣在那儿,不敢去接。马垃说:“这篇小说刚在杂志上发表时,我就看过。我主张班上所有的同学都看看。当然,不是在课堂上看,是下课后看!”他见谷雨惊讶得合不拢嘴来,又若有所思地说,“我念中学时就经常看小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青年成长的最佳养料,她能使你的内心由贫瘠变为丰富,由狭窄变得辽阔,由懦弱变得坚强,由碌碌无为变得充满理想。尤其是书中那些个性突出、品质高尚的主人公,会不知不觉成为你的良师益友,值得你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效仿、追随……”
马垃这句话像一把刀似的,牢牢刻进了谷雨的脑海里。从此,他不仅染上了看小说的爱好,还悄悄地把马垃当成了自己的“良师益友”,甚至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效仿、追随”。他总是把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和马老师混在一起,弄不清他们谁是虚构人物,谁是真实的人物。
躺在旅社房间里的谷雨脑子里空前的活跃。直到快半夜,他才渐渐有了些睡意。当谷雨终于像对面床上的马垃一样发出鼾声,沉沉睡去时,手里还紧紧捧着那本打开的《创业史》……
第二天一大早,马垃和谷雨起了床,办理完退房手续,他们就直奔公共汽车站,按照谷雨昨晚画出的交通路线,去农科所买稻种。
他们转了两趟公共汽车,又步行半个多小时,才找到那个农科所。农科所背靠着岳麓山,前面是一条幽静的林荫大道,两边长满了高大挺拔的松树以及别的树木,繁茂的枝叶像一把把巨扇,把整个天空都遮住了。道路那边,是农科所的试验田,种着棉花、水稻、大豆和小麦等作物,分布的很均匀,而且用低矮的木栅隔成一小块一小块,每个田埂上都竖了一个牌子,上面标着种植单位的名称和各种各样的数字。
农科所只有两幢房子,紧挨路边的是一幢两层红瓦青砖的楼房,另一幢是老式的紫瓦平房,显得有些破败。石头砌成的围墙布满了绿色的苔藓和密密麻麻的葛藤,一群群蜜蜂在上面嘤嘤嗡嗡地飞来飞去。
农科所的铁栅门只开了半扇,院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安静得出奇。
谷雨仔细看了看大门旁边那块白底黑字的门牌,确认这就是他们要找的那家农科所后,回过头对马垃耳语了一声:“没错,就是这儿。”说完,就带头大摇大摆地向农科所院子里走去。但他刚穿过那道半开的铁闸门,就从传达室里窜出一个只有一条臂膀的老头,操着长沙口音大声叫道:“站住!你找哪一个?”
谷雨不情愿地停下来,说:“哪个都不找,我们买稻种!”
“买稻种?你们没弄错吧?这里可是农科所!”独臂老头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们,不耐烦地说,“晓得不晓得农科所是搞么子的啵?”
“晓得晓得,”谷雨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不就是研究下种育苗么!”
“晓得个鬼!既然是搞研究,又何曾变成种子站的呢?”
谷雨被独臂老头呛住了,支支吾吾答不上来。马垃走上去解释道:“老同志,是这么回事,我们从报上看到新闻,说你们农科所最近培育了一种杂交水稻新品种,叫南优2611。”说着,从挎包里摸出一张折叠的旧报纸,“喏,你瞧,我们就是专程来买这个种子的……”
独臂老头见马垃不卑不亢,气质不凡,态度缓和下来,他乜了一眼递过去的报纸,挠了挠头皮,咕哝道:“南优2611?好像有这么回事,是杂交水稻研究室搞的。不过他们是邮购,从未有人上门来买呢。”
“我们本来也想邮购,可怕耽误下种期,就直接上门来了。”马垃说。
“只要没找错地方就好。我们进去问专家!”谷雨一边说,一边又莽里莽撞地要往里面走。
“你这后生好性急,”独臂老头再次拦住了他,“要问也得明天再说,今天是星期天,都没上班,你找哪个去问?”
搞了半天,却没想到今天是星期天。谷雨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怏下劲来。马垃拍了拍谷雨的肩,宽慰道:“没什么,今天就算认个路,我们明天再来。”
离开农科所,两个人沿着山脚下的林荫大道上漫无目的地溜达了一会儿,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了一片白墙青瓦、雕梁画栋、错落有致的建筑群,随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几个古朴苍劲的大字映入眼帘,马垃才恍然发现,他们到岳麓书院了。
马垃这是第二次来岳麓书院了。上一次是在二十年前,他刚从河口中学辞职不久,第一次跟逯老师出差,来长沙采购一批货物。由于和供货方价格谈不拢,他们不得不在长沙滞留了两天。待在旅社里无聊,逯老师就提出带他去岳麓山逛逛。去岳麓山必去岳麓书院,否则怎么算是来过长沙?文化大革命期间,逯老师参加串连,曾到过一次岳麓山,所以那次带着马垃,每到一个景点,就像导游那样解说一番,让他长了不少见识。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他们游览了称为“书院八景”的柳塘烟晓、桃坞烘霞、桐荫别径、风荷晚香、曲涧鸣泉、碧沼观鱼、花墩坐月、竹林冬翠。后来,他们又来到湘江边的爱晚亭,面对水天一色的秋景,马垃吟诵起那首在中学课文里学过的名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不由想到自己当初参加高考时,填写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第二志愿就是湖南大学。那时他的理想就是考入某所名牌大学,刻苦钻研学问,将来成为一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者,何曾想到现在竟成了一个生意人呢?……
马垃更没想到的是,相隔二十年后重游岳麓书院时,他换成了跟逯老师一样的角色,每到一处就给谷雨讲解一番,连语气和内容都差不多。谷雨呢,则处在了当年马垃的位置上,因第一次游岳麓书院,又没念过大学,对眼前的景致新奇十足,但也只是“新奇”而已,对于岳麓书院丰厚的文化意蕴则一知半解、似懂非懂。
这天,马垃和谷雨没有再回城里的旅社住宿,而是在岳麓山下就近找了个当地居民开的客栈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农科所。
这一次,看门的独臂老头没有阻拦马垃和谷雨,而是热心地告诉他们:“水稻研究室在二楼,最东边一间就是。”
两人上了二楼,楼道内很暗,由于刚到上班时间,有的办公室门还没打开,有的人则刚到,还在打扫卫生和打开水,显得有点乱。他俩来到最东头,果然看见门边的小招牌上写着“杂交水稻研究室”几个字。门开着,里面有个身材矮胖的姑娘正在抹桌子、拖地。走在头里的谷雨敲了敲门,那姑娘抬起头来,用衣袖揩了一下满脸的汗问:“你们找谁?”
谷雨说:“买稻种呢。”
胖姑娘哦了一声:“你们为么子不早点来?上周末我们刚发出去一批稻种,仓库里没剩下几斤种子了……”
马垃又掏出那张旧报纸,把昨天说过的话又对重复了一遍。胖姑娘瞅着他俩风尘仆仆的样子,问道:“听口音,你们是从外地来的?”
“可不,我们从湖北来的,家里的水田就等着下种呢。”谷雨快言快语地说,“大姐,说什么你也得卖点稻种给我们……”
“哪个是你大姐?”胖姑娘不高兴地白了他一眼。
谷雨细看了一下,才发现胖姑娘模样尽管有点儿显老,年龄却不大,比自己还小几岁,就忙改口道:“对对,应该叫大妹子。你行行好……”
马垃见谷雨这副滑稽样子,觉得有些好笑,在旁边替他打圆场:“姑娘,你刚大学毕业吧?”
胖姑娘原本撅着嘴巴有些不悦,听了马垃的话,竟露出了笑容,说:“嗯,我去年才从湖南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研究所。”
“袁……老师是不是在你们这个研究室?”马垃又顺口问道。
胖姑娘万分惊异地问:“怎么,你认识袁老师?”
“哦,不不,我只是仰慕而已。”马垃忙说,“1975年,我们村就种上了袁老师的杂交水稻,当年就让全村人吃饱了肚子,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呢……”
“好多邮购稻种的人都在附信里这么说。”胖姑娘自豪地咧开嘴笑了,“不过,袁老师不在这儿工作,他只是我们研究室的顾问。南优1126就是在他指导下培育出来的。”
抹完桌子,胖姑娘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找出一串钥匙,让马垃和谷雨跟着自己出了办公室,下楼来到那幢老式平房,打开其中的一间屋子,一股谷物的气息扑面而来。看来这里就是胖姑娘说的仓库了。
仓库里空空荡荡的,地上散落着一些邮寄稻种用的包装袋,所幸墙旮旯还剩下几只装得结结实实的麻袋,这让马垃和谷雨看到了一线希望。
“就剩这几袋了,今天的邮购汇款单还没到,再晚一步,你们就白跑一趟了。”胖姑娘用脚踢了下麻袋,故意避开谷雨,把脸偏向马垃,“你们要多少斤呢?”
“让我算一下,五个农户,原来的水田每户两亩左右,加上正在改造的旱田改水田,每户四亩,三五一十五,总共有……”马垃掐着指头换算着,“估摸得一百多斤吧!”
胖姑娘说:“那好,把这几袋都卖给你们。不够我也没办法了。”
“行行,不够不怪你,”谷雨赶紧说,生怕被人抢先似的,走到墙旮旯,抱起一袋稻种,掂了掂,“妹子,多的也卖给我们好不好?”
谷雨这一声“妹子”,彻底改变了胖姑娘的态度,她爽快地说:
“好,都给你们算了!”
称完稻种,付清款,马垃和谷雨在农科所门口叫了一辆三轮机动车,拉上稻种,直奔火车站,赶乘当天的火车,回神皇洲去了。
马垃和谷雨回到河口镇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因惦记着各农户旱田改造水田工程的进展情况,想着早点把稻种分给大家,两个人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也不想在镇上多待哪怕一分钟,恨不得马上赶回神皇洲去。但时间这么晚,汽车站门口连一辆麻木都没有,马垃想起了包小立,就在街边的一家超市给他打了个电话。不到五分钟,包小立就开着他那辆麻木过来了。
“小立,都休息了吧?”
“还没呢,正跟两个朋友在喝茶。马叔,这么晚了从哪里回来呀?”
“噢,这不,去长沙买了点儿稻种,麻烦你帮忙给拉回神皇洲吧!”
寒暄了几句,三个人就一起七手八脚地把那几袋稻种搬上麻木,然后往神皇洲开去。
由于天太黑,麻木开得较慢。这一整天的劳顿,已经让马垃和谷雨又热又累,两个人坐在后面的车厢里,耷拉着脑袋,身体随颠簸的车身像散了架似的晃悠着,不知不觉快睡着了。
当麻木从公路驶上通往神皇洲的渠道时,由于两边没有人家,全是棉花地,四野里黑乎乎的一片。包小立虽然经常跑这条路,可这么晚了还是第一次。即便打亮车灯,坑坑洼洼的路面还是让麻木像在波峰浪谷中行船一样跌跌撞撞、歪歪斜斜……
突然,麻木来了个急刹车。坐在后面的马垃和谷雨悚然一惊,睁开眼,见包小立从驾驶座上跳了下去。少顷,发出一声惊叫:“哎呀我的妈,这不是小拐儿么?”
听到这声惊叫,后面的马垃和谷雨全醒了。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也相跟着跳下车,看见惨白的车灯光下,小拐儿仰面朝天,满脸血糊糊地躺在渠道中间,刚才如果不是包小立刹车快,真是不堪设想。
包小立叫了几声,小拐儿也不回应。高小立就弯下腰,想把小拐儿抱起来,但小拐儿身体沉沉的,整个人像死了一样,小立对跳下车的马垃和谷雨喊道:“快搭把手!”
几个人一起把小拐儿连拖带抱地弄上了车。这当儿,小拐儿才发出一阵呻吟,四肢不停地抽搐,显得很痛苦的样子。
“小拐儿不是在镇上开麻木么,”马垃探询地问小立,“他这是怎么啦?”
“唉,他整天跟镇上几个小流氓斗地主,早把麻木输掉了,听说还欠了一屁股债。”小立紧锁眉头,望着马垃,“他这肯定是还不起债,被人打的……马叔,你看怎么办?”
马垃垂下眼皮,略略思忖了一下,果断地说:“回神皇洲,赶紧找村医吴道坤给他把伤治一下。”
“好!”小立应了一声,回到驾驶座,重新开动了麻木。
为了减轻麻木颠簸增加伤口疼痛,马垃把小拐儿抱在自己怀里,又让谷雨抱起他的两条腿,防止磕碰。黑暗中,他觉得小拐儿的身体烫得像一把火。对于这个孩子,马垃觉得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说起来,小拐儿的父亲赵光荣跟自己还是赤屁股朋友,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赵光荣的父母残疾,平时在生产队每天只能拿半个公分,碰上坏年景,碰上家里粮食经常不够吃,或每到青黄不接的季节,赵光荣就背着只空书包,在江边外滩上寻寻觅觅,凡是树上爬的,天上飞的、底下钻的,逮到什么吃什么。有年冬天,是一个星期天,马垃给生产队放牛,刚牵着一头牯牛翻过江堤,就看见赵光荣撅着屁股趴蹲在一片灌木丛里烧野火。马垃很好奇,站在他身后问,“光荣,你在搞么子呢?”赵光荣忙的顾头不顾尾,哼哼唧唧地水果来一句,“嘻嘻,我抓到一只獾子,烧熟了咱俩一块吃吧!”马垃也正感到饥肠辘辘呢,一听这话肚子顿时咕咕叫唤起来。他把牯牛放到一边去啃草,跟赵光荣一起趴在灌木丛里忙活起来。过了没多久,赵光荣用木棍从火堆里扒拉出一个烤得香喷喷的獾子。那天,马垃跟赵光荣吃掉了一整只獾子,吃得满嘴冒油。那个冬天,马垃跟着赵光荣在外滩上又抓到过好几只獾子和野兔。那时候,在马垃眼里,赵光荣多么像小人书里的那些抗日小英雄啊……一晃几十年过去,马垃怎么也没想到,两年前他刚回到神皇洲,就听说赵光荣在山西挖煤时死了。
这当儿,麻木剧烈地摇晃了一下。小拐儿再次呻吟起来。马垃抱紧这个伤痕累累的孩子,觉得他的身体那么廋小,很轻很轻,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走。回来这么长时间,想到自己对朋友的遗孤没有尽一点责任,马垃心里不禁有些内疚……
小拐儿伤得真不轻,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这一个多星期里,都由马垃照料着。他把小拐儿安顿在楼下的空房间里,不分白天黑夜地守候在旁边。小拐儿发着高烧,因气温太高,伤口都化脓了,闭着眼睛不停地说胡话、经常做恶梦。马垃让谷雨去请来村医的吴道坤,接连给小拐儿打了几天吊瓶,高烧才渐渐退下来,但身上的伤口还没有痊愈。
吴道坤每天都要来给小拐儿换一次药。一边换药,一边叹息:“这孩子命真苦,爹死了,娘跟人跑了,自己还被人打成这样,孤零零的以后怎么活啊……”
吴道坤以前是神皇洲的赤脚医生,常年背着一只红十字药箱,走村串户,到田间地头给人看病送药。在马垃的记忆中,年轻时的吴道坤有一双白白净净的手,手指又长又细,跟女人似的。大概正因为这样,他给人打针时动作很轻,一点疼痛都感觉不到。马垃记得,吴道坤给他动过一次阑尾炎手术,就在当时的大队卫生室里。那时候的吴道坤真是一表人材,不仅懂医术,歌也唱得好,年轻人不分男女都跟他玩得来。从武汉和县城里来的那些女知青更是如此,稍有一点头疼脑热,就往大队卫生室跑,吴道坤心软,经不住几句乖巧话,就给开张病假条。后来,吴道坤跟一个女知青好上了,大队把他和女知青恋爱的事报到公社和县里,上面还当做“知识青年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典型,大张旗鼓地宣传了一番,可没过两年,那个女知青就招工回城了,吴道坤这场曾将让他无比自豪的恋情也无疾而终。那时,吴道坤带了个女徒弟,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儿。不知什么时候,女徒弟和沿河县城本地的知青李海军恋爱上了。可女徒弟的命运比吴道坤也好不了多少,李海军返城时,两人的关系也就走到了尽头。女徒弟一时想不开,竟然在大队卫生室里上吊自杀了……两年多以前,马垃回到神皇洲,刚见到吴道坤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年那个相貌英俊、风度翩翩的赤脚医生,跟面前这个骨瘦如柴,脸上布满皱纹,牙齿都已开始脱落的老头,无论如何也对不上号。马垃心里一阵感慨。也难怪,吴道坤已经五十多岁了……
作为老资格的村医,吴道坤治疗这类皮肉受伤还是有把握的。过了几天,小拐儿的高烧就退了。最后一次开完药,吴道坤叮嘱马垃:“这孩子身子骨瘦,又受了这么重的伤,要想尽快好,得加强营养……”说着,他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听说赵广富的那个要女儿找了个比他大二十几岁的对象,是真的?”
马垃不明白他为什么问起这事儿。“有、有这事吧!”
“那男的以前在神皇洲当过知青?”
“是的,怎么啦?”
“他叫李海军?”吴道坤几乎是逼问道。
马垃刚想回答“是的”,但意识到不对劲。他抬起头看看吴道坤,发现对方脸色阴沉,眼睛红红的,像打摆子那样咬着牙帮子说,“当初,就是这家伙把我徒弟祸害的……”
马垃听心里咯噔了一下。对于当年发生的事情,他只是曾经略有耳闻,但那时候他还小,无法体会在当事人心里烙下的阴影。此刻,他注视着吴光荣那张苍老哀伤的脸孔,不知说什么才好。
吴道坤给马垃出了一道难题。长期的单身生活,使马垃在生活上随便惯了,一日三餐不饿肚子就行,哪里顾得上什么营养不营养?况且,他平时吃的极其简单,家里也没储备什么“营养品”,连鸡鸭都没养,平时吃鸡蛋他还得去镇上买呢。
马垃正为小拐儿的“营养”犯愁时,谷雨和茴香就送来了一罐鸡汤。从长沙回来后,谷雨就张罗把稻种分到各家各户,抓紧时间下秧,谷雨不仅要忙自己家的活儿,还要给合作社另外那几家农户做指导,一个人恨不能分成两半,忙得不亦乐乎。还是茴香提醒他,小拐儿的伤那么重,光靠马老师一个人照料也不行。两口子一商量,就杀了一只还在下蛋的老母鸡,煨了一罐鸡汤送来了。
鸡汤还没喝完,大碗伯又送来了一只他没舍得吃的腊猪蹄膀,说是炖了给小拐儿补补身子;
胡嫂也来了,带来一篮子红枣;
连一向很吝啬的曹广进也来了,他带的是一小袋端午节包粽子没包完的糯米。
十天后,小拐儿原来苍白失血的脸色出现了红润,他第一次下了床,走出房间,让正在堂屋里谈事情的马垃和谷雨喜出望外……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