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灵史》改定版连载(1)
张承志
编者按:张承志先生的《心灵史》面世于1991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迄今为止,这个版本是唯一的一个单行本,此后虽有几种文集收录,但除“花城”版外,再也没有单独成书过。尽管民间巨大的盗版印刷量让所有出版社垂涎,在文化界引起的广泛震动亦足见其影响力,但它似乎成了一道难题,让人握着烫手,又不舍放弃。于是,《心灵史》成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最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以谜题甚至禁忌般的存在方式,挑战了诸如文学、历史、宗教学科的研究者们,也让大西北的田间炕头众口相传,识字不全的农民搬出字典,势要老学新知,务必将它读完。
2011年,相隔二十年之后,《心灵史》改定版完成。新版的修改篇幅较之原版,高达三分之一,可谓易筋洗髓。改定版《心灵史》的问世,宣告着张承志思想的变化革新,新旧对比,从半内部化到彻底公开,从教民到人民,从特定群体到中国社会,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历史……全部做出了文本上的修改和内在逻辑上的融会贯通。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在被封锁的语言夹缝中,改定版《心灵史》以自印750本收藏版的方式,实现了思想的突围,并以售书所得,全部捐献巴勒斯坦难民营,实现了对天下大义的落地式践行,以此界定了当代知识分子与正义的基础与上线。
熟悉两个版本的读者可能会有体验,以新作定义《心灵史》改定版也无不可,在很多地方,改定之于原版,已经不是修订,而是断腕与换血。二十年蹉跎,新旧两相较,思想上的蜕化,恰如新生。
鉴于纸书绝版,即日起,“我们文化”获授权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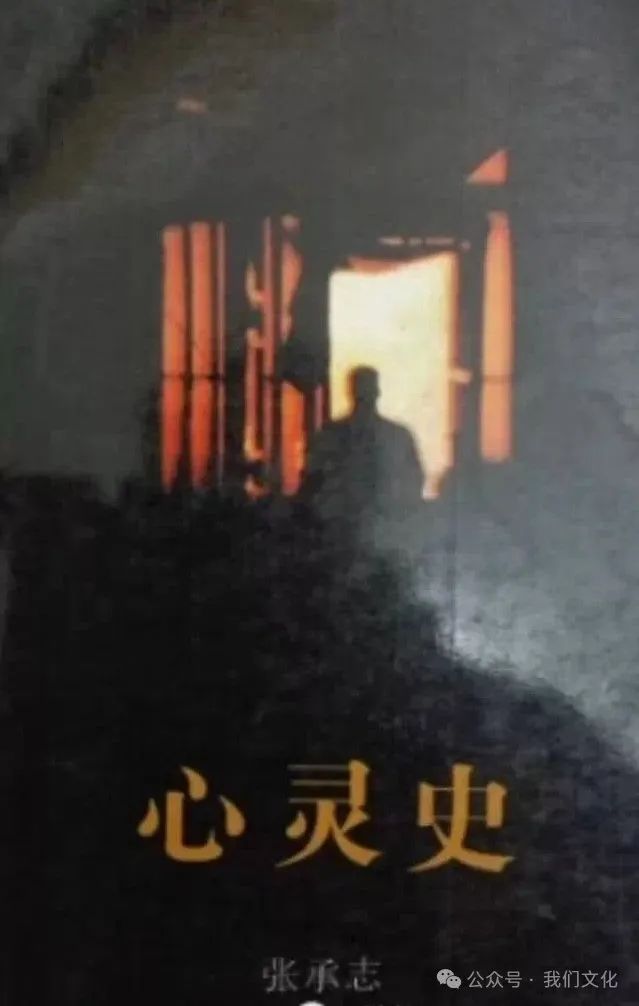
花城版《心灵史》(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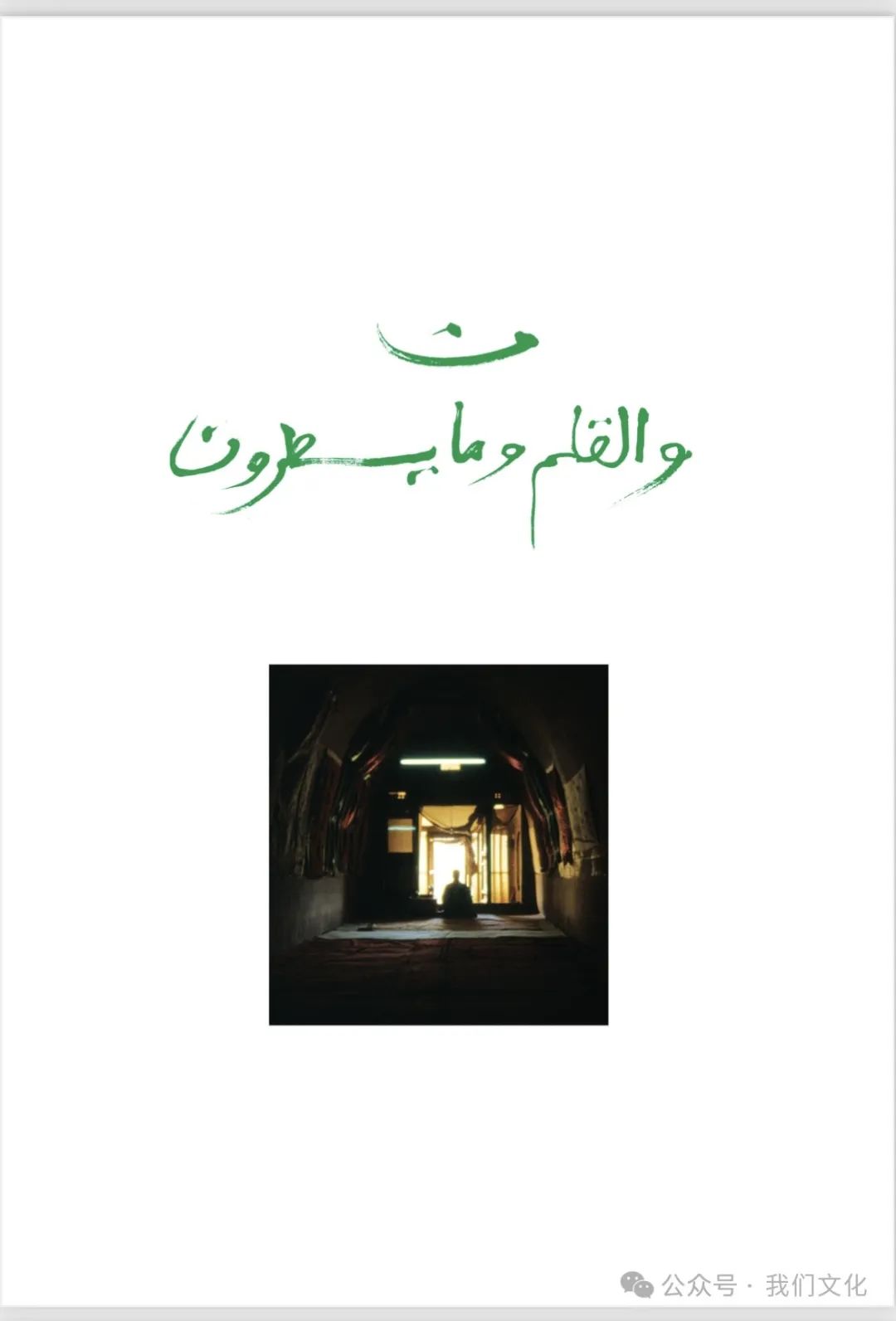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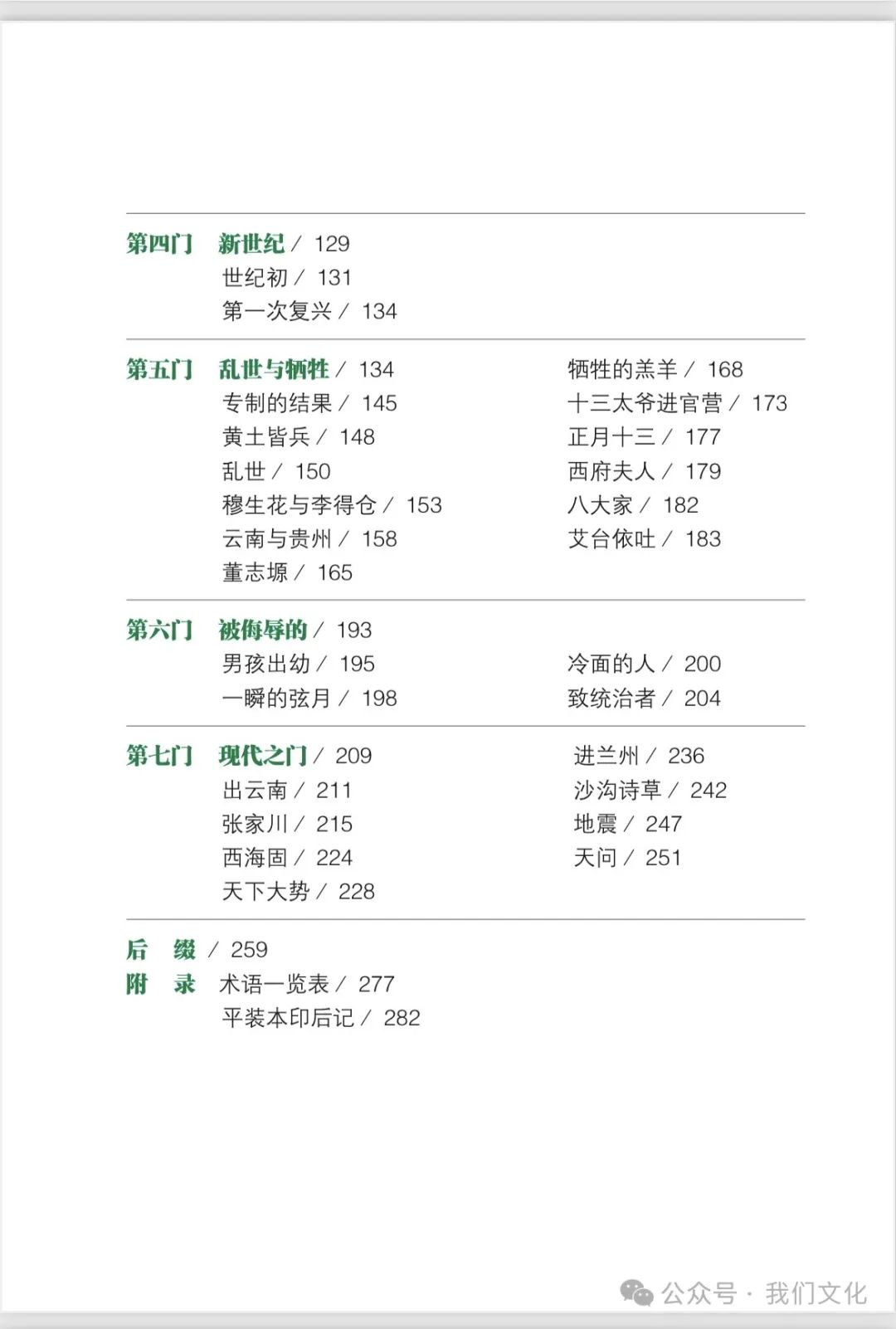

我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一个儿子,背负着它的感动与沉重,脚上心中刺满了荆棘。那个时代的败北,那个时代的意义,使我和远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同志一样,要竭尽一生求索,找到一条——自我批判与正义继承的道路。
1
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
也许此刻我面临的,是最后一次抉择。
肉躯和灵魂都被撕扯得疼痛。激动如潮水涌来。温暖的黑暗,贴着肌肤卫护着我。我沉默着,强忍着这种限界上的激动和不安。但是我必须解说;你们密集地簇拥着,焦躁地等待出发——大西北雄浑苍凉的黄土高原,已经大门洞开。
我被冲动窒息了。我如此渺小;而世界却在争抢着我。
谜底全数公开,本质如击来的大浪。
数不清的人物故事,熔化着又凝固成一片岩石森林。我兴奋而恐惧,我真切地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我只想拼命加入进去,变成那潮水中的一粒泡沫,变成那岩石中的一个棱角。
然而我的任务,却是描述它们。
怎么可能呢?炼炉中的铁矿石是无形的。成千上万人马呼啸着冲下、扬起漫天黄尘时,大场面中的人是无形的。
气质、血脉、信仰、心情——我要描述的这一切,是无形的。
而且无法概括。再无须说什么《黄泥小屋》或《西省暗杀考》;我的能力和经验,无法承托感受的巨大。
用诗么?在临近“它”的一个时期,我曾放纵于抒情,渲染我喜爱的图画。但是大西北交付给我的是一种复杂的过程。只有这过程,才是抒情的依据。只不过——哪怕简略地讲述一遍,私人的抒发也就消失了。
2
也许我追求的就是消失。
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渴望皈依、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
我找到了。我要把它写给你们,我的读者。它不应当仅是一种私人的体验。我盼望你们能理解、能了解我消失其间的大西北。
它也不是秀才的历史。大西北的所谓历史,早就湮灭了。我一直远离着——只听说了一片树叶、就吹嘘一片森林的方法论。
千真万确历史就在脚下活着。它在每一个早晨,在每一个庄户里重新开始。也许,我倾尽半生所做的,只是加入进去——和他们一起,写下这难言、复杂、激动、泥泞的一页。
大西北深沉而沉默。
我不敢断定。既然它忍受了那么漫长的苦难,难道就一定要在今天公开自己的心情吗?
3
一九八四年隆冬,完全是由于一种莫名的前定,我走进了大西北。
回忆从那个冬天起,至执笔的(1989)整整六年、再至此次(2011)重新修正之间的三十年;不尽的遭遇和体验、密集的脱胎换骨的过
程,已经很难逐一回忆了。
只是时至今日,回忆与西海固的初逢,依然觉得不可思议。
我虽然出身于一个回族家庭,但从小我接受的,多是革命的教育。所以,在和大西北穆斯林农民结交的最初日子里,如此一个受难的伊斯兰,给了我超出想象的强烈刺激。
一些年号,一些词汇,比如同治十年、一九五八,这些常用词随着农民们粗重的西海固嗓音,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
在判断的天平上,我三十年沉吟,掂量着轻重。思索中,对立的结论,在激烈地抗辩。
因为所谓三座大山,也确实并非莫须有。在农民们代代攀附舍身卫护的共同体中存在的神权压迫、阶级对立和人身控制,也是铁打的事实。
那场由国家发动的运动,也许有过支持底层阶级的动机。但它最终成了一场向着饥饿褴褛的农民实行的恐怖运动。它并非事出无因;但无论如何,它难能获得辩护——侵犯人道的抓捕、拷问、甚至滥杀,同时是对共产主义初衷的践踏!已经不能宽恕地结论为一次导致伤害的群众运动。那是一个国家,在拯救与歧视混杂的思想基础之上、以错误的施政,导致的对一部分人民的迫害。
那时我大约十岁,不知道这部分人民的遭遇,不知道他们几乎到了绝灭的边缘。
听着西海固的控诉,我还留意到,这种声音与流行的对革命的诅咒,并不相同。
——无论如何,不仅五八年、包括以前和以后全部与中国革命共生的悲剧,都是大西北给我的一种两面悖反的赠予,供我一生的思索与探寻。
4
西海固山区传说着一个个哀伤的故事。
这些故事伴随了我二十年。我先是听说、再读笔录,它们的刺激,它们对我的影响无法形容。
初次阑入的村庄,给我揭开了巨大的帷幕。我第一次活生生地听到了一个村庄的饥馑,听到了难以置信的冤案。
比如,哑巴阿訇的故事。
那一年,固原县黄沟村的王耀成刚念完经,还没有当上正式的阿訇,便赶上了五八年的灾难。他和一些宗教人士被关押在一个地点,日夜拷打,逼供莫须有的“叛乱”。那是全国性的灾难的开始;也是在银川市进行的﹑批斗哲赫忍耶教派负责人的前夜。
当王阿訇听说次日要把他押赴银川的消息时,他决意以死相抗。他趁夜逃出了关押队,一夜跑了近一百里。天亮时到了黄沟家中,他对父亲说:
“我举意死。因为,若受不住拷打,岂不坏了一家的伊玛尼!”
是夜他躺在自家的坟院里,用刀割了脖颈。
第二天,家人去坟地埋他,见地上流了一大摊血,但人却没有断气。治疗的办法居然是宰一个鸡,用鸡皮贴住伤口。从即日起他趁势装哑,不再开口说话。
从那一天起,王耀成沉默了整整十七年。直到“四人帮”灭亡、宗教活动得以恢复,他才重新开口。
他的故事震惊了整个西海固,也震惊了晚来的我。
虽然闻名已久,但我见到他时已是十年以后。
他握着我的手,把他在重新开口后抄写的一部《曼丹叶合》,送给了我。他已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依然罕言寡语。
我注视着他。民众抗议的形象,原来就是这样。
还应该说到李得仓,只是我无缘见到他了。
在五八年灾难最烈的关头,固原地区以召开会议为名,大肆对阿訇实行抓捕。李得仓不能忍受,他举起斧头,砍向压迫。于是他立即遭到逮捕,并迅速被处以死刑。
这是当时的一件大案。到了后来,人们还常用这件事来概括当年的形势。李得仓和他的斧头也出了名,成了流传的哲赫忍耶传说。这件事给了我一种崭新的、关于暴力的印象。
随着一次次不得已的心灵的自卫,暴力的血污,涂上了这一本宗教的历史。抵抗与暴力、和平的无望,二百年来这些悖论折磨着哲赫忍耶的心。只是,李得仓的故事告诉我:没有这把斧头,就没有民众的尊严。反抗,是受迫害的民众在绝望中的唯一选择。
5
大西北,即便不说西北五省、仅在甘肃宁夏一角,世界也依然过于辽阔。我一直在徘徊,想寻找一个合我心意的地方,仿佛冥冥的指引,我一步就踏入了西海固。
西海固——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最响亮的名字。它是宁夏南部陇东山区西吉、海原、固原三县的简称,也是黄土高原东部穆斯林山区的代名词。
那时的我如一粒风中的尘埃。我毫无知觉地、意外地飘进了西海固,并且落在了它的腹心地带——沙沟。
在这里,我结识了我人生中的挚友。他也说,好像是真主的安排,他在沙沟等着我。他是一个回族农民,从小穷困,没钱念书。但是他硬是识下了几个字,并且啃过《水浒》,他的名字叫马志文。他和他的乡亲们以一部沉重的西海固大书对我的启蒙,我永生不会忘记。
此刻,我开始动笔写这部书了,我知道他从此刻便一丝不敢松懈。我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目光像触摸一样,烫着我这只握笔的右手。从此刻直至这本书写完,他的心情会比我更紧张和严肃。等到我和出版社的编辑们谈论稿子时,我知道他会在遥远的山上祈求。那时沙沟四野苍凉的大山上,酷烈的旱风正吹黄稀疏的麦子,他和他的女人——时至二○一一年那个挂念我的小小行列里更站满了一代儿女——手里正握着镰,晴天里,从大山向远处望去,西海固的沟壑峰峦茫茫无边,像一片黄土的海。
我总在琢磨,他和他的乡亲们,究竟在等待着怎样的作家和作品。他们不读史书,他们不读小说,他们甚至曾经反对学习文化反对认字读书——然而,今天如此一类人,正期待着我。
由一个庄子或一家人,扩大到西海固、再扩大到青铜峡和甘宁两省、继而再扩展到大西北和半个中国。就这样,在他们的牵引簇拥下,我一步步靠近了本书描写的哲赫忍耶。
6
哲赫忍耶,是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支系。这个集体在历史途中曾遭遇多次镇压也多次选择抵抗,因此带着浓重的牺牲色彩。哲赫忍耶一词是阿拉伯语,意思是高声赞颂。
如今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回族穆斯林,是历史上进入中国的,阿拉伯、波斯或中亚穆斯林的后裔。自唐至元,从西亚、北非、中亚出发,信仰伊斯兰教的商人、工匠、军人,群体,或自愿或被迫、曾持续地涌入中国。
有的是跨海迁来,有的是组成商队——广州港和泉州港只是因他们与中国的这种商业与移民的关系,而成了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港口。珠江因阿拉伯珠宝商人船沉珠散,江水吞下珍珠而得名。云南因元朝以这种穆斯林人物为行省长官,所以不仅从那时起划入了中国版图,而且曾是中国穆斯林最多的省份。
外来的穆斯林移民,在中国每一个角落都定居下来。他们与汉蒙各族通婚,娶妻生子,体质上逐渐与东亚的中国人混血相融,人们不易区分他们了。
一两代人之后,在强大的汉文明同化之下,他们忘却了自己曾讲过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及中亚诸语——不仅失去了故乡,也失去了母语,他们变成了一种信仰的中国人。
人们后来觉得他们令人奇怪:穿戴语言都和汉族毫无区别,却古怪得不吃猪肉、还要守斋礼拜,有各样的禁忌与规矩。中国人喜欢含糊地看待事物。所以时间愈长,中国对于回回民族(这个词汇从宋元之际出现一直语义难考)的认识就愈糊涂。严谨的一神信仰和饮食禁忌,总是因无知而被曲解,甚至酿成可悲的伤害。信教,对中国人来说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虽然中国人也常常进香许愿,处处有雄伟的寺观、有数不尽的神像。
穆斯林生活在汉文明的海洋里。继失去故乡和失去母语之后,失去信仰的历程也一直在进行。随着历史的境遇,兴衰如潮落潮起。加之地理等原因,总是一部分回族区淡漠了信仰,而在另一部分聚集地宗教正繁衍兴盛。
哲赫忍耶因历史的厄运而达到了传播与发达;至二十世纪末它大约有四十至六十万人,主体部分聚集在甘宁新三省,零散信众棋布于半个中国。
7
正是中国史上的八九年。
那一年我抛弃了职位薪俸,习惯了在以西海固荒山为中心的北方放浪。
我一遍遍地让西北粗砺的旱风抚摩肌肤,心里总是满盈感动。向西我走到了伊犁,二百年前有一位妇女在这里殉命。我抵达她弃命的伊犁河畔,面对水天苍茫为她悼念。一种奇异的安堵感觉,环绕着我。向东我一直走到了松花江,步步体味了流放的艰苦。我遍访了各式各样的派别,请教了许多潜伏民间的奇人。我喜悦地感觉着自己的蜕变,这一个我,终于结束了昨天。
后来我才发觉:取道清洁的行为,不仅只是使人们不理解,它甚至招致了强烈的敌视——知识分子纷纷正攀附体制,我的行为对他们构成了否定。至于我与伊斯兰的结合,更引起了一片质疑、流言、与呱噪。
解释与辩白是困难的。当人缺乏共同的基础时,各自说的是不同的话题。
并非在今天我们才分道扬镳。
他们从昨天就与我不同。早在昨天我们也未曾同路。我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一个儿子,背负着它的感动与沉重,脚上心中刺满了荆棘。那个时代的败北,那个时代的意义,使我和远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同志一样,要竭尽一生求索,找到一条——自我批判与正义继承的道路。
一九八四年的岁末恍如隔世。就个人而言,那时我刚刚从日本的东洋文库学习归来,刚刚攀登完了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等求学路上的台阶。同时我作为一名青年作家正接连获得文学奖,暴发般变成知名人物。
唯我的心向着相反的方向躁动。因为,首先作为一名原红卫兵、其次作为一名原草原牧人,我渴望的远非这些。我对遍地的小人得势和知识分子作态,本能地滋生着反感。在无意识之中,突破新桎梏的冲动,一天天地蓄积着。
而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也刚刚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运动。
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无秩序、经济停滞、和以阶级的名义对人性的压迫——已然彻底结束。新的倾向在同步地发展:一种清算革命的思潮,从那时起抬头占据了主流。经济急速地复苏,被打得粉碎的官僚体制也完成着它的修复。文学在标榜着人道,不同政见在炫耀,但掩藏了粉饰西方的本质。学术在重建规范,但以考据的砖瓦砌筑起来的楼阁,在凝视中渐渐变得歪斜。
不能说我处处不同意。但我确实时时地感到——胸中异议的涌动。
文化大革命如中国的一种原罪,它折磨得人心不得安宁。肯定和否定的两极,都需要对官僚体制裁断。虽然我在它发生的时候只是个中学生,但我一直认为:若说那场革命有什么罪恶——那么以血统的借口对他人实行歧视的行为,是文化革命中的最大罪恶;同时,如果还能说出它有什么进步意义——它对庞然大物的体制实行过的破坏,永远给人民以想象和鼓励。无论如何,强大的国家机器曾在人民面前土崩瓦解——其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份。
清算过去的渴望,一直纠缠着我。
作为“红卫兵”这一词汇的作者,我希望自己对革命的反省,不是流行的道德表演,而是一次立场的改变。
是的,立场。我渴望自己从此拥有——人民的或底层的立场。这一渴望于我是很自然的;自从文化革命归于终焉,我在蒙古草原成了牧民,我早就惯于活在“底层的一翼”。
带着这样的背景和心情,一九八四年冬,我在黄土高原的深山里,遭遇了被称为哲赫忍耶的农民。
一张张粗糙的脸庞围着我。深夜泥屋的密语,他人不能尽知。人们争先恐后地向我诉说。他们深深地吸引着我、拉扯着我、诱惑着我。最初我毫无悟性,我没有察觉:一种承启的瞬间,已经出现。
我听着他们的故事,听着一群中国人怎样陷入绝地,在二百年时光里怎样牺牲和前赴后继。在蚁命苟存的中国风土中,我怎么闯进了一个造反者的集团?他们的刚硬,使我感到彻骨的震惊。
他们如波涛,拥载推撞着我。我沉入了这片黄土海,我变成了他们的一个。
他们真诚也复杂、淳朴也粗野。与他们在一起,于我永远是一种对中国理解的测试。哲赫忍耶喜欢使用一个称呼——多斯达尼,这个词是穆斯林常用的“多斯弟——朋友”的复数。我敏感地觉察到:多斯达尼就是一支中国底层的人民。
为着活命,也为了心中一念的自由,他们血迹斑斑地冲撞着,一连二百年。渐渐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精神——在外人看来,它耀眼夺目,诱人追究它的含义。
我所渴望的、对“六十年代”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那大时代的继承;我们一代人悲愿的、耗尽了年华岁月青发白发寻找的出路,可能就在他们中间。
以上都是本书写作的原因。
早就不是文艺或学问。我在讲另一种更深沉的初衷。如此的道路有如黑洞,走通了有一种晕眩。让文章突破名利的桎梏,让一粒的自我,投入民间传统的“共同体”。让自己的生命战胜异化——我为自己遭遇的这一切激动不已。
我下定了决心。我踏上了终旅。不会再有更好的契机,不会再有能与一个人民的共同体结合的方式。穆斯林喜欢把具有宗教意味的决定叫作“举意”——我举意:作一支民众的笔,写一本他们的书。
8
——有过这样的事:
在海固哲赫忍耶起义失败之后,那是在一九四〇年。政府进剿的军队探得领导起义的马国瑞师傅曾潜居一个山村读书;那个小村在固原,叫双林沟(或二林沟),师傅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丈夫投身起义后,家里女人娃娃,守着师傅阅读的两木箱书籍。后来官军前来搜查。当时女人正在切菜,见官军一拥而入,她举起菜刀,兵卒被她砍伤一个,她也死于刀枪之下。官军毁了她的家,但是没有找到那两箱书籍。
四十多年以后,哲赫忍耶能够公开了。这个村庄找到了师傅的女儿,正式把那两木箱书还给了她。
一九八九年,我看到并浏览了这两木箱书。木箱子很旧,书籍大多霉黄了。我说不出自己的感动。
我觉得,这些书是幸福的。
——早在考古学的阵营﹑后来又在蒙古学的队伍里,我已经怀疑了很久。面对深奥地层的猜测、渺无终日的碎片堆积, 使人往往忘记了历史的目的。同样,那种脱离游牧真实的貌似实证的作业,也无法回答我作为牧人时、对蒙古学问的初衷。学院经历在给了我知识的同时,也积累了我的不满足。长久以来,我感到天性的催促,我总想追求一种方法:那是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道路——它将把专业的知识和感动的立场,结合在一起。
如果我能驱使史料,又饱蘸民众的心情;如果我不仅完成历史的叙述,而且能温暖人的心灵——那将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在接受哲赫忍耶委托的瞬间,我感到了一种时机的临近。虽然我已经愈来愈多地看到了这件事的复杂性,但我还是不犹豫地接受了委托。
大西北热烈地欢迎了我。尤其哲赫忍耶穆斯林,给予了我以热烈的欢迎与合作。
秘藏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秘密抄本,为我译成了汉文。悄无声息的大规模调查开始,家史和地方资料送到了我的手里。一切秘密向我洞开,无数村庄等我居住。清真寺里的学生争当秘书,撇下年轻的妻子陪我寻觅古迹。困难时,尤其在一九八九年当我弃职之后,德高望重的农村老人破天荒地写信,给我寄来鼓励。这算是又一次出名么——从西海固到青铜峡,从云南到新疆,山区川地里的农民们半准不准地传说着我的故事,我尝到了从未有过的快活、自豪和幸福。
其中还有一九八九年秋天的心境。
那一年秋天,在悲愤和抗议的心情笼罩下,我摊开纸笔,开始了我的人生尔麦里。很快我写出了这部书,并与它一起,投入了光荣与危险、盛誉与贬毁的激烈漩涡。
9
以后约二十年的时光,磨炼了我也打磨了这部书。这是一场远较八十年代更长、也更细致的第二次深入。
倾听着从云南到新疆一块块土地上对它热烈的夸奖,心想着从北京到世界的世事万端,我在人群中,独自咀嚼和审视着自己在一九八九年写成的这一部书;也研究着自己又耗费了二十年人生潜入的、这个奇特的民众共同体。
随着我发现了一处处阙失、遗漏、失准、错误;随着我又用了近二十年渐渐感到了一种火候的把握,随着我终于对它的学术本质、宗教特征、仪礼内涵、社会枝杈——都能掂量分寸之后,我也就学会了从反对的话语中获取参考,就像学会冷静对待百姓们令人担忧的激赏一样。
我深知,无论是为了向社会负责,还是为了对读者负责,都必须把旧版《心灵史》做一次全面的修正。
同时,世界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剧烈演变,也激发了我更多的思考。在继续放浪广袤山河的岁月里,一个新版的腹稿,在酝酿之中渐渐成形。
分寸与把握日日增加,大小的缺欠也逐一暴露。进行一次最后的尔麦里、重写或修改的思绪,渐渐开始在心头萦绕。
尔麦里,一般指宗教功课的实践,在哲赫忍耶多指家族逝者的纪念仪式。但二百年里,人们常把决意、舍弃、牺牲、赴约等严肃大事与它混用,使得这个概念份量沉重。终于我再次举意——这一次,我感到笔尖份量的异样。
二〇一〇年春天,我完成了修正版的第一次作业。
我忆起文化革命的遗恨。
我常独自回味文革之后,知识分子竞演的道德戏。不知他们是否还想批判封建的血统论?如今它早已重建得固若金汤,俯瞰着左右的异端。
我觉察出,自己已经走得太远。早已不是对革命的忏悔,而是与强大秩序的对峙。难道不是么?对歧视的批判,必须站在被歧视者之中。如今我千真万确,正站在最受歧视的人群里。
对哲赫忍耶的赞否,实际上是对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底层民众的赞否,也是对千百万受歧视的穆斯林的赞否。是的,这是一个宗法封建的烟火社会,在神圣的名义下,现实粘满了污浊泥巴。但是,十八年的喑哑、被迫举起的斧头、屈死的遗体,依然是更大的问题。被压迫者昂首翘盼的,不是科学的套语,而是起码的公正。
官僚因为革命时代的结束,正用警察的眼光打量我的文学。一度对我寄予厚望的原教旨主义分子也最终断念,改取了与我对立的态度。我的姿态触怒了附庸体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围攻将永无终结。
——但是三重的包围,拦不住一条魅人的道路。
我已经学会平静地与误解共存。我个人的努力,即便最后被漫画与否定,也依然只是我的前定。说到底,文笔能够探索价值,人能与一方民众毁誉与共,也是一种幸福。
在艾尔默·莫德写的托尔斯泰传中,作者面对托尔斯泰的一生,谨慎又坚决地写下的如下一处,曾使我吟味不已:
但是托尔斯泰犯了许多高尚的智者在他之前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他看出一件重大的罪恶,又愤怒又急躁,急切地接受了一种不适当的补救办法,但在试验这个补救办法时却没有成功而是失败了。劝说人们离开人类生活的主流,而采取一条孤立的道路去拯救他们的灵魂这个办法,一次又一次地被尝试来纠正社会的弊端;但是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以外,一切社会改革的道路都证明是死胡同。早期基督教公社是这样,伟大的圣芳济会运动是这样,托尔斯泰运动也是这样。
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确是“不可分的成员”,脱离普通群众,我们决不能生活得更好。在实践中,结果是拒绝专业化的人——就是说,拒绝主要从事他能做得最好的工作——倒真正是过着不自然的生活。
《托尔斯泰传》,中译本p.671
这也许是价值观和思想史上,最严肃的一次驳难。显然,以普通、分工、自然等话语,对托尔斯泰倾向实施否定的——说到底是一种资本主义秩序的说教风潮——今日正百倍喧嚣地蔓延。
但是奴隶们仍拒绝知识分子建议的“专业化与自然的”奴隶生活。正是先行者托尔斯泰为我们辟出了崇高的方向,他的伟大遗教告诉我们:走通一条知识分子道路的需要,同样是紧迫的。
没有必要因为泥泞,就害怕穿过沼泽。不能因流行的歧视和舆论的不公正,就吓得从路上拔脚抽身。
毕竟我们和民众建立了难得的关系。毕竟蹒跚迈出了这一步,并走进了真正的共同体之中。毕竟此刻泥泞的两脚踏着的立场,是宝贵的。毕竟“人民的意识形态”——今天伊斯兰教已愈来愈成为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全球进攻的精神武器——也是一种深含意味的依据。
10
《心灵史》一书使用的、超出其他历史研究著作引用的资料,大致如下:
1. 《热什哈尔》(Rashh),阿拉伯文及波斯文,手抄本。阿布杜·尕迪尔·关里爷著,成书约于清嘉庆年间。在旧版《心灵史》(1991)
对之使用后,该书汉译本分别由三联书店(1993 年简体字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年繁体字版)在北京和台湾出版。
2.《尼斯白提》(Nisba),手抄本,阿拉伯文,哲赫忍耶穆斯林内部收藏的道谱。
3.《兰州传》,手抄本,阿拉伯文,阿布杜·秀库尔·西马营阿訇著,成书于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本书使用的是它的汉译本,未刊。
4.《哲赫忍耶道统史传》(Kitab al-Jahrīya),阿拉伯文,曼苏尔·马学智著,民国初年刻本。本书使用的是它的汉译本,未刊。
5.《曼纳给布》(Manāqib),阿拉伯文,阿布杜·艾哈德·毡爷著,成书于民国初年。本书使用的是它的汉译本,未刊。
6.《曼丹叶合》(Madā’ih ),阿拉伯文,赞圣诗。
7.《穆罕麦斯》(Mukhammas),阿拉伯文,赞圣诗,穆罕默德·舍尔夫丁·蒲绥里著,民国37 年(1948)迪化陕西大寺刻版,马良骏译。
8.《沙沟诗草》(拟名),汉文,马元章著,未刊。
9.《浩劫生日记》,汉文,金鼎著,民国10 年石印。
10.《历史社会调查资料》,约120 份,哲赫忍耶东寺义学记录稿,未刊。
其他一般的研究著作和参考资料,略不附录。
阿拉伯的文体,常把故事划分在一代代光阴,不称章节而叫作“门”(al-Bāb)。我借用他们的形式,把此书划为一共七门,勾勒哲赫忍耶穆斯林的一半故事。书的下限写到民国九年(1920)。至于当代和未来,我不打算续写:因为所有本质都已尽在其中。狗尾续貂不仅并无意义,而且有沦为世界资本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否定
工程之一砖半瓦的危险。
我终于描写自己的母族了。
但是你们会相信,这里并无狭隘。
我并没有离开你们:我的汉族、蒙古族,以及一切我的无形的读者们。我没有在任何一个瞬间忘记你们。我用汉语写作,我落草于北京。我似乎远走去了一个陌生异域,其实我时刻与你们在一起。
我借大西北的一抹黄色。我背靠着黄土高原和北方草原。不,我描写的不只是宗教,我一直描写的都是中国。我讲述各种异族的故事,但是我爱情的归宿和批判的矛尖,都指向着中国。
中国,这个我们生长于斯的古国,这片撕扯着我们情感的热土!她包涵广阔又混沌未开,她包容谦虚又自负傲慢。她怀抱着亿万儿女,又常给他们施以悲剧。一个世纪的救国呐喊,眉睫眼前的昌盛危机,都必须在自我与他者、人心的尊重、经济的复兴与天下的公正——这一系列巨大关口的面前,经受试炼。
对于我在一九七八年童言无忌地喊出的口号——那倍受嘲笑的“为人民”三个字,我已能无愧地说:我实践了它。这是对你们的一个约束;如今我践约了,没有失信。
在这篇前言里,我已尽量介绍了一些概念和常识。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漫长沉默的初次诉说,这毕竟是一种秘密的初次公开,我盼它不至于过份突兀与隔膜。要紧的是,茫茫的黄土高原和大西北向你们洞开了,走进来吧,习惯干旱和酷烈的风景,忍受锻炼的艰苦。当你们以这部书为地图,当你们也八次从大西北、十次从西海固归来时,你们会感到你们已经参加了我们共同的创作。我相信,当你们擦掉额上的汗碱和黄尘,重新细细品味我的著作时,你们会发现——它因你们的参与而完美了。
——那时,你们不仅会觉得自己触着了我的心,也会觉得自己触着了大西北的心。我的感情、你们的感情、死去的烈士们的感情,会彼此冲撞。那一刻的震撼将无法形容。我坚信那千金难买的一刻。未来的一代将羡慕我们,他们会觉得:在人世间,再也没有更珍贵的感情了。



 红歌会网 SZHGH.COM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